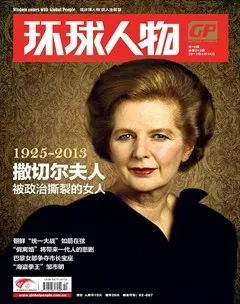“里根總統為父親再鑄勛章”
“外侮需人御,將軍賦采薇。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音同皮,意為棕熊)威。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沙場竟殞命,壯志也無違。”1943年3月,毛澤東在延安寫下《五律·海鷗將軍千古》,哀悼國民黨軍第二○○師少將師長戴安瀾。毛澤東一生只為兩位將軍寫過挽詞,一位是羅榮桓元帥,另一位便是戴安瀾將軍。
約訪戴安瀾長子戴復東先生時,記者有些猶豫。今年已85歲高齡的戴復東,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名譽院長、高新建筑技術設計研究所所長。不久前,老人剛剛經歷了喪子之痛,一直不愿意面對公眾。
記者來到同濟大學,獲悉戴老依舊很忙:給學生講課,參加各種學術研討會。在黃埔軍校同學會的幫助下,最終老人答應了采訪請求。回憶往事,戴老眼含熱淚,幾度哽咽。
談起父親戴安瀾,老人甚至對80年前的往事記憶猶新,他忘不了三四歲時,父親教他學游泳的場景,更忘不了父親犧牲后,靈柩抵達云南省騰沖縣時,全縣父老鄉親20萬人,沿街跪迎的撼人場面。“從昆明到廣西全州,沿途各城鎮,家家戶戶門前擺設香案,傾城祭奠。作為家屬代表,我從靈車上下來跪謝百姓,就這樣一路上,不知道跪了多少次……但母親和我們都不知道,其實棺材里,并不是父親完整的遺體……”
誓與同古共存亡
戴安瀾,字海鷗,1904年出生,安徽無為人。1924年投奔國民革命軍,1942年5月26日,犧牲在遠征緬甸的抗日戰場。國民黨中將杜聿明曾在回憶文章中用“慘絕人寰,欲哭無淚”,形容戴安瀾犧牲前后的慘烈。當時,國民革命軍抗日殉國的將領有160多位,第二○○師師長戴安瀾只是少將,卻同時得到國共兩黨的高度評價,可見其影響力非凡。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軍侵占中國東三省。1933年3月,時任國民革命軍第17軍25師145團團長的戴安瀾,奉命率部趕往長城古北口,與日軍主力展開激戰。這是戴安瀾抗戰生涯中,第一次與日軍交鋒。戰場上的日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中國士兵卻多為農民出身,不懂戰術,有的士兵槍還沒摸熱,便上了戰場,死傷慘重。為弄清日軍機槍與步槍如何協調作戰,戴安瀾冒著炮火登上長城觀察,被日軍發現后,用機槍封鎖了足足兩個多小時。
“很多人批評父親,說你是團長還跑到最上面去,太不安全。父親回答說,我就是要親自上去看看,如果我不去,就不知道敵人的情況,在使用哪些不同的兵器作戰。”戴復東說。
1937年,戴安瀾總結古北口抗日的歷程,寫下軍事教材——《痛苦的回憶》。“父親每每回憶起犧牲的士兵,都極為痛苦,因而起了這個書名,以表紀念。抗日戰爭開始后,他在日記中提出教育士兵射擊是非常重要的,總結了‘三個不打’等戰術,即看不見敵人不打;瞄不準不打;打不死不打。只有這樣,手中的槍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戴復東告訴記者,父親對自己要求極嚴,“那一時期,他還給自己制定了讀書計劃,要讀200本書,既有軍事方面的,也有政治、歷史、文學方面的,還要學英語和數學”。
對于屬下軍官,除了必要的文化素養,還有軍事考核,這方面戴安瀾把關相當嚴格。戴復東曾親眼看到過父親考核軍官,“一個大長桌子上面放一挺輕機槍,被測試的軍官用黑布蒙上眼睛,在規定時間內把機槍全部拆成零件,再全部裝起來,做不到的就不能晉升。”
1939年,戴安瀾接替杜聿明升任國民黨軍第二○○師少將師長,這一年他剛剛35歲。1941年底,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切斷中外海陸交通線。武器、彈藥、油料、裝備極度缺乏的中國軍隊,拼死也要打通中緬公路,以便美國的軍事援助能迅速輸送到中國。1942年初,國民黨十萬遠征軍進入緬甸。3月7日,為營救被困英軍,二○○師直抵同古城。此時,英軍不敢留在同古,慌張逃退,只剩下戴安瀾的二○○師孤軍鎮守。戴安瀾當時召集全師營以上軍官開會,帶頭立下“誓與同古共存亡”的遺書,他說:“此次遠征,系唐明以來揚威國外的盛舉,雖戰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同古。”3月20日起,二○○師與5倍于自己的日軍在同古城激戰12天,殲敵5000人,我方犧牲1000人,以1比5的戰績創造了中日交戰史上前所未有的戰果,國際輿論為之震動。
然而,戴安瀾不會想到,就在西方為中國軍人善戰而興奮時,一場災難即將降臨在中國遠征軍身上。
生為中華軍人,死為中華鬼雄
在同古戰役后,由于西線英軍一路大敗退,緬北戰局急轉直下。英國要求中國遠征軍申請難民身份,由英國軍隊收容。戴安瀾表明立場,“我生為中華軍人,死為中華鬼雄”。他發誓,“我戴某人寧愿與日寇戰死,絕不茍且偷生!”
戴安瀾率領與他出生入死的二○○師官兵,進入緬北野人山,開始向祖國方向艱苦突圍。5月18日黃昏,二○○師官兵隱蔽在緬甸朗科地區。戴復東后來聽大人們講,“父親一共要穿過5道防線才能回國,兩道山路,三道水路。敵人對父親恨之入骨,前四道防線父親都闖了過去,最后到了河邊,一部分官兵已經過了河,父親走在后面掩護,被日軍發現,腹部連中三槍。他身邊當時就剩下18人了。”
士兵們用樹木做了一個簡易的擔架抬著身負重傷的戴安瀾,走了一個多星期,5月26日到達緬甸茅邦村,眼看距離祖國只有三五天的路程了,但由于條件太過艱苦,別說藥品,連口吃的都成問題,戴安瀾的傷口開始嚴重化膿甚至生蛆。戴復東后來聽士兵們講,他們好不容易從老鄉那里要了點米,給父親拿來煮米湯,“父親開始還吃了兩口,后來發現他的士兵都沒有吃,就明白過來,也堅持不吃了。他在彌留之際,叫軍官們拿出地圖,給他們指明了一條回國的路線,這是一條日本人沒有安排重兵把守的路線,使得部隊能夠安全的回國。最后,他讓身邊的人把他扶起來,朝著北方也就是祖國的方向,望了最后一眼。
士兵們并沒有拋棄他們的師長,他們砍下木頭做成簡單的棺材,十幾人輪流抬著師長的遺體翻越緬甸野人山,往中國云南方向走去。“然而緬甸高溫,尸體幾日后開始腐臭,不得不就地火化。我后來才得知,他們取了一些父親的遺骨帶回祖國。”戴復東說,回國后,一位老華僑還專程找到他們,把本為自己做的最好的楠木棺材,送給父親用。
杜聿明在《悼念戴安瀾將軍》一文中寫道,“當我聽到他殉國的噩耗,正在緬北荒無人煙的野人山麓行軍。雖然沒有遭遇大敵和猛獸毒蛇的侵襲,而在原始森林,卻有無數不可勝數的蟻蚊螞蝗,足以殺人。眼看著成千累萬的將士,忍受著饑餓的掙扎,惡瘧的傳染,螞蟥的吮血,甚至一經倒地,幾小時之內,就被這些昆蟲吮吸成枯骨,此種殘酷的情景,簡直無法形容。想到將軍負傷前后的經歷,正同這是一樣,真是慘絕人寰,欲哭無淚!”
戴安瀾犧牲時,戴復東只有14歲。他還記得母親在貴陽得知消息后,整個人幾乎不能動。“我們不知道該怎么辦,抱頭大哭,但這是不能改變的。”讓戴復東感慨的是,護送父親棺木出生入死的幾位士兵,并沒有回到部隊,而選擇留在他的家里,幫助家人一起種地,共同謀生。
給里根總統寫信
父親去世后,戴復東決定擔起照顧母親和撫養弟妹的重任。他坦言,外界的條件如何艱苦,他都能扛得住,但內心深處,卻有一塊無法言說的“傷疤”。
原來,1942年10月29日,美國政府為了表彰戴安瀾將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做出的卓越貢獻,向其頒授了一枚軍團功勛勛章(武官級),中國稱為懋(音同帽)績勛章。戴安瀾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斗爭中第一位獲得美國勛章的中國軍人。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命令說:“中華民國陸軍第二○○師師長戴安瀾將軍于1942年同盟國緬甸戰場協同援英抗日時期,作戰英勇,指揮卓越,圓滿完成所負任務,實為我同盟國軍人之優良楷模。本總統依據美國國會授權特追贈軍團功勛勛章一枚,以示表彰。”1943年,美國又為戴安瀾頒發由杜魯門總統和史汀生陸軍部長簽署的授予軍團功勛勛章的榮譽狀。榮譽嘉獎令稱:“戴安瀾少將作為中國陸軍第二○○師師長,在1942年緬甸戰役中著有豐功偉績,聲譽卓著。戴將軍出色地繼承和發掘了軍事行動之最佳傳統,為他自己和中國陸軍建樹了卓越的聲譽”。
戴復東說:“這是父親用生命換來的榮譽和證明。然而在‘文革’中,這枚勛章遺失了……我們一直覺得愧對父親,愧對整個家族。這個事情幾十年來,在我們心里是一個很大的疙瘩。”
1982年,民革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戴安瀾將軍犧牲40周年紀念座談會,對戴安瀾的功績給予肯定。1983年,戴復東有幸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赴美國學習考察。當時,家族交給他一個艱巨的任務,希望能找到一張戴安瀾勛章的照片,如果可能的話,最好還能有美國政府授勛的文件復印件。到達美國后,戴復東一直心事重重,“時間不等人,美國這么大,我該到哪里去尋找?我根本不知道勛章是在哪個工廠制造的,甚至連勛章的名字我都想不起來了。”戴復東感到非常無助和迷茫,最后他想到一個辦法,嘗試給時任美國總統里根寫信。他寫道:“總統先生,我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訪問學者。有一件事情找您,不知是否妥當……”他在信中陳述先父戴安瀾在緬甸作戰,并榮獲美國政府頒發的軍團功勛勛章和榮譽狀,以及勛章和榮譽狀遺失等情況,商請里根總統理解他作為抗日先烈后代的心情,補發一張勛章照片和一紙榮譽狀存根復印件。“我根本沒敢奢望,只是想以此舉了卻我的一樁心事,也9cad0b5664f301a10c4ea9e3e99e1d7f91563c656cf2c4f7216e6398c6c193bd算是給家族一個交代。”信寫好了,戴復東卻苦笑,“不知道該怎么寫地址,寄到哪兒”。
“后來,我簡略寫下‘華盛頓市白宮里根總統收’,因為太籠統,連掛號信都無法寄,就這么塞進了學校門口的郵筒。”戴復東開始像往常一樣上課、教學,然而20多天過后,他突然收到一封印有美國陸軍部字樣的掛號信。“我第一反應是緊張,而不是興奮,以為自己惹出什么事端。一個很大的A4信封,拆開來一看,里面是美國陸軍部副總參謀長給我的一封信。信中說,由他代表里根總統處9cad0b5664f301a10c4ea9e3e99e1d7f91563c656cf2c4f7216e6398c6c193bd理這件事。隨信寄來了硬殼子綠色封面的榮譽狀和當年美國陸軍部的功勛檔案記錄復印件。信中還說,他已通知美國陸軍有關方面,將再鑄造一枚軍團功勛勛章直接寄給我。”
“我不敢相信,興奮得簡直要跳起來”,10天后,戴復東收到了美軍軍事授勛部核準處塞耶爾主任寄來的一枚嶄新的、金光燦燦的勛章!“沒想到我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寄了一封信,總統竟然能這樣幫助我。”這是戴復東晚年最欣慰的事情。
黃埔愛國情懷貫穿一生
在和戴安瀾共事最久、相知最深的杜聿明眼中,戴安瀾有著“雄偉的儀表和剛毅的個性,態度孤傲而不受縛羈,內心極度敏感而熱情奔放。”對于杜聿明的評價,戴復東坦言,他眼中的父親充滿生活情趣,很熱愛親人和家庭。
讓戴復東敬佩的是,父親對自己的發妻始終不離不棄。“母親是個農村不識字的婦女,很早便和父親定了親。父親從小學習成績突出,思想敏銳,后來考取了黃埔軍校第三期。入學后,他便把母親接到了廣州。母親本來沒有名字,纏著小腳,父親開始給她取名王荷心,他說荷花的心是很苦的,但出淤泥而不染。父親耐心地教母親認字,后來又給她改名荷馨,意為散發著荷花的馨香。”
戴復東下面還有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黃埔軍校的愛國情懷,貫穿了戴安瀾的一生。戴復東說:“1924年父親進入黃埔軍校后,將名字改為‘安瀾’,立志要在亂世中力挽狂瀾,報效國家。他為我們4個孩子所取的名字,都與國難和抗日有關。”戴復東原名戴覆東,意思是覆滅東洋。妹妹叫戴藩籬,意為筑起一道藩籬,抵御日本侵略;二弟叫戴靖東,平靖東洋鬼子;三弟叫澄東,澄清東洋鬼子。“在父親眼中,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的死敵,他永遠不可能有任何妥協。”正如蔣介石在同古之戰勝利后所說,“此役是中國軍隊的黃埔精神,戰勝了日軍的武士道精神。”
戴家的子女都很爭氣,戴藩籬后來成為上海市政協委員,戴靖東是原南京理工學院教授,后移居美國;戴澄東是原江蘇省委統戰部副部長。
2011年5月,戴澄東也終于圓了自己和家人的心愿,找到了父親的犧牲地。“這么多年,我忘不了一個場景。母親生前每每說起父親殉國,總是念叨‘他死的時候,怎么連個夢都沒托來’……不知怎么回事,我一直想去緬甸尋找、憑吊父親的遇難地,讓父親魂歸故里”。戴澄東在電話中向記者講述了自己尋找父親遇難地的艱難過程。
史料記載戴安瀾的犧牲地名叫“茅邦”,但地圖上卻找不到。戴澄東來到緬甸后,心里沒底。他先找到了“莫羅”,“據《第二○○師在緬作戰行動日志》記載,師長于茅邦殉國,一天后于莫羅渡瑞麗江歸國。與茅邦不一樣,日志在記載莫羅時配有英文注譯‘MOLO’,在緬甸地圖上能夠找到。” 戴澄東說,此行得到中國外交部的大力幫助,通過與緬甸方面交涉,詳述父親在抗日戰爭期間率部與緬甸人民一道抗日的情況,得到緬甸總統辦公室特批,才獲準進入。
戴澄東的到來,在當地華人圈引起了轟動。他先找到了當地3位中國遠征軍的后代,最終輾轉抵達莫羅。“此地是距父親犧牲最近的一個村莊,我們從3位80多歲的老人那里聽說,當時從南邊下來一支軍隊,步子很緊,到了江邊。部隊在江邊扎木筏、竹排,準備渡江。”戴澄東還得知,父親是在莫羅附近瑞麗江的一個江心坡上火化的。
“在莫羅附近確實有一個叫茅邦村的地方,我們大喜過望,第二天一早便啟程向茅邦進發。那里根本沒有路,汽車無法通過,大家租了7輛摩托車。然而到達后,我們卻非常失望,這個叫茅邦的地方和史料上記載的父親遇難地在地形、地貌上相差很大。”戴澄東說,只有再次尋訪村里的老人才能解開謎團。“一位老人突然記起,還有個老茅邦村。那里全是深山老林。”戴澄東一行人幾經周折,多次迷路,最終在當地副村長的幫助下,找到了老茅邦村。
“終于找到了與史書上記載的父親犧牲地一模一樣的地方,兩棵榕樹、老寺廟——寺廟雖然已毀,但舊跡尚存”。戴澄東說,大家一到這里,仿佛有心靈感應似的,不約而同地喊著:“就是這個地方!”
鋪開席子,點香、燃燭、燒冥幣,煙霧繚繞間,戴澄東已經哭成了淚人,這位已屆七旬的老人呼喊著:“父親,我帶著母親、先輩們的遺愿來看您了,不要做他鄉之鬼,您跟我們回家吧……”戴澄東下山時,從榕樹下取回兩小袋土,準備帶到父親在安徽老家的墓前。
雖然在十年動亂期間,曾有人質疑戴安瀾只是國民黨的英雄,戴家人也未受到過特殊的禮遇,但戴家子女在學業上卻個個成績優異。讓戴復東晚年痛心的是,自己的獨子熬過了“文革”的逆境,自學成才,在紐約大學畢業后,進入亞特蘭大一知名企業,后被派往中國做主管。“兒子對自己要求太嚴了,壓力很大,白天處理中國事務,晚上和美國那邊開會溝通,因為時差經常無法睡覺。他英文、日文都很好,吃飯的時候常常又做翻譯,三兩口對付了,后來發現是直腸癌時,已經中晚期了……”
年逾八旬的戴復東夫婦,還工作在第一線,他們將內心的傷痛深深掩埋起來,樂觀、積極地面對生活。戴復東覺得,相比那些連名字都沒留下便犧牲在異國他鄉的遠征軍戰士,自己已經很幸運了。“我們應該更關注那些普通的遠征軍戰士,歷史更應該記住他們。”這就是一位遠征軍將領后代的胸襟與心愿。(感謝黃埔軍校同學會對本采訪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