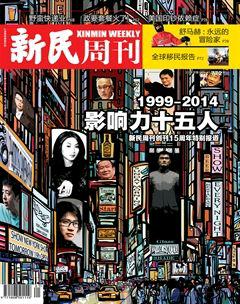似水柔情
西風
《阿黛爾的生活》好就好在毫無獵奇心態、驚人之語和驚險情節。
歷經多年抗爭,2013年5月18日同性婚姻在法國正式合法化,法國成為世界上第14個認可同性婚姻的國家;5月26日,女同題材的《阿黛爾的生活》非常應景地奪得第66屆戛納金棕櫚大獎,成為現象級影片。
有時候,一部電影足以改變你對這個世界和人性的看法。記得很久以前看過的一張影碟:一個老帥哥很郁悶,不知如何是好;一個大胡子男人則坐在沙發上掩面而泣:“你不是說他不會來的嗎?你不是說過不理他了嗎?”弄了半天,傷心總是難免的,這家伙在吃醋!我大吃一驚,媽的,這不就是在談戀愛嗎,他的反應和異性戀有啥區別?
同志電影的發展歷程,和同志婚姻合法化一樣艱難。1916年,瑞典導演莫里斯·斯蒂勒根據同性戀作家赫曼·邦的小說《麥克爾》改編的《翼》,可能是影史上第一部同志電影:藝術家愛上了他的男模,對其百般縱容。藝術家死后,模特才發現世界上最愛他的那個人去了。翼,比翼雙飛的翼。沒有你,飛得再高又有什么意義?丹麥電影大師卡爾·德萊葉1924年重拍《麥克爾》,在美國上映時不得不以“科學講座”的名義供醫生和學者觀賞。
1919年8月14日柏林阿波羅大戲院上映同志電影《與眾不同》,遭致全面禁映,僅供專業人士用于醫學研究。1968年松本俊夫捧出的日本新浪潮先聲之作《薔薇的葬列》,為日本同志電影的開山之作,薔薇在日本成為同志的代稱。
考慮到現實處境,同志愛情或可看做是戴著鐐銬的靈魂之舞。他們更需要愛和溫暖,以及理解與同情。隨著科學的發展、社會的開放、人權運動的興起,人們對同志題材的敏感和關注,逐漸轉移到電影本身呈現的藝術水平之上。
一個娘娘腔的男人和一個革命者同處一間囚室,會發生怎樣的故事?1976年,曼努埃爾·普伊格發表了他最著名的反映同志生活的小說《蜘蛛女之吻》。1985年,巴西名導赫克托·阿爾特里歐將這本小說搬上了大銀幕。威廉·赫特令人信服地詮釋了一個娘娘腔的同志為革命獻身的整個過程。同志只是和我們性取向不同的普通人,他們一樣會為了友誼、理想而赴湯蹈火。
有個長鏡頭:在革命者和監獄長之間如魚得水的同志,以探聽情報為誘餌,讓獄方為其購買食品。威廉·赫特懷抱兩大包食品,穿過院落、走廊,一路上熊腰款擺,風情四射,有許多驕傲,有些許忸怩。憑借此片中的天才演出,威廉·赫特獲得奧斯卡和戛納兩項電影大獎的影帝稱號。
1998年情人節,《愈墮落愈快樂》在香港舉行首映禮。導演關錦鵬對華人世界的同志之愛表現得非常到位,那么放蕩、驚世駭俗、難以啟齒卻又非常真誠的同志情感,以及看見心上人的心花怒放與小心謹慎,深深地感染著觀眾:為博得心上人的好感,身材矮胖、性情溫和而又善良的中年同志請帥哥到家里吃蝦,一幅占據了一堵墻壁的《悲情城市》的劇照漫不經心地出現在背景里,劇照的主題是出殯,一些剽悍、悲痛、沉默的黑衣男子撲面而來,極富視覺沖擊力。
就藝術品質而言,上學、吃面、艷遇、做愛、隔閡、失戀、授課,《阿黛爾的生活》那些流水賬般平易的鏡頭,將阿黛爾的日常生活娓娓道來,片長3小時也不令人感到厭煩。幾乎每個中國導演都可以用他們的作品告訴你,要做到這點有多難。
《阿黛爾的生活》好就好在毫無獵奇心態、驚人之語和驚險情節,長達數分鐘的情愛畫面也不讓人覺得尷尬,因為自然,觀眾體驗到的是美感和生命之火的激越:“同志”和我們一樣是人,理應享有和我們一樣的權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