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嫦娥之父”歐陽自遠:中國人不能止步于月球
文 _ 特約撰稿 馮在
“嫦娥之父”歐陽自遠:中國人不能止步于月球
文 _ 特約撰稿 馮在

從2013年12月15日開始,中國探月工程首席科學家歐陽自遠院士又一次過上了“月球時間”。這天凌晨4時35分,嫦娥三號著陸器與巡視探測器成功分離,“玉兔號”月球車正式開啟月球之旅。我就嫦娥三號有關問題發郵件向歐陽院士請教,在簡短的回復里,他這樣寫道:“在第一個月球的白晝,我只能集中全部精力探測月球,2014年1月23日以后的月夜,我們再討論相關問題。”
1月25日,嫦娥三號著陸器和巡視探測器相繼進入月夜休眠狀態,上面的部分儀器暫停工作。之后,我如約來到國家天文臺歐陽自遠院士的辦公室。
中國人為什么要登月
歐陽院士已年近八旬,卻保持著健朗的身體與活躍的思維。兩個多小時的聊天里,他對遙遠太空中的許多星球如數家珍。時間和空間的屏障好像都被打破,遙遠空間和時間里那些陌生星球的故事,在歐陽院士的講述中,親切得猶如鄰里間的家常話題。
中國人為什么要登月?在很多場合,歐陽自遠都會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
“中國人的目標是探測整個太陽系。登月只是個開始,好比一個門檻,你要拜訪鄰居,先得跨過門檻。雖然我們現在還沒能力去探測那些鄰居,但我們必須先走出去。”所謂“鄰居”,指的是金星、火星等。
面對公眾,歐陽自遠的回答形象而生動。但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歐陽自遠等人在論證探月計劃時,卻遠非這么簡單—反對的聲音從未停止過。
有人說,國際上已經近20年沒有任何國家探測月球了,美國的“阿波羅計劃”當年何等威風,后來也沒了下文,可見勞民傷財。
也有人說,美國與蘇聯在月球探測方面已做了不少事情,中國人再做,也不會比他們做得更高明。既然這樣,何必還要去做呢?
這些質疑,不只來自公眾,也來自部分專業航天人士。
支持歐陽自遠的人也不在少數。時任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就曾公開反駁對探月必要性的質疑。他說:“如果按照反對者的邏輯,對國外一切先進的東西都不必學習、借鑒和研究,那我們今天還在坐牛車、住茅草房。而且,如果中國人自己不做,那就只有買了,可月球能買嗎?月球資源、月球環境能進口嗎?”
日后,在幾所大學做報告時,歐陽自遠多次說道:“一個人一生當中,遇到各種挫折是難免的,我在做科學研究時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不被理解、支持……有時候很傷心,眼淚往肚子里流,但我從來沒有打過退堂鼓。”
有人把探月計劃論證期間的歐陽自遠比作戰國時代游走于各國間的“名嘴”蘇秦、張儀,面對科技人員、官員、企業家等不同的群體,歐陽自遠準備了不同的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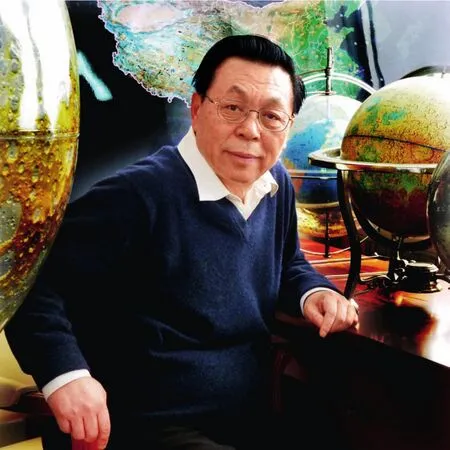
有“勞民傷財”的質疑在前,在計算用于第一顆月球衛星的經費時,歐陽自遠格外慎重:這筆錢必須是當前國家經濟實力能夠承受的,這筆錢投進去,還要通過探月衛星的發射,推動我國一系列高新技術的發展,同時培養、訓練出一支月球探測隊伍。歐陽自遠最終匡算出一期工程的總經費為14億元人民幣。
在各地做報告解釋這個數字時,歐陽自遠常選擇另一個數字作為參照:在北京,修建1000米地鐵得花7億元人民幣,即用在月球探測一期工程的錢,只能在北京修2000米地鐵。
經過一系列的論證、研究、爭取,歐陽自遠首次提出中國開展月球探測的申請報告。11年后的2004年1月23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自批準,中國開始啟動首次月球探測—繞月探測。
當天下午,歐陽自遠就知道了這個消息。當晚,歐陽自遠從家里拿來一瓶茅臺酒,請跟隨他的四個年輕骨干去一家餐館小酌慶祝。他們高高舉杯,歐陽自遠更是激動得話不成句:“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今天,我們很……幸運。”
把手伸到了十萬八千里外的天上
歐陽自遠的科研生涯是從研究地質開始的。1952年,歐陽自遠高中畢業,在國家“開發礦業”“地質是工業化的尖兵”的號召下,他成了北京地質學院礦產地質勘探專業的一名學生,并立志要“喚醒沉睡的高山,獻出無盡的寶藏”。畢業后,他找過礦、學過核物理、參加過粒子加速器實驗、參與過地下核試驗,但在做這些的同時,他始終關注著衛星探測。
1957年10月,蘇聯人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這給了地質專業研究生歐陽自遠強烈的震撼—原來,人類最終是要跳出地球去了解地球的。他隨之萌生了“跳出地球”的想法:“我想去做天上的東西,但怎么做,當時我并不知道。”
1958年,美國和蘇聯開始探測月球,1959年開始取得成功,之后越來越順利。1961年,美蘇開始探測火星與金星。他們發布的有關月球、火星與金星的新知識,歐陽自遠都會認真學習。
“我想知道為什么人家要搞月球和行星探測,他們是怎么做的。那時,我總希望未來有一天,中國也有能力發射衛星,探測月球和其他行星。”他說。
20世紀50年代末,面對緊張的國際形勢,中國開始了核武器試驗基地的建設。歐陽自遠參與了地下核試驗選址工作,一去就是十余年。
1976年,核試驗結束后,歐陽自遠為月球探測做準備的想法日益迫切。“萬一中國有一天可以進行月球探測,我就可以系統地提出中國該怎么走這條路。我覺得我的責任是要做好準備,假如我沒有認真做好準備,就提不出像樣的方案。”歐陽自遠曾這樣對媒體回憶。
歐陽自遠長期在中科院地質研究所、地球化學研究所工作,他通過對隕石這一“天外來客”的研究慢慢靠近月球。
1992年,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立項,歐陽自遠很高興—機會可能到來了!他認為,這說明中國具備了一定的經濟實力,航天技術發展很快,再努一把力就可以上月球了。次年,歐陽自遠提出了中國開展月球探測的申請報告。
但有人在背后嘀咕:“一個搞地質專業出身的,手卻伸到了十萬八千里之外的天上。”事實上,這也是歐陽自遠被問過無數次的問題。
從得知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的那天起,歐陽自遠就開始思考:如果把月球看作一個小地球,是不是也可以用地質學研究地球的思路、理論和方法來思考月球的問題?日后,他在很多場合重復自己思考的結果:完全可以用地質學的研究方法研究月球,包括月球的地形地貌和內部結構,月球的起源和演化,月球上有沒有礦產,人類以后能不能加以利用,等等。
歐陽自遠辦公室的墻上,掛了三張大圖:衛星遙感影像圖、首次月球探測工程全月影像圖和火星表面圖。后兩張尤其珍貴,那幾乎是他一生的夢想,用十個字概括便是—到月球上去,到火星上去。
除了科研工作,他也執著于激活年輕人心中的科學夢想。除了著書立說,他一年中要進行四五十場演講。針對不同的聽眾,歐陽自遠準備了幾十種版本的講稿,光講月球的就有28種之多。
關于探月工程,歐陽自遠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覺得探月工程是國家的,也是大家的。人民有權知道為什么要搞這個,取得了哪些成就,下一步準備怎么做,花了多少錢等等。所以我特別樂意去向大家報告這項工程的現狀和未來。”
中國人不能止步于月球
《讀者·原創版》:您現在看到滿天繁星,會想到什么?
歐陽自遠:我現在的視野不光是一個月亮,我看到的是,在直徑10萬光年的銀河系里,有1000億個太陽這樣的星球。所以在我眼里,滿天繁星都是遠遠近近的“太陽”。但不是所有的星球都有生命,在一個宜居帶上才可能有生命,只有在一定范圍內的星球才是值得關注的。
《讀者·原創版》:美國航天局上一任局長說,假如中國人愿意的話,可以在2020年實現載人登月。在您看來,我們什么時候能實現載人登月呢?
歐陽自遠:載人登月的時間有三個說法:美國人說是2020年;葉培健(繞月探測工程、嫦娥一號衛星系統總指揮兼總設計師)說是2025年;中國科學院召集了一批專家去討論,建議最好的時間是2030年。后來開了幾次國際會議,外國人最感興趣的也是這個,我的回答是:目前中國還沒有明確的時間表。

嫦娥三號在月球完美著陸
《讀者·原創版》:如果要為中國青年科研人員做一場演講,您會選擇什么題目呢?
歐陽自遠:我很想講的一個題目是“中國人要飛得更遠,不能止步于月球”。這是我的使命,中國人也有能力飛得更遠。我希望能激發大家對科學的熱愛和對宇宙的關注。我寫過一本書《再造一個地球》,就是希望改造我們的鄰居火星,把它變成一個適宜人類生存的星球,如果成功了,地球上至少一半的人可以移居火星。
要寫《地球之命運》
《讀者·原創版》:您一直很喜歡讀書,可以推薦一本您印象深刻的書嗎?
歐陽自遠:我非常喜歡的一本書是兩位搞天文學的科學家寫的,非常有意思,叫“繼續生存十萬年,人類能否做到”。現在我們擔心的都是50年或100年后,人類在地球上還能不能夠存在。人類已經造成了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生物多樣性銳減、全球變暖與海平面上升、資源匱乏等諸多問題,我相信人類能逐漸改正自己的錯誤,但要有個過程,我真的不知道100年以后地球會怎樣。
但這本書從整個地球發展的角度,憂慮地球的命運,假如人類不好自為之的話,地球的活力將維持不了10萬年。10萬年在地球的歷史上相當于一天中的兩秒鐘。50億年以后,人類絕對不會只棲息在地球上,但是我們要弄明白地球的命運,所以我也準備寫一本書,暫時命名為“地球之命運”。
地球上為什么有生命?地球的“先天遺傳”,如大小、與太陽的距離等決定了地球的命運。50億年之后,地球內部的能量將全部耗盡,沒有火山,沒有板塊運動,沒有溫泉,地球將非常安靜,就是一塊大石頭,跟現在的月亮一模一樣。月亮已經“死亡”了,它的活力在30億年以前已經釋放完了。所以,我要研究地球是怎么變化的,它有哪些特性,與它的兄弟姐妹—火星、金星等又有哪些共性。
《讀者·原創版》:您現在最想問自己什么問題?
歐陽自遠:現在科學家都在討論地球曾經發生過什么,我們也已經知道地球的產生和演化的歷程,但很少有人去設想地球的未來。所以,我最想問自己的問題,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按照地球自己的規律,它的未來會怎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