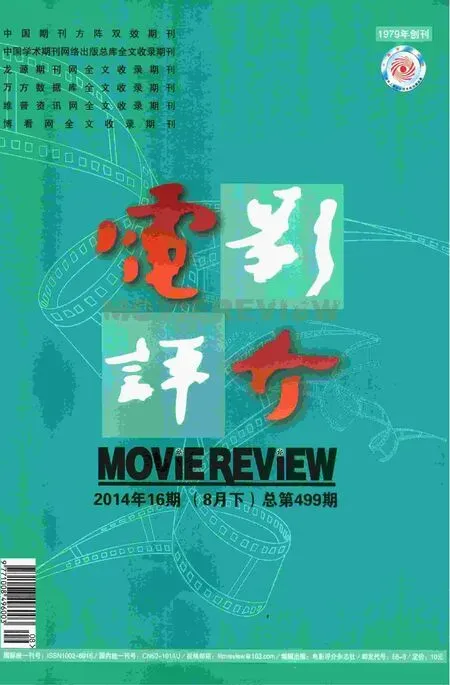論庫珀對美利堅的民族書寫
李 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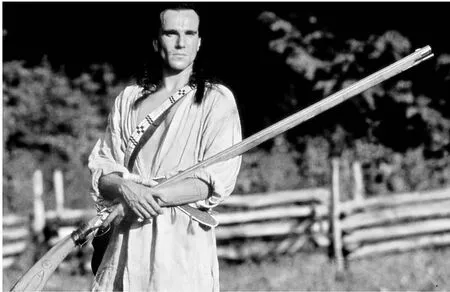
電影《最后的莫西干人》劇照
詹姆斯·費尼莫爾·庫珀(James Fenimore Cooper)是美國文學史上的一位重要的小說家。關于庫珀的作品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邊疆小說的個別作品研究上,在整合性研究方面尚有拓展的空間。本文從作家的民族國家意識出發,將庫珀的創作分為西部邊疆小說、海洋小說和寓言小說。通過對作者的各類代表作品進行的梳理和歸納,研究庫珀在創作的不同時期對美利堅民族的歷史做出相應的文學描述和想象。
庫珀作為美國民族文學的先驅者和奠基人,將文學創作與整個時代的發展緊密結合,喚起了美利堅民族對北美這片熱土的渴望與關注。庫珀的創作內容涉及美國革命、邊疆、海洋和荒野,成功地展現了邊疆和海上的既浪漫又現實的生活,象征性地再現和預見了美利堅帝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從《拓荒者》中表達的頗為謹慎的樂觀主義到《火山口》展現的世界末日圖景,庫珀記錄了美利堅民族的身份訴求,同時表達了對人類未來的憂思。
庫珀不僅強調地理、經濟的重要性,還重視其政治文化發展的重要性。他認為民族與海洋的關系更密切,倡導海洋民族主義。1812年戰爭中海軍的勝利及其后迅速的壯大使國家的航海業成為直到內戰前的民族身份的同義詞。國家的建立必須通過歷史與文化的建構,以分享共同的經驗進而形成“生命共同體”,才構成正式的“民族國家”。而敘事就是指民族的文學或文化生產。民族的觀念作為一種文化構成是共和國初期庫珀海洋小說的鮮明特征。許多美國作家想通過創造獨特的美國文學傳統來聲稱美國的民族身份。雖然庫珀并非通過小說塑造民族精神的第一位作家,他的愛國主義思想體現在小說《間諜》中,使他成為美國民族文學的開創者。小說《間諜》描寫的是一個關于美國獨立戰爭的故事,卓越地表現了美國當時民族獨立的感情,明確地歌頌了美國獨立戰爭事業。《間諜》所體現的民族國家概念深入人心,激發了美國民眾的開拓進取精神,而當時的背景是國力強盛,民心振奮,年輕的共和國蒸蒸日上,開發西部的熱潮方興未艾。與此同時,庫珀也表明了高尚的動機和崇高的目的如何被伴隨社會革命而來的暴力與混亂所扭曲,主要體現為民族矛盾和宗教困擾。
《最后的莫西干人》和《打鹿將》都展現了內部矛盾對民族身份建構帶來的威脅。在民族前進的道路上,屠殺令人痛心,但印第安人的宿命似乎是既定的。庫珀表現了三種矛盾:歐洲殖民者與印第安人之間的矛盾、殖民者內部的矛盾——英法戰爭及印第安各部落之間矛盾。庫珀考慮了歷史的力量和復雜性,大自然的美被暴力損毀。在《拓荒者》(1823)中,庫珀對荒野的描寫傳達了田園氣息,然而在這可愛的畫框內活動著一個充滿潛在的破壞性變化的人類世界,文明對原始荒野肆意侵擾。庫珀對于在荒野中創造一個世界的過程感到異常興奮,同時他內心又很矛盾,對于被破壞的自然表達了其生態意識。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社會的不穩定,民主政體暴露了它的陰暗面,對后來的美國社會結構造成了威脅。這里體現了庫珀自身兩部分的沖突,即獻身文明世界,投入美國進步事業與留戀邊疆的昔日田園生活景象之間的沖突。自然與社會的邊界受到人類及人類的政治野心的突圍,直到他們節節敗退,印第安人被大肆屠殺。庫珀是第一位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印第安人的作家,盡管攜帶著白人的偏見和優越感,但他對印第安人尊嚴的肯定,對他們的品德和才能的認可,實屬難能可貴。
《打鹿將》中有一段精彩的質疑之聲,書中第十一章明哥(休倫)印第安酋長瑞文諾克的一番言辭不啻為一篇駁斥白人教義的檄文:“那么,為什么白臉人自己要用槍炮呢?如果是上帝命令白臉人有人要一件東西,就應該給他兩件,那為什么印第安人什么也沒有向他們要,他們卻要從可憐的印第安人手中奪走雙倍的東西呢?白臉人夾著這本書(《圣經》)從太陽升起的方向來,勸導紅人讀它,可是為什么他們自己倒把圣書里面說的話全都忘記了呢……”一番話一針見血道出了教義的偽善,虔誠的白人姑娘海蒂一心篤信《圣經》,聽罷此言,失聲痛哭。單純的她想不明白出了什么問題,圣經解釋不了,解決不了。《圣經》是白人的教義,只對白人有益。在此庫珀對清教進行了質疑和譴責。在掠奪成性的新英格蘭,美國的加爾文教派培育了片面追求金錢和財富的精神,夸大了自身利益的重要性。庫珀深刻憎惡清教主義虔誠與貪婪的結合導致的極端狂熱和殘酷。然而,西進的征程勢在必行。庫珀的作品以歷史的視角反映了美國當時的三大問題:清教、西進運動和印第安人。
庫珀晚期的小說表現了對共和國未來的擔憂以及對人類文明的悲觀展望,具有寓言啟示錄的意味。《威什頓威什的悲哀》(1829)、《懷恩多特》(1843)和《火山口》(1847)勾畫出了作者的文學創作轉向,主題的筆調越來越陰郁低沉。邊疆居留地的美麗河谷變成了死亡與毀滅的荒原。《火山口》中描述居留地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土著和海盜,而是來自內部。當整個島嶼沉入海底時,庫珀對祖國的極端憤怒及前途的絕望表達得淋漓盡致。《杰克蒂爾》(1848)筆調陰郁悲觀,展現貪婪與暴力為所欲為。《海獅》(1849)表現庫珀的混亂感不斷增加,具有寓言意義,大自然必須整頓目之所及這個正在失控的世界。《爍林空地》(1848)表現大自然的美與戰爭的暴力交織,宗教成為最后安慰,暗示了救贖的思想。
貫穿庫珀小說的一個主題即民族身份的本質,庫珀的目的是幫助美國人達到精神上的獨立。他的小說中的400多個鮮明可辨的美國人物對國家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塑造作用。事實上,庫珀的小說作為社會產物和歷史記錄(盡管是間接的),積極地參與了政治,探討和反思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庫珀通過小說對民族身份建構進行想象和反思,探討民族身份的本質,表達對其穩固性和持久性的渴望與擔憂,延伸到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懷。
一個國家的人由于政治原則獲得民族身份后,通過想象自己屬于一個共同體,想象著自己擁有屬于該共同體的身份而獲得歸屬感。安德森強調想象的功能,而想象是文學的特質。然而這種通過想象而獲得的歸屬感是動態的,這種身份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從早期對民族身份的展望,到后來對民族身份的擔憂和反思,庫珀的作品一直在參與民族身份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