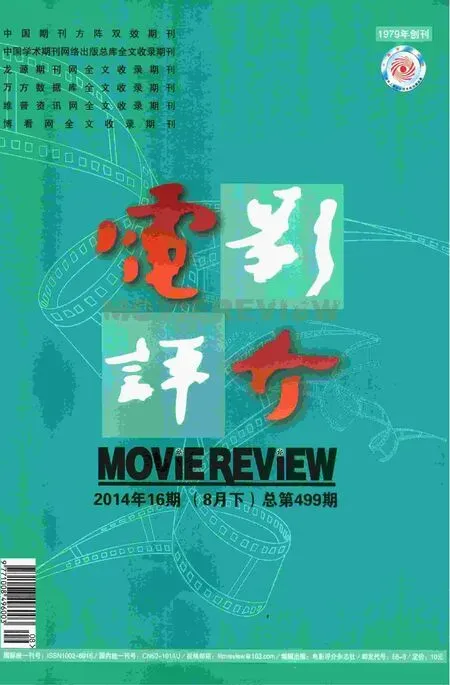革命歷史電視劇的敘事藝術
黃巧莉
革命歷史電視劇的敘事藝術
黃巧莉

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劇照
一、人民性的革命領袖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中國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在塑造革命領導人時就非常注重刻畫其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親密聯系,從中凸顯中國共產黨為民代言的價值立場。比如在很多革命歷史劇中常常出現軍民聯歡的場景,在中國共產黨取得重大戰斗勝利時,在歡慶中國共產黨入城時,在慶祝中國共產黨重大紀念日時,在慶賀中華傳統民族佳節時,電視劇中通常會出現民眾載歌載舞的熱鬧情景。在這樣的場景中,革命領導人一般也會加入到民眾的行列“與民同樂”,于是,熱情的吶喊,鼓舞人心的革命歌曲,洋溢著歡樂的張張笑臉,舞動的紅彩綢就會環繞革命領導人左右,在鏡像上將革命領導人置于人民的圍攏擁護之中。電視劇《周恩來在重慶》將這種人民群眾簇擁中國革命領袖的儀式化場景具體化為日常生活片段,濃墨重彩地描繪了周恩來對人民群眾的“輻射力”以及人民群眾對周恩來的向心集聚效應,通過周恩來在泥濘中與大家一起推車,日軍空襲重慶時保護驚慌失措的一對母子,關心身患肺病的文藝女青年小貓等一系列“與民相處”的小事,形象地刻畫出一幅“周恩來總理與人民群眾在一起”的歷史畫卷。此外,在軍民聯歡的狂歡化場景中,革命領袖人物與普通民眾之間通常會發生隨意而親昵的身體接觸,“而這種親昵接觸中同志間的身體接觸顯得十分突出:握手、撫摸、擁抱、扶、拉手、拍打等成為革命同志間的最常見的身體語言。”[1]在電視劇《周恩來在重慶》中,周恩來總是時刻準備伸出雙手,張開懷抱去溫暖鼓舞每一個身世凄苦的弱小者,在同這些普通人親切的身體接觸中,周恩來總理與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也就不知不覺地得到了藝術呈現。
二、氛圍的營造
新時期出現的許多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在注重情節敘事的同時,還十分注重借助霧氣、日光、陰雨等畫面構圖因素營造獨特的歷史氛圍,從而傳達某種主題意義。比如《長征》、《紅色搖籃》、《毛岸英》、《中國1921》等革命歷史電視劇中曾多次出現的“雨”的意象,在電視劇歷史氛圍的營造上顯示出獨特的敘事功能。在《長征》敘述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以及長征前期的損兵折將時,“雨”的鏡頭時時穿插顯現,比如當彭德懷視察前線陣地時,鏡像上呈現的是如注的大雨,雨水打濕了彭德懷將軍的衣服,在雨霧中他神情凝重地巡視戰地部署,通過“雨”所形構的悲哀愁苦的氛圍襯托了戰略決策的重要與戰爭的殘酷,以及紅軍將士大無畏的勇敢作戰精神,也有力地襯托出共產黨高級將領體恤下屬的深情;再比如當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紅軍主力被迫戰略轉移,實行長征方針之前,賀子珍將毛毛托付給妹妹照管,當妹妹抱起毛毛漸漸消失在滂沱大雨中后,賀子珍仍佇立門前,向前張望,雨景的設置很好地展現了賀子珍對兒子的深情,雨水聲恰似如泣如訴的嗚咽述說著一位母親對兒子難舍難分又只能忍痛分別的復雜心情,從而也凸顯了革命先驅者為革命事業所做出的超常貢獻。“‘雨’作為意象雖并不與特定歷史時期必然相關,但作為一種獨特的視覺意象,‘雨’的反復出現,無疑彰顯了歷史敘事在空間上的悲愴與悲劇意味。”[2]中央蘇區所在的地域的確常年雨水較多,但雨景的經常出現已不再是單純的環境意義,而是敘事情節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承擔著主題意義的傳達使命。通過與“雨”形成對比的“日出”,我們似乎可以更加印證這一看法。在攻占遵義縣城,召開遵義會議前夕,毛澤東與朱德曾經有過一次談話,談話的地點是在霧氣彌漫的小樹林,通過逆光拍攝的鏡頭,我們可以清晰看到一輪紅日正在升起,太陽的光線穿透云霧灑滿了整個樹林。這個鏡頭出現在紅軍就要召開具有扭轉性意義的遵義會議前夕,“撥云見日”的意味就顯得特別明顯。在遵義會議召開的當天,毛澤東與朱德談話時的那點霧氣也不見了,創作者以仰拍鏡頭展現了在幾聲清脆的雄雞啼鳴聲后,太陽從召開會議的小樓東方“噴薄而出”的態勢,與此同時還輔以雄壯的《國際歌》旋律,通過這種氛圍的營造,遵義會議的意義不彰自顯。而在紅軍到達陜北后,鏡頭中的畫面總是置于太陽的強光之下,畫面的明亮色彩與中央蘇區時陰暗低沉的色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鏡像上預示著紅軍擺脫了國民黨部隊的圍追堵截,到達了自由廣闊的陜北地區。它們“把紛繁復雜的戰爭敘事升華為主流意識形態范疇內的歷史哲理,從而最終實現影片的創作立意并提高其藝術品位。”[3]
三、角度的選擇
新時期許多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也注意角度的選擇。比如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敘述了一個脫離戰場的革命干部石光榮與其頗具小資情調的妻子褚琴之間柴米油鹽、吵架斗嘴但仍相伴幾十年的故事。作為其改編依據的《父親進城》等系列小說敘述的卻是“一個經組織安排,以戰斗英雄的單向激情而構成的捆綁式婚姻故事,展現壓制個人意愿,由行政命令主宰的婚姻悲劇”。[4]石光榮蠻橫霸道的大男子主義不僅扼殺了褚琴的婚姻幸福,也斷送了三個子女的人生。通過搜集、考察小說創作者的創作談話,我們不難發現這種敘事構想其實隱含著作者對父母關系一廂情愿式的主觀猜想以及作者某種隱秘的情感缺失,在一種有些偏激的心理動機支持下,作者無疑在小說中放大了父母之間的爭吵與斗爭以及由此而來的婚姻悲劇。但是在電視劇中,電視制作者們摒棄了這種創作角度,不少主創者都認為“這兩個人在一起幾十年,怎么可能沒有好過呢?”顯然,這種猜想更為符合現實生活邏輯,也更能引起廣大觀眾的認同,否則,我們無法解釋這兩個人在彼此憎恨的情況下又如何相伴一生的事實。于是,在電視劇情節中,與石光榮爭吵了大半生的褚琴終于意識到石光榮這個倔強的老頭對自己的意義是那么重要,三個子女也從起初對父親的反抗不解轉為認同理解父親的良苦用心,由于在父親的安排下都收獲了人生的圓滿與幸福,在情感指向上也從站在母親一邊轉為對父親更深沉的情感依戀。因此,在從小說改編為電視劇的過程中,一個反思人性復雜性的文本,但在某種程度上也內置著創作者偏頗思想的小說文本變成了一個通俗淺顯,但是也更具人間真情的倫理故事。在創建社會主義文明的征途上,我們需要知識分子創作的激進文本,以時時給社會大眾以痛徹肌理的警醒,但是,我們更需要溫情的世俗文本,以維系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與溫暖人心的倫理親情。
[1]楊厚均.革命歷史圖景與民族國家想象——新中國革命歷史長篇小說再解讀[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04:63.
[2]宗俊偉.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的敘事機制[J].中國電視,2012(8):24-25.
[3]楊鼎.“后革命”時代的革命歷史影視劇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07:41.
[4]張紅軍.從教化到迎合:中國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的商業化敘事策略[J].現代傳播,2009(3):70.
黃巧莉,女,河南商丘人,中國傳媒大學藝術學部戲劇影視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影視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