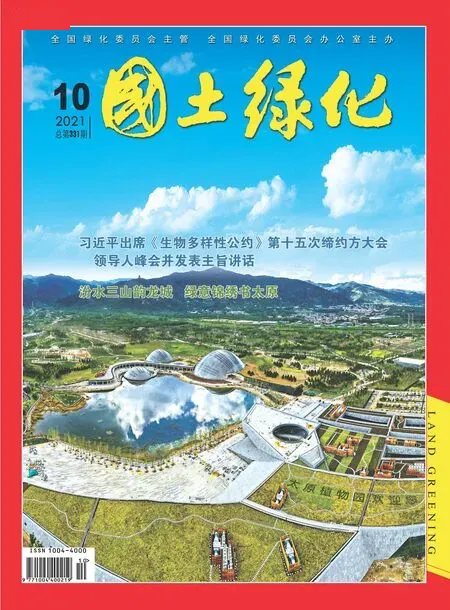風搖梧葉秋意濃
◎ 武華民

中秋已過,滿園的梧桐樹葉隨風飄。
梧桐,是大院綠色的主角。從春到夏又至秋,梧桐樹高大挺拔的軀體上,滿目的綠葉,或隨風搖曳,或靜如處子,繁若云海。
天空依然澄澈,陽光卻不再威風凜凜。參天的梧桐樹,似乎擁有頂天立地的神奇。縱然夏天里驕陽如刀似劍、勢不可擋,濃綠厚重的梧桐樹葉,卻如綿柔的盔甲,瞬間將瘋狂的炙熱柔化。綠蔭所至,陽光退讓。偶爾勉強透進來的一束束炙熱,也被濃密的綠色擠成一地的影影綽綽,留下遍地的失意和黯然。
院里的梧桐樹,經過移栽、修剪和澆灌,在漫長的歲月里,漸漸生長成擔當和希望。長大后,它枝繁葉茂、偉岸實在,擎天立地,拱衛出片片綠蔭。這種擔當和希望,寬厚與親切,與時空共存,和大地渾然天成。它把綠色寫滿天空,讓濃密的屏障遮天蔽日。
秋雨綿綿,樹葉沙沙,雨水滴答的韻律像首夢幻曲,和著節拍,撫摸著片刻的寧靜。濃密的樹葉呼吸著濕風,飄忽著綠色的靈動,生命的乳汁在吮吸里煥發出厚重的力量。水珠,晶瑩剔透,穿越斑駁,悄然滲入大地,水天一色,煙云共生。
入夜,樹葉在一束束燈火里似醒似睡,斑駁里泛著沉穩的光澤,擁抱著暗夜,搖搖晃晃,忽明忽暗,或濃綠,或幽暗,斑斕莫測。
秋風一陣陣襲來,那張揚的茂密漸漸消失。清瘦了許多的梧桐樹葉,飄落如串串詩行。經歷過陽光風雨和陰晴圓缺之后,滿院的梧葉奉獻了如山的希望和濃郁,看淡了莊重和熱烈,悄然注視著蕭條和寂寞,枝頭多了空曠和落寞。
大風漸起,高大的綠色屏障在空中搖曳著。梧葉脫離羈絆,飄飛起來,悄無聲息。這些金黃色的精靈,翻卷著、飛舞著,堆積成厚厚的柔軟,鋪滿大地的懷抱。
梧桐葉子,那如詩如畫的樣子,經過了青春和奮斗,被日子發酵成平淡,消磨成無棱,便再也沒有了遺憾和落寞。
落葉,悄然融入大地,從此天地一脈。或榮或枯,或綠或黃,或在高處,或在塵埃,終也無悔。歲月如洗,生命如歌。待到又一個春暖花開,隨風跳動的枝頭,又將迎來一個生機勃發的如夢世界。
人生,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