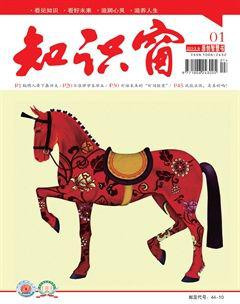深圳沒有地方話
馬繼遠
1
初到深圳的人,或許會驚詫于深圳竟有這么多的“關”:梅林關、布吉關、南頭關……非但如此,“關內”“關外”也是深圳人經常掛在嘴邊的詞匯。聽多了,就讓人覺得“關”的內外,仿佛真是有著天壤之別的兩個世界。
一個“關”字,也容易讓懂點歷史或讀過武俠小說的人神游九州,想到函谷關、玉門關、山海關等天下名關。這些名關蘊含著的,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是烈風黃沙、恩怨情仇,是金戈鐵馬、家國山河……也因了這眾多名關,“關”字便滿浸著歷史的塵埃、歲月的風霜、時世的滄桑!只是,這一切,會和年輕的深圳相關嗎?
向早些年來深圳的人打聽,他們多會很有經歷似的告訴你:現在來深圳,很自由,以前可不是這樣,那時來深圳需要辦邊防證,入關需要接受檢查的。經歷過入關苦痛的人,可能還會抱怨這些關卡的可惡。他們的痛苦經歷,甚至是同已漸被人們淡忘的“收容”“遣返”等制度聯系在一起。
深圳這些“關”的所以然,也沒幾個人能完全解釋清楚。不過打聽下來,你還是會恍然大悟:原來深圳的“關”與歷史、武俠并不搭邊;原來大名鼎鼎的深圳經濟特區的范圍和深圳完全畫等號,只是近兩年的事。這些關卡先前隔開的,正是特區內外。
即便現在深圳經濟特區的范圍已擴大到了“關外”,“關”內外的差異仍相當明顯。直入“關內”的人,初見深圳特區的高樓林立、車流人流,肯定會止不住感嘆:特區就是特區啊!可某日經梅林或布吉出了“關”去,則會產生大大的失落:“關外”的城市面貌,竟和普通內陸城市差不多。
隔開特區內外的這些“關”,深圳人習慣統稱它們為“二線關”。如果你執著地發問下去,那也該有“一線關”啊,在哪里?估計更沒幾個人能說清楚。
在網上查找,你就可能明白深圳“一線關”的所指——粵港邊境管理線!只不過,“一線關”上沒有叫“關”的,都叫“口岸”,像皇崗口岸、羅湖口岸。別說,“口岸”聽起來比“關”是要洋氣點。那些出入境口岸,都通向與深圳毗鄰的香港,口岸的數量,好像也是全國城市中最多的。
如今在深圳,“一線關”少有人提及,卻仍在那里堅實地扎著。“二線關”深圳人還不停地說,可已形同虛設。過“二線關”,真的不需要履行檢查手續了。一些設在交通干道上的關卡,因為阻礙交通,還面臨著被拆除的命運。
2
經常有朋友問我,深圳人講話,能否聽得懂。我的答復總是:哦,深圳這邊的人基本都講普通話。
其實我這樣回答時,心里頗有點小慚愧。我帶著濃濃家鄉味的腔調,肯定就不算普通話。真要往普通話上靠,套用洛陽挖苦人的說法,只能算“半自動普通話”。沒辦法,小時候在農村上學,很多字的音調沒讀準,長大了,就再糾正不過來了。
幸運的是,我如果不講偏僻的方言俚語,說話大家都還能聽懂。這也是沾了洛陽地處中原,曾經長時間做“首都”的便宜。不像南方有些地方話,差不多相當于一門“外語”,外地人休想聽懂。
深圳匯聚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方言自然五花八門,說是個小“聯合國”也不為過。來自同一地方的人聚到一起,就會嘰里呱啦、旁若無人地用家鄉話聊天,外人對此也不會有意見。誰讓人家是老鄉呢!老鄉見老鄉,說兩句家鄉話,再正常不過。
原以為,粵語應該是在深圳最常聽到的地方話,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我周圍就很少有人講粵語。幾個廣東籍同事,他們似乎從未用粵語交流過。后來,我才知道這幾位廣東籍同事都是客家人,“客家話”才是他們的地方話。
這下我來了勁。客家人是古時候從中原南遷而來的,偃師前兩年還建了一座“客家人南遷紀念碑”;客家話和洛陽話之間有很多的淵源……這些情況我是知道的。于是,我開始和這些客家同事“套近乎”,向他們瞎謅些“五胡亂華,漢人南遷”的事,以說明客家人“根在河洛”,小小地滿足一下我的地域自豪感。
有次,我在網上看到個帖子,用洛陽方言表達一些語義,諸如“有一種同行叫廝跟著”“有一種孤單叫獨孤眼兒”。看后我覺得很精彩,立馬粘貼給客家同事們看,以為這些純正的洛陽方言,應該和客家話有諸多相似。沒想到他們看后,說只有“有一種吵鬧叫嘰喳”的說法與他們相同,頗讓我大失所望——這個算相同嗎,“嘰喳”的說法普通話里也有用啊!
我還開玩笑讓他們用客家話背古詩,不過仍很遺憾,他們的客家話,我真聽不出和洛陽話有多少相似。客家人來到南方,歷史已經太久,語言自然不斷變化。不同地區的客家話之間,差異就很大,客家話與數千里外的洛陽話大相徑庭,也很正常。
扯得有點遠了。拿有歷史淵源的客家話和洛陽話說事,只想表明這么個意思:“十里不同音。”不同的地方有各自的地方話,太正常自然不過。
所以,最牛還是深圳。深圳沒有地方話,如果非要找一種,那普通話就是“深圳話”。普通話講不好,也沒關系,只要講話能讓人聽懂,就成。深圳,就是這么寬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