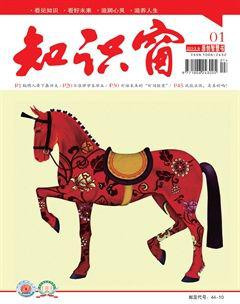我不想太早成名
青青子衿
他是江蘇興化人,早在1994年,他寫的電影劇本《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就被大導演張藝謀搬上了銀幕,并先后獲得了第49屆戛納電影節及美國金球獎最佳攝影獎、1995年全美影評人協會最佳外語片獎等,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巨大的反響。
憑借張藝謀三個字,他就能賺足眼球,可他卻選擇了沉默。著名主持人楊瀾曾問他道:“借這個事推一下自己,有什么不好呢?張愛玲不是也說出名要趁早嗎?”
他回答:“不知道,那時我還沒讀到過這句話。”
楊瀾大為驚訝,說:“你那時候還不知道張愛玲說的這句話嗎?這么有名。”
他說:“不知道,但這不是最重要的。”
楊瀾說:“你是覺得如果要是借助了這些大導演的名頭,是對自己的一種辱沒嗎?”
他說:“是的,極不得體。對我來講,我不想借助于任何人,我得靠我自己的作品,一個一個把自己寫出來。”
這樣的想法,放在如此浮躁的社會里,的確讓人難以理解。他卻覺得理所應當,在此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他都拒絕任何采訪,也一直很少談及他編劇的這部影片。他甚至逃離了人們的視野,跑到浙江斗門鎮扎根農村。
這里是一個暮氣沉沉的村子,除了老人和孩子,沒有一個青壯年。在一個寬敞的院子門口,他看到一個很老很老的老太太,一個人坐在門檻上。他試圖用普通話跟她聊天,她聽不懂,就使勁盯著他看,臉上特別自豪,然后用手指了指家里面的一個空屋子,跟他講她有五個兒子,他也聽不懂。大概重復了十幾遍之后,他才從她伸出的五個手指頭意會了老太太的意思,這是他聽懂的第一句紹興話—五個兒子,她就是想告訴他,她有五個兒子,她其實不是一個孤獨的老人,她很幸福。可是在剎那之間,他的心酸了,同時也激起了他創作的欲望,他要寫出空村的疼痛。
兩年后,《哺乳期的女人》問世了,并很快被《作家》雜志發表,這給了他很大的鼓勵,也更加堅定了他內心的信念。那個時候,與他年齡相仿的余華、格非、蘇童等作家早已成名,而他對自己的告誡就是要有耐心。看著有人接二連三地出書,他無動于衷;也有出版社向他約稿,寫一部鄭和下西洋的書,開的價格也很高,他想都不想就回絕了,因為這不是他熱愛的東西。他最熱衷的是疼痛的社會現實,是現代人的情感焦慮、生存疼痛。
他的文學創作沒有絲毫的功利心,為了避開浮躁的社會環境,他停掉了手機,雖然幾十個好朋友送的手機在家閑置,但他就是不想用,他覺得用手機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只是一種時間上的額外開銷,用手機時,接到的大多數電話都是找他吃飯和玩樂的,跟他的寫作沒有任何關系。他不喜歡應酬,也不大參加飯局,只是愿意享受寫作這樣一種永遠安定的生活。
他癡迷各種文字,有時可以宅在書房里好幾天,也會為了一個題材,轉悠半個城市,跑遍一些特定人群所在的角落。他一旦進入寫作狀態,便寢食俱廢,狀態非人。寫作一部長篇小說期間適逢春節長假,父母來南京與他團聚,結果全家過了一個小心翼翼、躡手躡腳的春節—連他當時只有四歲的兒子都知道不可以碰書房的門。事后作為情感補償,他專門請假陪同父母妻兒去浙江旅游了一趟。
他的生活很有規律,也很簡單,除了運動、聽京劇、品咖啡就是寫作。閉關十幾年,其中有苦也有樂,過得踏實也過得緊張,有一些他人所不知道的精彩,也有他人所不知道的困難和沮喪。但不管怎樣,他必須這樣走過,因為寫作對于他來說就是一個一個日子,跨不出去,也離不開,而這樣的生活回饋給他的是一部又一部的作品。
憑借著自己對社會現實的深刻理解,他把國內的文學大獎幾乎都拿了個遍,魯迅文學獎獲得了兩次,2010年憑借《玉米》獲英仕曼亞洲文學獎,他的小說也被翻譯成多國文字。2011年,他的長篇小說《推拿》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2013年被改編成電視劇和話劇。
他就是畢飛宇,一個帥帥的作家,一條牛仔褲,一件條紋衫,標志性的寸頭。他說:“我覺得寫作就像是植物上長葉子,而得獎則是植物上開花時飄出的芬芳,首先是要長好,飄出芬芳可以不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