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田采出水預處理工藝技術優化
馬志榮 祝守麗 傅俊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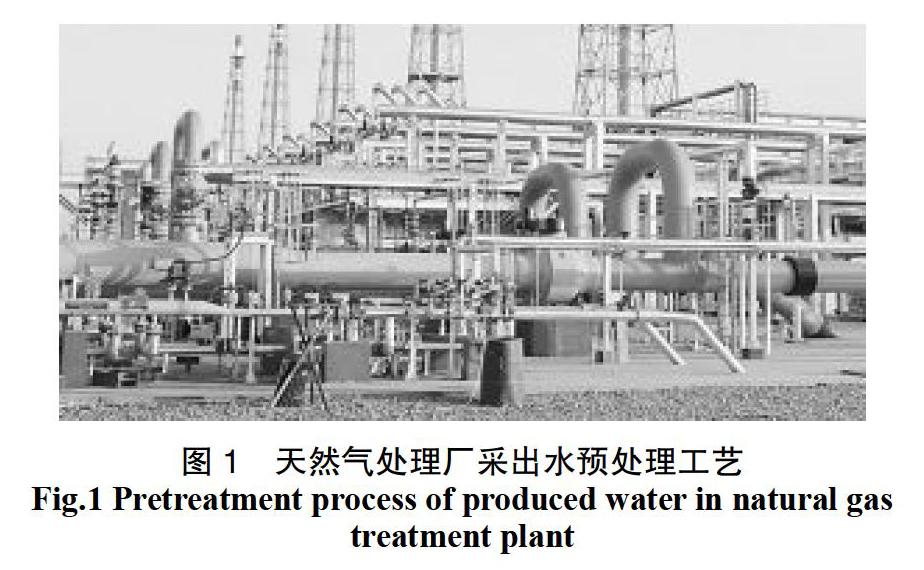
摘 ? ? ?要: 針對氣田處理廠采出水預處理工藝整體運行效率不高,甲醇回收系統腐蝕嚴重,注水管線污泥堵塞明顯等問題,對采出水預處理工藝技術進行了優化改進。通過延長采出水在卸車池及原料水罐中沉降時間,使采出水中油水充分分層,必要時添加破乳劑,進一步將采出水中油分分離。冬季在管道混合器或在反應罐外壁增加伴熱,或安裝可加熱型管道混合器,對液體進行適當加熱,采出水與藥劑混合充分均勻,充分發揮藥效,防止絮體過快析出,從而提高沉降效果。并提出了相關的工藝優化及改進措施,為采出水預處理工藝提供借鑒。
關 ?鍵 ?詞:采出水;水處理;混合器;水質分析
中圖分類號:X 741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1671-0460(2019)12-2836-04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of low overall operation efficiency, serious corrosion of methanol recovery system and obvious sludge blockage in water injection pipeline, the pretreatment process of produced water in gas field treatment plant was optimized and improved. By prolonging the settling time of produced water in the unloading tank and raw water tank, the full stratification of oil and water in the produced water can be realized. If necessary, adding demulsifier can further separate the oil from the produced water. In winter, heat tracing should be used in the pipe mixer or on the outer wall of the reactor tank, or a heated pipe mixer should be used to properly heat the liquid, and the produced water should be fully and evenly mixed with the medicament, preventing the flocs from quick precipitating, thus improving the settlement effect. The relevant process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etreatment process of produced water.
Key words: Produced water; Water treatment; Mixer; Water quality analysis
天然氣開采過程中,隨著氣田不斷深入開發,氣藏壓力降低,地層水逐漸浸入氣藏隨著天然氣一同被采出;同時,為了增加天然氣產量,氣田大量采用排水采氣工藝,使得氣田采出水產量劇增。由于天然氣與水容易形成水合物,在天然氣集輸系統中,導致管線流通面積減小進而導致管線堵塞[1]。為了抑制水合物的形成并降低水合物的冰點,通常在天然氣采氣井口或集輸管道噴注有機抑制劑,甲醇是最常用的一種。注入管道的甲醇與天然氣混合,經過集氣站過濾分離,進而產生了氣田含醇污水。
氣田采出水經過從天然氣集輸到初加工的整個過程,具有成分復雜、雜質種類多的特點[2]。不同地區不同季節氣田采出水成分不同,由于采出水吸收天然氣中的二氧化碳、硫化氫等呈酸性,并含大量的懸浮物、凝析油、礦物質、機雜等,對管線、設備等具有腐蝕性[3,4]。若不經過預處理,會使甲醇回收精餾塔操作困難,生產甲醇合格率低,同時會導致管線腐蝕、設備堵塞、結垢、裝置運行不平穩等問題,塔底廢水含醇率高回注時會污染環境。為降低采氣成本及減小甲醇對于環境的污染,將采出水中甲醇回收再利用,故需對氣田采出水進行一系列的綜合處理[5]。
1 ?采出水預處理現狀及存在問題
1.1 ?采出水預處理現狀
氣田采出水預處理是指氣田采出水通過污水車卸至卸車池至采出水進甲醇回收裝置前的流程,主要去除采出水中的凝析油、固體機雜、導致設備管線腐蝕結垢離子等的一個物理化學過程[6,7]。具體流程如下:氣田采出水從集氣站拉運至天然氣處理廠,首先進入卸車池,在卸車池進行沉降,初步進行油水分離,污油進入地埋轉油罐。污水經過污水提升泵轉到原料水罐,靜置12 h使油水有效分層,進行二次油水分離,污油通過排油管線再次排至地埋轉油罐,污水通過轉水泵去原料水罐,轉水過程中利用汽水混合加熱器對原料水進行加熱,加熱至25~30 ℃左右,注入壓力式除油器進行油水分離。污油進入地埋轉油罐,除油后的污水與藥物(pH值調節劑、混凝劑、雙氧水)通過管道混合器進入反應罐內充分混合,再加入助凝劑、絮凝體,污水和藥劑反應后進入原料水罐進行絮凝沉降,除去機雜和污油后的采出水通過給料泵送入甲醇回收裝置進行精餾分離。在此過程中,進入地埋轉油罐的污油由轉油泵輸送至原油儲罐,去凝析油穩定裝置變為成品凝析油(圖1)[8]。
靜態混合器的規格可以根據需求來進行選擇,在選擇時應明確混合器的型號、材質、公稱直徑及壓力等參數。在一些場合由于溫度過高或過低、反應過程中需吸熱或放熱,為解決之一問題,在原有的靜態混合器的基礎上帶上夾套,如由啟東恒業石化冶金設備有限公司生產的HYVF型混合器即為帶夾套混合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來選擇尺寸規格。
(2)HTF型強化傳熱混合反應器。其內部結構與靜態混合器的類似,可以使流體充分混合,內部有較細的管束,可以通加冷/熱換熱介質,既能夠起到混合的作用,還能提供很大的傳熱比表面積。HTF-I型強化傳熱混合反應器可直接與管道相連,不需要與其他配件結合使用,對于高粘度的流體的混合及傳熱有較好的效果。HTF-I型的特別適合用于聚合反應器,能使進入管道的流體很好的混合,還能強化傳熱過程。
其它類型混合器。除過以上列出的常用的混合器之外,還有一些其它類型的混合器,SK型、SL型列管強化換熱器,JLF型靜態混合器式換熱器等被用到熱交換場合的混合、溶解、反應過程。SK型、SL型列管強化換熱器是在管殼式換熱器的列管中裝入SK或SL的單元,這樣會形成許多SK型靜態混合器并聯的結構,在使用過程中可同時達到物料混合及傳熱。
2.2.4 ?靜態混合器的應用
(1)靜態混合器在石油化工中的應用。靜態混合器在石油化工主要用于油品的調和、原油脫鹽與脫蠟、萃取等工藝。油品的調和主要有燃料油調和、潤滑油調和以及瀝青的調和,即根據國家標準對石油產品的特性(如密度、辛烷值、十六烷值等)進行調和,使之達標。將管道混合器引入到瀝青的調和中,相對于原始的機械攪拌的方法,其混合效果更佳。蠟含量是評價原油的一個指標,利用靜態混合器分離油蠟具有高效、耗能低等優點。江漢油田含鹽量高達16×104 mg/L,在使用靜態混合器之后含鹽量降到了188 mg/L,由此可以得出混合器在原油脫鹽方面有著較好的效果。在萃取過程中,兩相混合比較困難,采用混合器能是兩相充分混合,提高萃取效率,上海高橋石化公司煉油廠使用靜態混合器替代文丘里管后,提高了油品收率,降低了能耗。
(2)靜態混合器在醫藥領域的應用。在醫藥學領域中,管道混合器可以用于混合、乳化、萃取、化學反應等過程。在醫藥學中,靜態混合器被用于不易互溶的液體,特別是黏度較高的流體之間的混合。肖林久在硝化實驗中將靜態混合器與傳統釜式反應器進行了對比,能耗降低了33%~50%。并由于靜態混合器封閉性好,適合于有毒,易燃等危險的反應,安全系數高。
(3)靜態混合器在環保領域的應用。廢水是污染環境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處理廢水時會加入一些絮凝劑、助凝劑等溶劑,在初期使用機械攪拌法,由于混合不均勻處理效果差,在使用了混合器之后效果明顯提高,聚合氯化鋁是處理廢水常用的絮凝劑,由于在絮凝過程中絮體的顆粒小,因此會添加助凝劑,常用的為聚丙烯酰胺,經調查,上海怡中紡織公司在處理廢水時用到了SVL型靜態混合器,取得了理想效果。上海染化二廠生產碳酸二苯酯時會產生含酚污水,在廢水處理中,用靜態混合器代替脈沖萃取塔,廢水處理量從12 t/d提到了30 t/d,并且水的含酚量從523.3 mg/L降到了43.3 mg/L,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3 ?現場管道混合器優化改進
經過對“管道混合器”的文獻和市場調研,建議處理廠對原有的管道混合器安裝加熱裝置或更換為加熱型管道混合器。可以考慮以下類型管道混合器:
(1)靜態混合器。靜態混合器安裝不受限制,可根據具體需求水平或垂直安裝,其混合單元前的加藥管道可由用戶自己設計。藥劑混合效率能夠達到90%以上,對于提高污水處理效果具有重大意義。
(2)HYVF型混合器。在一些場合由于溫度過高或過低、反應過程中需吸熱或放熱,為解決該問題,在原有的靜態混合器的基礎上帶上夾套,如由啟東恒業石化冶金設備有限公司生產的HYVF型混合器即為帶夾套混合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來選擇尺寸規格。
(3)HTF型強化傳熱混合反應器。
3 ?采出水預處理工藝優化及建議
采取以下控制手段進行有效的處理:
(1)延長采出水在卸車池及原料水罐中沉降時間,使采出水中油水充分分層,必要時添加破乳劑進一步將油分分離出來。
(2)通過水質分析發現反應罐的pH值并未達到預期的7.5,造成此結果有兩種可能性,一為NaOH加量不足,二為原料水和反應藥劑混合不均所致。針對該問題,建議嚴格執行加藥制度,并定時檢測水質pH值。由于采出水和反應藥劑不能充分混合,建議立式反應罐更換為多級渦流反應沉降罐,渦流反應沉降罐采用多級渦流方式,在罐內通過多級渦流,微小漩渦數量增加,各種微粒碰撞次數大大增加,有助于采出水與藥劑的充分混合。通過微小漩渦凝聚和立體接觸絮凝,可大幅度提高反應速率,提高絮凝效率。
(3)嚴格保證加藥絮凝沉降時間,以便于采出水在原料水罐總充分絮凝沉淀。
(4)由于采出水中鐵離子含量較少,可通過對反應溫度、攪拌速率、沉降時間、加藥順序、加藥量等加藥處理工藝的優化來提高除鐵率。
(5)冬季在管道混合器或反應罐處增加伴熱,或安裝可加熱型管道混合器,對液體進行適當加熱,防止絮體過快析出,從而提高沉降效果。
4 ?結 論
將立式反應罐更換為多級渦流反應沉降罐,進一步加強采出水與藥劑混合效果(渦流反應沉降罐采用多級渦流方式,在罐內通過多級渦流,微小漩渦數量增加,各種微粒碰撞次數大大增加,有助于采出水與藥劑充分混合),通過微小漩渦凝聚和立體接觸絮凝,可大幅度提高反應速率,提高絮凝效率。
參考文獻:
[1]蘇碧云,黃力,李善建,李曉曼.氣田含醇污水預處理工藝參數優化[J].石油化工應用,2018,37(11):21-24.
[2]王莉娜,王春輝,種法國.低滲透油田采出水OD-MBR生物膜處理技術研究[J].石油和化工設備,2018,21(8):103-105.
[3]王濤.青化砭采油廠采出水處理工藝適應性分析[J].中國給水排水,2018,34(7):85-88.
[4]黃曉英,郝堅,革曉東.氣田采出水揮發酚預處理消泡方法探討[J].油氣田環境保護,2017,27(5):54-56+62.
[5] 陸爭光,高鵬,馬晨波,等.頁巖氣采出水污染及處理技術進展[J].天然氣與石油,2015,33(6):90-95+14.
[6]王娜,張昆,趙麗麗,徐東,趙軒剛,馬連偉.氣田采出水處理裝置運行參數標準化[J].石油化工應用,2014,33(7):110-113.
[7]朱鋆珊,馬平,郭麗.膜分離技術及其應用[J].當代化工,2017,46(6):1193-1195+1199.
[8]闞連寶,段輝,丁思棋,等.電化學技術在有機廢水處理中的應用和展望[J].當代化工,2016,45(5):952-953+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