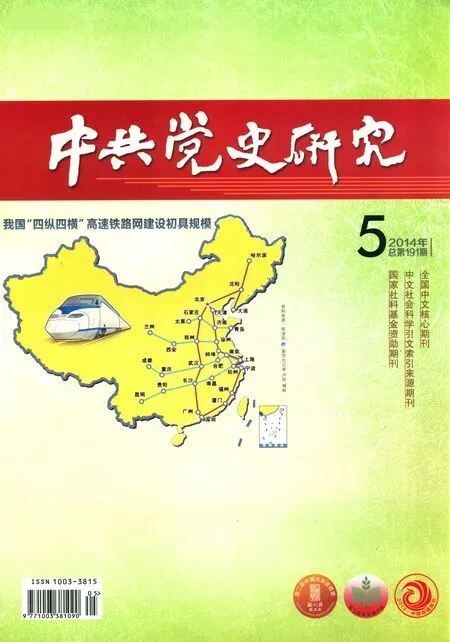中國對法政策調整與富爾一九六三年中國之行*
姚百慧
(本文作者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北京 100089)
中法于1964年1月發表的建交公報,曾被媒體喻為“外交核爆炸”。中法建立外交關系,不僅促進了兩國關系的發展,也挑戰了美蘇把持的兩極格局,沖擊了當時的國際秩序。中法建交的實際過程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63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 (Edgar Faure)受命訪華同中國領導人的一系列會談;第二階段是中法兩國代表在瑞士首都伯爾尼進行的正式建交談判。關于這兩個階段的關系,當時的中國駐瑞士大使、中方談判代表李清泉在回憶錄中曾這樣總結:“瑞士談判是北京會談的繼續。北京會談中,周總理、陳毅副總理親自解決了中法建交的實質性問題、原則問題。瑞士談判只是解決了中法建交的程序問題、方式問題。”①李清泉:《中法建交談判回顧》,黃舍驕主編:《春華秋實四十年——中法建交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第59頁。雖然富爾不是正式的總統特使,富爾訪華期間的會談也不是正式的官方談判,但這些會談在整個中法建交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深入細致地加以研究。
學術界對中法建交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比較全面地勾勒中法建交的全過程②代表性的著作有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第161—162頁;張錫昌、周劍卿:《戰后法國外交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第219—234頁;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361—372頁;福田園:《中法邦交正常化(1964年)和“一個中國”原則的形成——法臺斷交和圍繞“唯一合法政府”的交涉》,〔日本〕《國際政治》,第163號 (2011年1月);翟強:《從隔閡到建交:一九四九到一九六四年的中法關系》,《中共黨史研究》2012第8期 。;第二,從法國外交的角度,研究戴高樂同中國建交的意圖①代表性的著作如 Garret Martin,“Playing the China Card?Revisiting France’s Recognition of Communist China,1963—1964”,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Winter 2008,Vol.10 Issue 1,pp.52-80;Thi Minh-Hoang Ngo,“De Gaulle et l’unité de la Chine,”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n°4(1998),pp.391-412;張家展:《第五共和國時期的戴高樂與中國》,《法國研究》1991年第2期。;第三,從中國外交的角度,研究中國對法政策及中法建交過程中中國領導人的作用②代表性的著作如姚百慧:《中法建交談判中關于臺灣問題的“三項默契”—— 〈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形成考釋》,《當代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2期;姚百慧:《〈中法建交公報〉形成考釋》,《當代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2期;曲星:《試論毛澤東關于中法關系的戰略思想》,裴堅章主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239—255頁;王文博:《從中法建交談判看周恩來對西歐國家的外交政策思想及其談判藝術》,《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第246—247頁;高長武:《周恩來與中法建交的幾個關節點》,徐行主編:《二十一世紀周恩來研究的新視野》(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218—1227頁。;第四,研究美國、臺灣對中法建交的反應③代表性的著作如潘敬國、張穎:《中法建交中的美臺因素》,《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3期;翟強:《美臺對中法建交的反應 (1963—1964)》,《史林》2013年第2期;姚百慧:《論美國與中法建交的關系》,《世界歷史》2010年第3期;蘇宏達:《“一個中國原則”與“兩岸國際共存”并行的可能性評估——以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中華民國對法國外交政策為案例研究》,《美歐季刊》(臺灣)2000年春季卷;許文堂:《建交與斷交——1964年臺北、巴黎、北京的角力》,黃翔瑜主編:《戰后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8年,第159—200頁。。上述成果均涉及富爾1963年的中國之行,但都著墨不多④姚百慧:《中法建交談判中關于臺灣問題的“三項默契”—— 〈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形成考釋》,《當代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2期,但該文著重考察的是富爾訪華期間形成的關鍵文件《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的形成史,對富爾訪華前中方戰略及政策調整、訪華期間詳細談判情況等均沒有深入討論。除了上述這些學術研究成果外,還有一些紀實文學類的作品涉及中法建交問題,如柴成文等編:《三大突破:新中國走向世界的報告》,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張錫昌等編:《峰巒迭起:共和國第三次建交高潮》,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陳敦德:《破冰在1964——中法建交紀實》,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7年。從史料基礎上來看,這類作品不宜引用。,也沒有將此同中國的外交戰略、對法政策調整聯系起來。
鑒于富爾之行的重要作用以及學術界的研究現狀,本文擬以中國外交部檔案為基礎,從中國外交的角度,考察中方外交戰略調整與對法政策之間的關聯,以及富爾訪華期間同中國領導人的歷次會談詳情,并簡論富爾訪華成行與成功的原因。
一、中國對法美矛盾的觀察與“第二中間地帶”理論的提出
新中國剛剛成立,法國政界就開始醞釀承認問題。在內部討論和公開發言中,法國外交部都認為,承認新中國是“不可抗拒的” “不可避免的”⑤〔法〕史曼慈:《法中關系的法律基礎——法國對新中國的承認》,鄭秉文、馬勝利主編: 《走進法蘭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44—45頁。,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建交問題均未被兩國提上正式日程。究其原因,固然有朝鮮戰爭、越南問題、阿爾及利亞問題、臺灣問題等具體原因,但其根本還在于兩國都沒有擺脫美蘇兩極格局束縛的愿望。法國的態度,正如1955年7月法國外長安托萬·比內(Antoine Pinay)在參議院回答議員質詢時明確表示的:同中國建交“必須由西方國家共同決定”,法國“將考慮美國的態度”⑥《中法關系簡況》(1955年10月21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0148-35。。而作為社會主義陣營之一員的中國,也把歐美相提并論,在打擊“美帝”的戰略前提下,很少考慮發展同法國等西歐國家的外交關系問題。
20世紀50年代末國際格局從戰后初期的兩極格局逐步向多極化態勢演進,美歐矛盾和中蘇分歧的加劇,成為推動這種態勢的重要力量。與此同時,中國外交戰略開始有了一個較大的變化,從“一邊倒”、集中力量孤立和打擊美帝逐步轉變為反對美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反帝必反修)。由于當時西歐表現出更多的對美獨立姿態,中國開始把美歐區分開來,把西歐地位提高到在國際反帝反修斗爭中“間接同盟軍”的戰略地位,日益重視和發展同西歐國家的關系,并重提“中間地帶”的概念⑦關于中國的外交戰略調整,參見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2卷,第360頁。。這一概念最早是毛澤東在解放戰爭初期提出的,以指美蘇之間的“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59頁。。提出這一概念的主要目的,是為聯蘇反美作鋪墊。它實際上是后來“一邊倒”方針的理論支撐②劉建平:《“中間地帶”理論與戰后中日關系》(上),《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5期。。但20世紀60年代重提的中間地帶,內容發生了重大變化。具體而言,將中間地帶區分為兩部分: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是第一中間地帶;西歐、加拿大、日本等是第二中間地帶。在反對美帝蘇修的斗爭中,對這兩個中間地帶都要爭取。1963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曾概括說:“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日本、加拿大對美國是不滿意的。以戴高樂為代表的,有六國共同市場,都是些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東方的日本,是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美國不滿意。對蘇聯也不滿意。東歐各國對蘇聯赫魯曉夫就那么滿意?我不相信。情況還在發展,矛盾還在暴露。過去幾年法國人鬧獨立性,但沒有鬧到今天這樣的程度。蘇聯與東歐各國的矛盾也有明顯發展,關系緊張得很。”③《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05—506頁。
對于“第二中間地帶”理論,學術界已有很多研究。但有一點仍需指出,這一理論的形成,除了上述的中蘇分歧、美歐矛盾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對美法矛盾的觀察。分析和利用美歐矛盾,一直是新中國的基本外交策略之一。在這當中,中國高層尤其注重觀察和利用美法關系,尤其是戴高樂與美國的關系。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期間,毛澤東就曾召集參加八大的使節集體談話,要求大家抽時間讀《戴高樂回憶錄》④戴高樂的《戰爭回憶錄》此時已出版2卷,第1卷《召喚 (1940—1942)》出版于1954年10月,第2卷《統一 (1942—1944)》出版于1956年8月。這兩卷揭露了大量戴高樂與美國的矛盾沖突情況。。毛澤東指出:“這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其中有很多提法很有意思。例如,戴高樂承認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是‘大魚吃小魚’……戴高樂有獨立性,在一些國際問題上,他不同意美國的一些觀點和做法,不愿意讓美國牽著自己的鼻子走,也不愿意讓法國聽從美國的控制和擺布。”⑤孔祥琇:《耿飚傳》(下冊),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第47頁。1958年法國政局變動,戴高樂于當年6月再次執政。由于他之前經常為法國的海外殖民政策辯護,強調君主制的作用,并積極推動冷戰,輿論開始認為這是歐洲政局右轉的表現。中國的一些國際問題專家也持有類似的看法,一家有影響力的刊物甚至斷言,戴高樂上臺就是法西斯上臺。但毛澤東認為:戴高樂的民族意識、民族精神很強,始終強調國家的尊嚴和獨立,不依傍他人;他主張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反對大國的霸權,頗具獨立見解;他的當政,對歐洲擺脫美國的控制、推動歐洲中立主義的發展、改變世界格局,將會產生極大影響。8月在同來訪的赫魯曉夫談話中、9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反復強調了類似的看法。⑥《毛澤東政治秘書林克的回憶》,李靜主編:《實話實說豐澤園》(下冊),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372頁;《赫魯曉夫與毛澤東的會談記錄》(1958年8月1日),華東師范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藏:《俄國檔案原文復印件匯編:中蘇關系》第20卷,第11—40頁;《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45頁。
中國對法美矛盾分析變動的過程,還需要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但基本可以判定:從1958年到1962年,中國認為法美矛盾不斷深化、不斷發展;至少在1962年中旬,已認定法美矛盾已經激化。1962年6月外交部擬定的報告認為,自戴高樂重新上臺以來, “法美矛盾有很大發展”。法國堅持把歐洲六國發展成“一個反蘇抗美的第三種勢力”,發展獨立的核威懾力量,反對美國獨霸大西洋集團的領導權;而美國則力圖維持對歐洲的控制,最近“越來越露骨地”分化歐洲各國與法國的關系,孤立和壓制法國。這些使法美矛盾“更加尖銳”,“并已成為西方陣營內部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⑦《法國前總理富爾訪華的有關請示及中央的批復 (邀請來訪建議、富爾簡歷、來訪及接待方針指示、工作建議)》(1962年6月15日至1963年10月1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16。1963年初,由于戴高樂拒絕多邊核力量計劃、否決英國加入歐共體的申請、布魯塞爾談判破裂以及《法德友好合作條約》簽訂,這一連串歐美摩擦事件的發生,使中國開始認為“帝國主義集團加速走向四分五裂”,而法美矛盾是其主要矛盾。中國駐瑞士使館的1962年專題總結分析,這些事件“標志著帝國主義陣營內部四分五裂的趨勢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在當前內部你爭我奪、互爭長短的劇烈斗爭中,法、美之間的斗爭表現得最為突出和尖銳,法美矛盾在帝國主義陣營內部矛盾中占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中國駐瑞士使館還特別提高了法美矛盾的戰略意義,“法美尖銳的斗爭,在某種意義上,對美國推行獨霸全球的新戰略,起著某種牽制作用。其意義不僅限于帝國主義內部關系上,而且影響帝國主義同東方的關系,關系到殖民地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①《我駐瑞士使館報回對開展對法國工作的意見》(1963年3月26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4-03。
正是很大程度上基于對法美矛盾及其戰略意義的認識,中國高層提出了“第二中間地帶”理論。毛澤東在同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理事長安井郁的談話中指出:“社會主義陣營算一個方面,美國算另一個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間地帶。但是中間地帶國家的性質也各不相同:有些國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國;有些國家被剝奪了殖民地,但仍有強大的壟斷資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國家取得了真正的獨立,如幾內亞、阿聯、馬里、加納;還有一些國家取得了名義上的獨立,實際上仍然是附屬國。中間地帶國家各式各樣,各不相同,但美國統統想把它們吞下去。”“法帝國主義對阿爾及利亞人民來講不是同盟者……對非洲來說,英國、法國、比利時、葡萄牙不是朋友。可以利用的一點是,它們同美國有矛盾。”②《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87—488頁。后來,毛澤東又進一步提出,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為第一中間地帶,英、法、西德、日本、加拿大等資本主義國家為第二中間地帶。但在這些第二中間地帶國家中,也只有法國同美矛盾異常尖銳,從而最有可能成為中國的“間接同盟軍”。
可以說,到1962年中旬,中國已經完成對法政策調整的戰略準備,剩下的就是在具體政策上如何推動中法關系的發展了。
二、“抓緊目前時機,對法多做些工作”
從1961年初開始,在同法方有關人員的接觸中,中國領導人開始有意強調要發展兩國關系。1961年2月8日,毛澤東在接見來訪的法參議員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ois Mitterrand)時強調,中法之間沒有外交關系只是“暫時現象”③《毛澤東主席會見法國參議員密特朗的談話記要》(1961年2月8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7-00972-06。。1961年6月和1962年7月,在關于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期間,陳毅多次向法國外長莫里斯·顧夫·德姆維爾 (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探詢,中法關系是否可以改善?德姆維爾稱,目前兩國的經濟來往不錯,文化交流較少,可考慮加強,外交關系可隨時間解決。④《一九六一年日內瓦會議期間陳毅副總理出席法國外長德姆維爾宴會談話紀要》 (1961年6月16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389-03;《要求我駐瑞士使館研提開展對法工作意見 (與我駐瑞士使館有關往來電)》(1962年6月22日至11月8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123-01。
雖然法國對發展同中國的外交關系持謹慎態度,但中國駐瑞士使館基于對美法矛盾的判斷,提出“對法工作應采取較積極較主動的方針”,“以利于區別對待美、英、法、西德集團,充分利用它們的矛盾,特別是法美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美帝”,“從更好貫徹我外交政策總路線出發有此必要,而從目前法美矛盾和法對我態度來看是有可能的”⑤《我駐瑞士使館報回對開展對法國工作的意見》(1963年3月26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4-03。。中國駐瑞士使館的上述看法很有代表性,當時中方的一般認識是,發展中法關系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但在估計中法關系會發展到何種程度上,中國有關人士是存在分歧的。以新華社駐巴黎分社記者陳定民為代表的一種觀點認為,中法建交的時機已經成熟。1963年1月21日,他給陳毅副總理兼外長寫了一封長信,指出:由于戴高樂政府在國內得以穩定,在國外繼續對美鬧獨立,“估計戴政權面臨國內外形勢,與我建交利多弊少,積極因素正在不斷增長,時機已比較成熟”,如中國在外交上“稍采主動”,“促進建交的可能性很大”。但這封信并未受到及時的重視,直到3月4日,陳毅才批示:“姬鵬飛同志 (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引者注):請研究一下,如果向法國試探一下建交問題,是否有可能?可否寫一個報告給我,以便轉中央”。根據陳毅的指示,外交部先在西歐司研究,提出意見,并在黨委討論。西歐司在討論后認為,中法建立正式關系的“可能性不大”,但“利用當前時機設法改善一些中法關系,對分化法美和開展我對法工作是有利的”,“試探建交不一定就要建交,但可以起推動法國改善兩國關系的作用,因而是可行的”,并提出了一些試探建交的具體途徑。3月12日,外交部部長助理喬冠華批示:西歐司的這個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對于試探建交,不宜由我采取主動”,“而應等待對方有一定跡象時再搞,搞早了反而顯得我們急”,應該首先看看法國是否有這個打算。最終,陳定民的信及西歐司關于試探建交的建議并未上報。由此表明,外交部的主流思想是:“目前戴高樂對華作法還是著重開展對華貿易,適當進行一些科技文化往來,尚無進一步發展兩國政治關系的打算。”①《陳毅副總理對我巴黎新華社分社記者陳定民建議爭取與法國建交信件的批示 (陳定民信)、我對向法試探建交的意見 (未上報)》(1963年1月21日至3月9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4-02。
無論是積極的估計還是消極的估計,進一步發展中法關系已成為共識。1963年2月6日,外交部依據消極的估計,擬就《關于當前開展對法工作的請示》報請批示。請示稱,在法美矛盾“空前尖銳”的情況下, “我們可抓緊目前時機,對法多做些工作”。具體建議有:(1)“我駐瑞士使館可采取主動恢復同法駐瑞士使館參贊級個人接觸……并逐步發展為大使級的私人接觸”;(2)“增強巴黎新華分社的工作”,“可考慮盡快增派一活動能力較強、政治水平較高的干部以記者名義常駐巴黎,主要做法國政界和法共左派的工作”;(3)“法方去年多次向我提出簽訂半官方貿易協定……我駐瑞士使館商務處可同法商務參贊就此進行商談”;(4)“即著手邀請少數接近戴高樂而又對我友好的政界人士訪華”,初步考慮的對象有富爾、埃德蒙·密歇勒 (Edmond Michelet)②老牌戴高樂分子,曾任戴高樂臨時政府國防部部長,戴再度上臺后曾任司法部部長等職,1962年4月政府改組后因內部矛盾未參加政府。1955年曾率領議員代表團訪華,多次公開主張承認中國。、雷納·加比唐 (René Capitant)③原法蘭西人民聯盟全國委員會主席,當時為親戴高樂的“勞工民主聯盟”領導人之一,任國民議會憲法法律委員會主席,1960年訪華,對華態度友好。三人;(5)“對法政界經濟界人士要求訪華者,可適當放寬。對有一定地位的法國人士訪華,我有關單位可主動作些工作。”(6)“法航空公司同我民航簽訂聯運代理合同事,外辦已原則同意,可考慮早日簽訂。”3月8日,周恩來批示:關于第三條,目前法國對發展貿易“有些顧慮”,中方正擬訂購糧食、機械設備“進行試探”, “待有結果時,再作進一步處理”;關于第四條,“此事須看對方有無要求或暗示,不要強求”。除了第三、四條的這些修改,“擬同意”,送毛主席等核閱后退外交部辦。關于第二條,周恩來還轉達劉少奇的意見,新華社駐巴黎分社“可多做些報道和翻印我反修文章的工作”。④《關于開展對法國工作的請示及中央的批示、給我駐瑞士使館就開展對法工作的指示電》 (1963年2月6日至3月1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4-01。
上述報告和周恩來的批示,表示中方態度仍是謹慎的,沒有把同法建立正式外交關系提上日程。從第三條關于簽訂半官方貿易協定的問題看,中方對發展半官方的關系也是猶豫的。《請示》明確說,圍繞簽訂半官方協定進行商談“有利于爭取法國”,但“至于協定最終是否談成,可視以后的政治氣候和具體貿易條件而定”。周恩來對此條提議和邀請法政界人士提議的批復,顯示了中方對中法關系能夠發展到什么程度,還沒有明確的預測,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在這種情況下自然不宜過分采取主動。在接到周恩來的批示后,外交部除了將發展貿易這條留給外貿部辦理外,將另外五條于3月15日發給駐瑞士使館,請其研究執行。①《關于開展對法國工作的請示及中央的批示、給我駐瑞士使館就開展對法工作的指示電》 (1963年2月6日至3月1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4-01。
在隨后執行“三八批示”時,中國在兩方面加強了同法國的聯系。在經貿往來方面,批準了多起法國人員的訪華要求,1963年5月,外貿部副部長盧緒章赴瑞士訪問時又同法經濟界十大行業、32個集團的80多名有影響的人士進行了接觸。在外交人員往來方面,3月20日,中國駐瑞士使館王進參贊訪法國駐瑞士使館參贊高桑 (Gao Ssen)。高桑表示,他個人看不出中法有理由對立起來,但是,要有耐心,中法更正式地談兩國關系的這一天會到來的。他說:中國有不少代表團訪法,多系談貿易問題;在文化方面,也可做些事情。至于政治方面,他不認為他這一級人員可以談政治關系問題。法駐瑞士大使曾出席中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的招待會,法駐阿爾巴尼亞公使也多次主動同中方接觸。但在談話中,他們只對開展貿易有興趣,對兩國政治關系,不是避而不談,就是表示“要一點一點來”(法駐瑞士大使語)。②《西歐地區情況通報1—6期》 (1963年2月1日至12月2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550-02。
這些接觸加深了中方的印象:目前戴高樂的對華策略主要還是貿易往來,適當進行一些文化交往,尚無進一步發展兩國政治關系的打算。因此中方采取“等待”政策:如法外交官主動同中國駐外使館人員接觸或要求同中方建立聯系,可與其保持一般關系;在同法方接觸中,可主動做些工作但要注意避免使對方產生中方急于建交和有求于法的錯覺。③《西歐地區情況通報1—6期》 (1963年2月1日至12月2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550-02。
三、中法接近與富爾訪華之行的確定
1961年至1962年,隨著中國覺察到法美矛盾的升級,從利用法美矛盾和發展中法關系的角度出發,中方開始試探法方的態度。除了本文上述的一些行動外,外交部還提出了第一份具體建議,即1962年6月15日《關于邀請法國前總理富爾來訪的建議》。這份建議從戴高樂上臺后“法美矛盾有很大發展”的事實出發,提出“為擴大法美矛盾”,中方可采取一些措施,以“試探法國政府對我的態度,并施加影響”,“除擬囑我駐瑞士使館及駐法記者相機活動外”,該建議的核心是“邀請一個和戴高樂關系較密切、政治身份較高的政界人物訪華”。具體人選有兩個:一個是法國前總理富爾;另一個是獨立黨人、參議員羅希洛。外交部認為,“以上兩人,羅希洛的政治身份和與戴高樂的關系方面均不如富爾,可以富爾為第一對象。擬由我駐巴黎記者往訪,進行試探,如對方有意,再以外交學會名義發出邀請”。對于這份建議,陳毅于6月18日批示:“因要開日內瓦會議,此事到那里去相機而行,可以不必邀請富爾。”④《法國前總理富爾訪華的有關請示及中央的批復 (邀請來訪建議、富爾簡歷、來訪及接待方針指示、工作建議)》(1962年6月15日至1963年10月1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16。
外交部之所以把邀請富爾作為試探中法關系的重要舉措,與富爾的政治資歷、對華態度及其與戴高樂的關系有關。富爾曾在1952年和1955年兩度擔任法國總理,在多屆法國內閣中擔任部長級職務。富爾一向主張承認新中國,支持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57年5月至6月,富爾夫婦曾受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之邀,以私人名義在華訪問一個月,受到熱情接待。毛澤東接見他們,周恩來也同其多次交談,而且幾乎不受限制地讓他們走訪了許多地區。富爾對此非常滿意,訪華期間和訪華后,多次主張法中恢復正常外交關系。富爾回國后,借鑒毛澤東詩詞中的“龜蛇鎖大江”、“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等詩句的含義,寫了本《蛇山與龜山》介紹中國,主張中法建立外交關系。⑤Edgar Faure,Le serpent et la torture,les problèmes de la Chine populaire,Julliard,1957.富爾與戴高樂關系密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戴高樂臨時政府副秘書長;1958年戴高樂上臺前夕,富爾第一個表示公開支持。戴高樂曾在1960年召見富爾,商談遠東問題。據有的學者分析,富爾實為戴高樂“在中國問題上的半官方顧問”。①《法國前總理富爾訪華的有關請示及中央的批復 (邀請來訪建議、富爾簡歷、來訪及接待方針指示、工作建議)》 (1962年6月15日至1963年10月1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16;Thi Minh-Hoang Ngo,“De Gaulle et l’unité de la Chine,”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n°4(1998),p.395。
如前文所述,陳毅在日內瓦會議上向德姆維爾試探時,對方似乎對發展中法文化和貿易關系更感興趣。法國的態度影響了中國的判斷,邀請富爾來華的建議直到大半年后才再次被提出。1963年2月6日,外交部提交的《關于當前開展對法工作的請示》、3月西歐司提交的《對向法試探建交的意見》又把邀請富爾等人訪華作為開展對法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②《關于開展對法國工作的請示及中央的批示、給我駐瑞士使館就開展對法工作的指示電》 (1963年2月6日至3月1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4-01;《陳毅副總理對我巴黎新華社分社記者陳定民建議爭取與法國建交信件的批示 (陳定民信)、我對向法試探建交的意見 (未上報)》(1963年1月21日至3月9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4-02。。3月15日,根據周恩來“三八批示”,外交部就“開展對法工作問題”致電駐瑞士使館,請瑞士使館執行修改后的對法工作要點五條,其中第四條為:即著手試探邀請少數接近戴高樂而又對華友好的法政界人士訪華,如富爾、密歇勒、加比唐等。但進行時,須看對方有無要求或暗示,不要強求。③《關于開展對法國工作的請示及中央的批示、給我駐瑞士使館就開展對法工作的指示電》(1963年2月6日至3月1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4-01。
1963年8月20日,在瑞士度假的富爾拜訪中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向中方表示,希望能以私人身份于10月訪華④《我就法國前總理富爾訪華事與我駐瑞士使館往來電》(1963年8月20日至10月14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01。。在邀請法政界人士來訪問題上,中方一直試探法方“有無主動”,這次富爾主動要求訪華,確實是“送上門來了”⑤張錫昌:《四十年法國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2頁。張錫昌當時為中國外交部法國科二秘,曾參與富爾來華談判的整個過程,中法建交后為赴法籌建使館的先遣組成員之一;1964年至1967年在中國駐法國使館任職。。在周恩來批示后,中方很快同意以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的名義邀請富爾⑥高長武:《周恩來與中法建交的幾個關節點》,徐行主編:《二十一世紀周恩來研究的新視野》(下冊),第1221頁。。31日,李清泉向富爾口頭轉達了張奚若會長的邀請⑦《我就法國前總理富爾訪華事與我駐瑞士使館往來電》(1963年8月20日至10月14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01;李清泉:《中法建交談判回顧》,《春華秋實四十年——中法建交回憶錄》,第51頁。。
富爾是以私人名義訪華的,卻與法國的對華政策相吻合。當時法國正謀求打開對華關系的大門。從1962年中期開始,戴高樂在同其政府官員、同盟國政府首腦的談話中,開始較多地談及發展中法關系問題,并提出了承認中國的設想。在戴高樂看來,無論人們喜歡與否,存在著一個現實的中國;中國有5億人口,這使它具有巨大的影響力;貧苦的中國人不會與鄰國為敵,即便他們有了原子彈;中蘇分裂的事實,也需要人們直接同中國接觸。⑧De Bernard Tricot ed.,L’établissement de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entre la France et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27 janvier 1964):Colloque organisé par la Fondation Charles de Gaulle,le 16 mai 1994,Paris:Fondation Charles de Gaulle,1995,pp.25-27; 〔聯邦德國〕康德拉·阿登納著,上海外國語學院德法語系德語組等合譯:《阿登納回憶錄》(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08—209頁。戴高樂謀求承認中國與如下幾個因素有關。首先,正如中方所觀察的那樣,到了1962年至1963年,美法在北約領導權、核武器、歐共體建設等問題上的矛盾確實尖銳化了,法國需要在西方聯盟外尋求支持,以便支撐其恢復法國大國地位的戰略。其次,承認中國也與戴高樂一貫要求的對美外交獨立相一致。再次,中國的存在及其影響的擴大是不爭的事實,解決亞洲問題以及其他世界問題離不開中國的參與。1962年阿爾及利亞問題的解決以及法國和臺灣只是“代辦級”的關系,為中法建交打下了基礎。
促使戴高樂最終主動采取建交試探的因素是越南共和國動蕩的局勢。當時,由佛教徒抗議所引起的政治危機,不僅讓越南共和國吳庭艷政權搖搖欲墜,也加深了本已惡化的美國與吳庭艷政權關系的危機①參見時殷弘: 《美國在越南的干涉和戰爭 (1954—1968)》,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第131—141頁。。這種局勢讓戴高樂覺得有了重返東南亞的機會。1963年8月29日,戴高樂召開內閣會議,會后就越南問題發表聲明,表示密切關注越南發生的嚴重事件,法國了解并愿意真誠分擔越南人民的苦難②國際關系研究所編:《戴高樂言論集 (1958年5月—1964年1月)》,世界知識出版社,1964年,第457頁。。這是法國政府首次就越南問題發表聲明。法國要在越南發揮更大影響,當然離不開中國。戴高樂一向重視富爾在中國問題上的意見,為了明確中國對建交問題的看法,他緊急召見富爾,打算委托富爾秘密訪華。在得知富爾已接到邀請要訪問中國后,戴高樂說:“好吧,你到中國去。不過,你要作為我的代表去中國。”③De Bernard Tricot ed.,L’établissement de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entre la France et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27 janvier 1964):Colloque organisé par la Fondation Charles de Gaulle,le 16 mai 1994,pp.34-35;Edgar Faure,“Reconnaissance de la Chine”,Revue de la Fondation et de l’Institut Charles de Gaulle,Espoir,1972,No.1,p.22.由于當時中法并無外交關系,戴高樂不便給中國領導人寫信,也沒有給富爾正式的委托書。他寫了一封信給富爾,目的是將此信給中國領導人看,以證明富爾是代表他的。信的正文如下:“我再次重申我對你在下次旅行期間將和中國領導人進行接觸的重視。由于我們最近的會談,我能夠向你清楚地指出,為什么我非常重視有關我們和這個偉大人民間各方面關系的問題,以及我是怎樣重視這個問題的。請相信,我完全相信你將談到和聽到的一切。”④《法國前總理富爾面交周恩來總理的法國總統戴高樂給他的親筆信 (譯文及原件影印件)、富爾準備向戴高樂提出的報告及補充說明等》(1963年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07。戴高樂賦予富爾的任務,并非一般的試探,而是謀求發展兩國的全面關系。這種全面關系當然包括經濟關系,但更重要的是建立政治關系。戴高樂要富爾探明,在何種條件下,中法關系可以實現正常化,尤其是探明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和法臺關系問題上的立場。指示說,保持法臺關系,是合乎法國意愿的,即便必要時可以降級,比如在中法建交后法臺保持代辦或者更低級別的關系。⑤Charles de Gaulle,lettres ,Notes et Carnets,janvier 1961-décember 1963,Paris:Plon,pp.374-375.就這樣,本擬以個人名義訪華的富爾成了戴高樂的特使。
為了讓中國充分理解自己角色的變化,9月12日,富爾與夫人邀請李清泉夫婦在日內瓦一旅館吃飯。在餐前的正式談話中,富爾說:從瑞士返回法國后于上周見到戴高樂,戴要求他再次向中方表示,此次訪華是作為戴的代表同中國領導人會談,并將戴的一封信轉給中方,因此他此行實際上是“官方性質”,但希望中國完全保密,對外僅說他是個人旅行。會談的內容,主要是“兩國關系問題”,同時也談談兩國共同感興趣的國際問題。中國駐瑞士使館從富爾的這些談話準確地推測出:“富爾此次訪華很可能要試探和我建交問題”,并于14日以特急提前電報的形式將談話內容報外交部。⑥《我就法國前總理富爾訪華事與我駐瑞士使館往來電》(1963年8月20日至10月14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01。
富爾態度和身份的轉變讓中國外交部有點摸不著頭腦,有關人員對中國駐瑞士使館的樂觀分析半信半疑。根據以往的經驗,中國一直認為,法國目前的重點是發展對華經貿文化關系,而不是政治關系。外交部估計,“富爾訪華的主要目的是:在目前美蘇加緊勾結、中蘇分歧加劇的情況下,摸中蘇關系的底細,試探我對西方,特別是對法國的態度,了解我政策動向,供戴高樂決策參考,并在政治上作些姿態,相機同我拉些關系,以便在同美蘇打交道中加以運用”,“從現有跡象看來,當前法國的主要步驟是發展中法貿易關系、爭取設立貿易機構,同時以政治姿態配合經濟措施,一時還不會走到同我建交這一步”。“根據富爾向我駐瑞士使館透露的訪華意圖來看,也不能完全排除提出有關改善兩國關系的建議的可能性”,“也可能提出一些改善兩國關系的中間性步驟向我試探”。根據對富爾訪華使命的這一估計,外交部于10月15日呈報《關于利用富爾訪華時機開展對法工作的幾點建議》:“針對法當前對華作法,一方面我們可根據需要和對我有利的原則同法發展經濟關系,另一方面,可利用富爾訪華時機,開辟一些今后開展對法工作途徑,設法同法國保持一些政治接觸和聯系,并推動兩國政治關系的逐步改善。”①《法國前總理富爾訪華的有關請示及中央的批復 (邀請來訪建議、富爾簡歷、來訪及接待方針指示、工作建議)》(1962年6月15日至1963年10月1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16。為了做好接待富爾的工作,外交部之前 (10月2日)擬定了具體的接待辦法:由外交部西歐司和外交學會共同組成接待工作小組,領導和處理有關問題;至于接待規格和禮遇,原則上擬按私人身份處理,規格可與上次訪華相同;②1957年富爾訪華時,毛澤東予以接見;周恩來接見并便宴;彭真市長舉行酒會,周恩來出席;外貿、文化、農業、司法等部部長接見并會談有關問題。如富爾以戴高樂代表身份來華,則規格可以提高一些。當天,周恩來和陳毅批準了這一接待方針。③《法國前總理富爾訪華的有關請示及中央的批復 (邀請來訪建議、富爾簡歷、來訪及接待方針指示、工作建議)》(1962年6月15日至1963年10月1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16。
從外交部的估計和準備的對策可以看出,中方對富爾使命的認識是有偏差的:戴高樂賦予富爾的是同中國發展全面關系的使命,中方卻認為法國主要想發展經濟關系。這種偏差不能不給雙方初期的會談帶來困難。
四、富爾訪華第一階段會談(10月23日至25日)
1963年10月11日,富爾夫婦離開巴黎前往亞洲調查訪問。根據行程,他們將相繼訪問柬埔寨、香港、中國,然后到印度。中國開始通知有關方面做具體的準備工作,并通過各種渠道,打探富爾來華的真實目的。12日,富爾夫婦抵達柬埔寨。14日,外交部致電駐柬埔寨使館,請駐柬使館設法了解一些富爾的訪華意向。19日,駐柬使館根據柬埔寨媒體的相關報道,認為“富爾此行是代表戴高樂對我作進一步的接觸和試探”。④《法國前總理富爾訪問柬埔寨、緬甸和印度情況反應(與我駐柬埔寨、緬甸和印度使館往來電)》 (1963年10月14日至11月12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167-01。21日,富爾夫婦自深圳入境抵廣州。外交學會吳曉達副秘書長及翻譯張錫昌前往深圳羅湖迎接,并遵照周恩來的指示設法探明富爾此次來訪目的。富爾表示,其來華身份對外稱以私人名義,但對內正式代表官方,聲稱帶有一封戴高樂親筆介紹信要交給中國國家領導人。富爾強調,此次來華負有迫切使命,要同中方就全面開展兩國關系問題進行交談與探索。為此,他要求及早見到周總理,先交談兩次,旋即謁見毛主席、劉主席及陳毅副總理。他特別提出要見共和國主席,因為他是受戴高樂總統之命來的。⑤《接待法國前總理富爾訪華情況簡報 (第一期至第九期)》(1963年10月21日至11月8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167-02。至此,中國才得出結論,富爾“代表戴高樂”來談“中法關系問題”。于是,中方當即決定,在預定的高低兩種接待方案中按高規格接待,調用一節專列車廂掛在從深圳開往廣州的火車上。21日下午,富爾夫婦抵達廣州,廣州市副市長羅培元等到車站歡迎;當晚,廣州市市長曾生和夫人設宴歡迎。⑥張錫昌:《親歷中法建交》,《春華秋實四十年——中法建交回憶錄》,第8—10頁;《應我人民外交學會的邀請法國前總理富爾到廣州》,《人民日報》1963年10月22日。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富爾在北京的住處從北京飯店改為釣魚臺⑦《有關法國前總理訪華接待方案、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宴會祝酒辭、給我駐外使團的有關通報、有關值班簡報及周恩來總理批示》(1963年10月12日至11月11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02。。
10月22日,富爾夫婦抵達北京。23日,周恩來接見富爾夫婦,就改善兩國關系問題初步交換了意見。在會談之初,雙方一致肯定了增進中法關系的愿望。在發展對華關系上,富爾提出兩個方案:(1)先談建交、交換大使,在這種情況下,臺灣問題應如何解決;(2)如果臺灣問題不能解決,可考慮先互設政府的或民間的常設機構兼理經濟和文化事務。他說:如果法國承認了中國,法國支持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是“合乎邏輯的”。最微妙的是臺灣問題。對法國來說,同臺灣斷絕一切關系有困難,因為島上存在一個事實上的“政府”,而且戴高樂沒有忘記在戰時曾同蔣介石站在一邊,不愿突然切斷關系。如果法國承認中國,臺灣主動同法斷交,這是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困難的是,不能肯定蔣介石將采取什么態度。如果法國承認新中國,而臺灣不作任何表示,那么,照中國的想法,法國應撤回駐臺人員,但這使法國為難,希望共同尋找不使法國為難的辦法。他并探詢法在中法建交后可否在臺灣保留一個人,降低級別。周恩來反復強調指出,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如果戴高樂覺得采取勇敢的行動,切斷同蔣介石集團的關系,同中國建交的時機已到,中國歡迎這一決心,也愿意同法國建交,直截了當地交換大使,不采取英、荷那種拖泥帶水的辦法。如果戴高樂認為時機尚未成熟,還有困難,中國愿意等。周恩來列舉了四種不同類型的對華關系:一是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二是建立半外交關系;三是像法國目前同中國的關系,法國愿意促進對華關系,但由于臺灣問題等困難,尚未能建立正式關系;還可能出現第四種類型,即第三種類型的國家,在建立正式關系前,先建立非正式的關系,如先設立貿易代表機構,半官方的,民間的,都可以考慮。周恩來請富爾考慮后一意見。①參見《關于中法建交問題》(1963年10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359—372頁。
周恩來同富爾的這次談話,顯示了雙方的兩點分歧。第一,雙方的出發點略有不同,富爾更強調解決政治、外交關系,而周恩來側重于首先發展經貿關系。第二,在臺灣問題上,富爾秉承戴高樂的指示,不愿意同臺灣主動斷交,并試圖在臺灣保留領事,對此,周恩來斷然表示不可能。富爾在次日向中方有關人員談到他對這次會談的看法時說,他的印象是周恩來對我們所談的問題態度似乎比較消極,在發展兩國政治關系方面,中國總是希望法國先走第一步。富爾說:戴高樂對機器、產品之類不直接關心,他所著眼的是政治關系問題。他還略有埋怨地表示:“我推動了戴高樂,還要來拉你們。”②《接待法國前總理富爾訪華情況簡報 (第一期至第九期)》(1963年10月21日至11月8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167-02。
10月24日下午,陳毅副總理接見富爾夫婦,繼續就改善兩國關系問題進行會談。陳毅一方面重申了中方改善中法關系的愿望,另一方面著重闡明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陳毅說:從中方來說,建立外交關系沒有困難,“但是我們要向閣下申明,也請閣下向戴高樂說明,我們不能承認‘兩個中國’”,“似乎有這么一股暗流,有些人一方面承認我們,一方面又在美國的唆使下承認蔣介石集團,這對我們說,不能接受,如果有人要這樣做,即使建了交,我們也要馬上斷交”。陳毅提議,如果現在建交有困難,可以像埃及、古巴那樣,先發展經貿、文化和宗教往來,一天天增進關系,逐步把蔣介石的代表擠走。富爾提出了增進兩國關系的三種設想:(1)法國直截了當地承認中國,兩國互派大使,不附加任何條件。他說:采取這種辦法,中國方面擔心蔣介石可能繼續保持在法國的“外交”代表,同時讓法國的代表繼續留在臺灣。而他認為,蔣介石不太可能這樣做。中國愿不愿意冒此風險,由中國方面自己判斷。(2)中國對中法建交附加條件。法國承認中國,而中國要法國驅逐蔣介石的代表和撤回駐臺灣的代表。他表示戴高樂“不大喜歡這種辦法”,“因為這是粗暴的、突然的措施,是難以執行的措施”。他設想可以采取中間性的辦法,即法國召回駐臺灣的“外交代表”而保留領事或職員。(3)延期承認,先發展各種關系,這是中國的建議,他也理解這是為建立正式外交關系準備條件。他表示,這項建議是有趣的、合理的,但又表示,這種辦法過去在古巴、埃及行得通,而在法國比較困難,因為法國是重視禮儀的國家,必須給予臺灣的“外交”代表以應有的禮遇。如果找不到其他辦法,可以考慮這個建議,但希望中方“幫助我們找出同臺灣斷絕關系的辦法”。在闡述這三種設想時,富爾強調指出,中國方面不要因臺灣問題(這在法國看來是個小問題)而使目前新形勢下中法互換大使這樣的重大國際事件歸于失敗。③《陳毅副總理接見法國前總理富爾談改善中法兩國關系》(1963年10月24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09。
從這次會談可以看出,富爾仍在繼續試探促使中方降格以求的可能性,同時也為退而求其次就第三種設想達成一些協議留下余地。由于富爾已提出了比較具體的方案,討論已比第一次深入很多,接下來是就這三項方案,進行更為具體的討論。
25日下午,周恩來、陳毅同富爾舉行第三次會談。富爾進一步闡明昨日提出的三種方案,并將之概括為“無條件承認”、 “有條件的承認”和“延期的承認”三條。(1)法國公開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中國方面表示同意,并互換大使。這就是無條件承認。(2)有條件承認。如果法國承認了中國,中國提出同臺灣斷交、驅蔣的條件,戴高樂會不愉快。他提出一個避免這種局面的主意:法國照會中國,主動承認中國,中國方面給予答復,對法國倡議表示同意,但對這種承認附加兩點解釋,說明中國方面認為這種承認意味著同臺灣斷絕關系,而且法國不能同將來可能出現的“福摩薩共和國”發生關系。但中國不追究法國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對法國在臺灣的代表和臺灣在法國的代表可以不提,這僅僅是執行問題。采取這種辦法,就顯得中國并不提出任何條件,不致使法國丟臉。(3)延期承認。即先不作外交承認,但中法間形成一種特殊的局面,逐步將蔣介石的代表擠走。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互設商務、文化機構有著雙重意義,一方面是可以增進文化、貿易往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方面可以作為最后建立正式關系的階梯。這個機構可以采取民間方式,但從政治上準備條件著眼,派遣官方的比較好。但他強調,他傾向于采取比較完全的解決方案。周恩來肯定了三條:(1)雙方都愿意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互換大使。(2)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這是對1949年以前就存在的中國政府承認的延續,因此,“中華民國”不再存在。(3)剩下的只是一個臺灣問題。周恩來強調指出,如果法國認為臺灣地位未定,那就構成兩國建立正式關系的障礙;如果法國只是想擺脫同臺灣的困難情況,那就是一個程序問題。富爾表示,戴高樂對臺灣地位問題沒有考慮,戴高樂只委托他向中國了解,能否在承認中國的同時,在臺灣保持一個級別較低的代表。周恩來再次表示,這是不可能的。①《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接見法國前總理富爾談改善中法兩國關系》(1963年10月2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11。
通過23日以來的三次會談,中法大致摸清了對方的立場:法國不愿主動斷絕同臺灣的關系,力圖在同中國建交后在臺保留一定的代表,而中國則對這兩點斷然拒絕。談判陷入僵局。不過,雙方取得了兩點共識:第一,雙方都肯定了要發展中法關系的愿望,并愿意建立正式的大使級外交關系;第二,雖然法方不愿意主動斷絕與蔣介石的關系,但是富爾表示,法國不承認“兩個中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就不會再承認在臺灣的“中華民國”。這兩點為將來雙方達成最終協議打下了基礎。剩下的就是一個“程序問題”,就是找到某種辦法,使法臺較為自然地擺脫關系。
為了緩和談判的氣氛,同時也留出時間思考一下富爾在這幾天會談中的表現及提議,25日晚,周恩來決定安排富爾夫婦去大同和呼和浩特等地參觀游覽三天,談判暫停②張錫昌:《親歷中法建交》,《春華秋實四十年——中法建交回憶錄》,第18—19頁。。
五、富爾訪華第二階段會談(10月29日至11月2日)
經過上述第一階段的會談,雙方對對方的立場都有了解,并相應作了對策性的調整。富爾雖然想很快解決政治關系,但看到無法在臺灣問題上取得中方諒解,為了避免“空手而回”,開始更多地轉向先發展經貿文化關系等過渡性方案。實際上,在25日的會談中,富爾的調子已經降低,開始重視這一方案。26日在離京赴山西前,富爾將他準備返法后向戴高樂提出的報告初稿遞交中方。富爾的報告總結了前幾日同中方的談判,并把結果概括為兩條建議:(1)中法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在這種情況下,法臺斷交是“合乎邏輯的”,但中國同意法國在適當的時間采取合適的形式來進行,而且法臺相互保留非外交代表系出于“方便的考慮”,“沒有任何國際法的基礎”。(2)發展正式的經濟文化關系。如果考慮到上述意見,一方認為應該推遲建立正式政治外交關系,就轉向這一建議。雙方設立的貿易代表機構最好是政府性的,或至少是半官方的。“雙方認為這種經濟和文化關系應視為不僅符合雙方的直接和實際的利益……而且還應視為走向全面正常化的一個階段和一種過渡”。因此,“不能認為這種解決辦法比前一種解決辦法差得很多”。①《法國前總理富爾面交周恩來總理的法國總統戴高樂給他的親筆信 (譯文及原件影印件)、富爾準備向戴高樂提出的報告及補充說明等》(1963年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07。可以說,到這時,富爾已經設想如果無法達成正式建交方案,就采取后退一步的方案,先發展經貿關系。
針對富爾的報告和他同中國領導人會談的情況,外交部于28日擬就《關于與法國談判建立兩國外交關系的意見》。《意見》認為,目前法方在建立中法外交關系的談判中所采取的做法是:以不堅持第一方案 (無條件建交)和表示對第三方案 (延期建交,先互設貿易、文化機構)興趣不大,圖換取中方能接受第二方案(即不作為條件的建交)。對此,外交部的建議是:“從利用帝國主義矛盾及開展對法工作考慮,我們如能在堅持反對‘兩個中國’原則下,同法國解決建交問題對我是有利的。因此,我們應適當爭取這一途徑,盡可能和富爾就有關問題,談出一些眉目來”。根據這一考慮,外交部提出幾條建議:(1)建議就新提出的“有步驟建交方案”(見后文)同富爾交換意見;(2)劉主席接見富爾時,也可表示一下中國愿同法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愿望;(3)把周總理最后一次接見富爾時的“談話要點”以書面形式交給富爾,以便他能夠據此向戴高樂反映中方的意見;(4)關于互設半官方的貿易機構等過渡性措施,在中法不能建立正常外交關系之前,還是有必要采取的,應做這方面的準備,但富爾表示對此興趣不大,因此,可不必和他具體討論此事。但可向他表明,如他回國后,法方覺得有步驟建交還難以立即實現,便采用這一方案,通過雙方駐瑞士使館進行具體接觸。外交部將《意見》以及“有步驟建交方案”送交核閱。周恩來批示:“擬同意。”②《我與法國談判建立兩國外交關系的意見及周恩來總理的批示》(1963年10月28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15。
外交部的這份《意見》是中國官方第一次全面以追求中法建交為主要目的的建議,同以前的歷次建議相比,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前根據對法方意圖的判斷,制定的對策總是以發展經貿為主,這次則主要以建交為主;二是在外交部所提的“有步驟建交方案”中,已考慮了法方的意見,不再把法主動同臺斷交作為中法建交的前提。具體來講,把中法建交過程設想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法國通過中國駐瑞士大使館提出正式照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建議互換大使。中國政府復照表示歡迎,并在復照中申述,中國政府認為法國政府的這一行動意味著:(1)法國政府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認臺灣還有一個代表中國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不再同蔣介石集團保持任何等級或任何形式的官方關系;(2)基于同一理由,法國政府對于任何變相形式制造“兩個中國”的做法將不予以支持;(3)法國政府支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應享有的合法權利和地位,不支持以任何方式在聯合國保留蔣介石集團的代表。第二步,中法雙方相約同時發表上述往來照會,照會公布后,雙方派出臨時代辦籌辦建館事宜。第三步,在籌建使館過程中,可能出現三種情況:(1)法蔣各自撤回派駐對方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2)蔣介石集團賴著不走,法國政府把他們作為普通僑民看待,不給外交或領事的權利和地位。法國撤回在臺灣的外交代表,而不降級保留任何代表。即使有法國人員留在臺灣,也只具有普通法國僑民的身份。在上述這兩種情況下,一旦籌建使館事宜完成,雙方即可交換大使。(3)蔣介石集團的代表賴在法國不走,繼續以“外交代表”身份出現,法國在臺灣降級保留代表,這種情況還不如目前的中英關系,中國政府將不得不遺憾地中斷同法國建交的步驟,并召回已經派出的臨時代辦。③《關于與法國談判建立兩國外交關系的意見、同意裴特里為瑞典新任駐華大使、伊拉克要求援助事、英國畫刊刊登侮辱毛主席圖片事》(1963年10月19日至11月29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189-10。
10月29日下午,富爾夫婦乘專機從太原返回北京。可能為了緩和氣氛,陳毅于30日下午首先同富爾談及了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并共進晚餐。陳毅表示,希望中法建交后,法國直截了當地支持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反對蔣介石的代表,這就證明兩國建交是完全的、無保留的,但中方不以此作為中法建交的先決條件。①《陳毅副總理接見法國前總理富爾談關于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問題》(1963年10月30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12。10月31日,周恩來、陳毅繼續同富爾會談。周恩來在詳細敘述中方上述的“有步驟建交方案”后指出,如法方對此方案仍然感到困難,作為過渡性步驟,可以考慮雙方互設半官方的常駐貿易機構。富爾獲知方案后,調子反而降低。在富爾看來,中國還是以法斷絕同蔣介石集團的一切關系作為兩國正式建交的條件,戴高樂對此可能有不同意見,因此,現在考慮互設常設機構較為現實。經周總理再三追問,富爾才明確亮出法方的全部底牌:法國不能主動驅蔣,希望中法建交后法臺能相互保留“領事”。對于這些,周恩來并未像第一階段會談那樣立刻斷然拒絕,只是表示“還得想一想,還得同政府和黨說一說”。由于當時毛澤東在上海小住,中方約富爾到上海再談。②《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接見法國前總理富爾談中法有步驟建交方案》(1963年10月31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13。當日晚,劉少奇接見富爾夫婦時表示,“我們很歡迎同法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進一步發展中法兩國經濟和文化聯系”,中國沒有別的要求,只要不出現“兩個中國”就行了③《劉少奇主席接見法國前總理富爾談話記錄》 (1963年10月31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05。。
在同富爾這次談話前,周恩來與在上海的毛澤東通電話,報告同富爾談判的情況,并傳去有關文件。31日,毛澤東閱文件后,決定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等人于11月1日飛滬面商。當日,這幾名中央負責人在毛澤東的住處討論中法建交問題。周恩來匯報富爾關于中法建交提出的三種方案,以及在京常委對這三種方案的意見,認為法方的第一方案中方難以考慮;第二方案中方認為是好的,但法方有困難;如果別無選擇,就考慮第三方案。會議認為現在雙方都有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愿望,可不提第三方案,而是提出新的直接建交方案比較適宜。會議委托周恩來、陳毅代表中國政府同富爾進一步磋商。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73—274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592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鄧小平年譜 (1904—1974)》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777頁。
富爾夫婦乘坐專機抵滬后,11月1日晚,周恩來、陳毅在上海和平飯店繼續同其就中法關系進行會談,周恩來向富爾提出了“新的直接建交方案”。該方案分公開行動和內幕默契兩部分。公開行動是:法國政府首先向中國政府提出正式照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并且建議中法兩國立即建交,互換大使;中國政府復照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歡迎法蘭西共和國政府的來照,愿意立即建立中法兩國之間的外交關系,并且互換大使;然后,中法雙方相約同時發表上述往來照會,并且立即建館,互派大使。采取這一公開行動的前提是中法就如下三點達成了默契:(1)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認在臺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2)法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3)中法建立外交關系后,在臺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撤回它駐在法國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法國也相應地撤回它駐在臺灣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這一方案中,中方既未要求法國主動與臺“斷交”,而且在談話中,對法臺保留領事一節保留模糊態度,實際上是默認法臺可以相互保留領事。富爾說,“這個形式好”,他“沒有反對意見”。周恩來表示,將給富爾一份書面文件,以便于富爾向戴高樂報告。雙方還一致同意,發展經貿關系的第三方案,暫不列入書面文件。⑤《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接見法國前總理富爾談兩國直接建交方案、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 (草稿)》(1963年11月1日至11月2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10。
當日夜24時,周恩來把晚間和富爾的談話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報告,并附上“新的直接建交方案”(即“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全文。毛澤東于11月2日晨批示: “很好,照此辦理”。①《毛澤東主席對周恩來總理關于中法建交問題請示的批復、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 (草案、最后定稿、法文翻譯件)、周恩來總理批示》 (1963年11月1日至11月2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06。2日上午,周恩來在上海和平飯店同富爾繼續就“談話要點”中的細節進行商談,修訂了部分文字,形成最終定稿②《周恩來總理接見法國前總理富爾談兩國直接建交方案、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 (1963年11月2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03。。
11月2日下午5時,毛澤東接見富爾夫婦,周恩來、陳毅陪同。毛澤東說:“兩位來得正是時候”,“要把兩國正常關系建立起來”。富爾表示:“現在可以說已經成功了。”③《毛澤東主席接見法國前總理富爾夫婦談中、法關系及國內外局勢》 (1963年11月2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14。而實際情況也完全符合中法兩國的期望:經過1963年底和1964年初兩國代表在伯爾尼的正式談判,中法之間的外交關系完全建立起來了。
六、結 語
通過本文的上述考察,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第一,富爾訪華及其促成的中法建交,首先是中法外交戰略調整的結果。中國戰略重點在于打擊美帝兼及蘇修,法國要在防范蘇聯的同時對美獨立,雖然兩國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在追求獨立自主的外交、沖擊美蘇把持的兩極格局方面是一致的,這種一致性促成了中法的戰略合作,奠定了中法建交的基礎。這些,可以用兩國領導人超越時空的對話來進一步加以證實。1963年11月2日毛澤東接見富爾夫婦時,重提了他幾年前同英國蒙哥馬利元帥的談話,“如果蘇、中、英、法有大體一致就好……還是從倫敦經過巴黎到東京,把這工作做好。戴高樂有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想法,再擴大一點,通過北京到東京”,世界局勢在變化,“再過五年、十年,變化會更大。像英、西德、意大利、日本,獨立性會增加,這是不可避免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對于這種大戰略,富爾自然無法答復,只能籠統地表示“這是個好意見”。④《毛澤東主席接見法國前總理富爾夫婦談中、法關系及國內外局勢》 (1963年11月2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14。毛澤東1960年同蒙哥馬利的談話可參見《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21—435頁。在四天后,完全不了解富爾訪華情況的戴高樂卻作出回答,他對自己的新聞部長阿蘭·佩雷菲特 (Alain Peyrefitte)說: “我們總要有一個反面的同盟者。這是法國一貫的策略。法國的國王曾經和土耳其結盟以抵抗羅馬帝國;他們曾經和波蘭結盟以抵抗普魯士;他們曾經和美國叛亂分子結盟以抵抗英國。而我,我曾經和俄羅斯結盟,為的是使我們在面對德國時變得更強大。今天,我和中國結盟,為的是使我們再次面對俄羅斯時變得更強大。不過,我們現在還沒到那一步,現在僅僅是為了重新建交。”⑤De Bernard Tricot ed.,L’établissement de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entre la France et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27 janvier 1964):Colloque organisé par la Fondation Charles de Gaulle,le 16 mai 1994,pp.28-29.
第二,富爾訪華的最終成行,也是中國對歐戰略、對法政策一系列調整的結果。隨著“第二中間地帶”理論的提出,中國在60年代初調整了對歐戰略,把西歐作為反美反修的“間接同盟軍”。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對美法矛盾及其發展趨勢的觀察。在中方看來,戴高樂上臺后美法矛盾的加劇發展,實際上為中國利用這一矛盾提供了可能性;雖然英國、聯邦德國、日本、加拿大等國也在第二中間地帶之列,但這些國家與美國的矛盾,還不像法國那么大。也正因為此,中國嘗試從法國開始在第二中間地帶打開缺口,并相應地在60年代初調整了對法政策,采取了種種具體行動,如主動謀求發展中法關系、積極與諸如富爾等與戴高樂有密切關系的人建立聯系等等。中國的這種外交調整,加上戴高樂嘗試借助中國對美搞獨立和重返東南亞,使得中法關系不僅有了戰略上的基礎,也有了政策上的基礎。
第三,就在中法都謀求改善雙方關系的時候,富爾充當了“龜山”與“蛇山”之間的橋梁。富爾的這一角色,有一定的偶然性:他恰在1963年8月要求訪華,而在此后又恰好受戴高樂的委托來同中國談中法關系問題。但是,由于中國外交部長期以來就觀察到富爾與戴高樂的密切關系,且很早就擬以富爾為第一邀請對象來開展對法工作;①后來中方在相關總結中,曾把富爾看成是戴高樂的智囊團成員、中國問題上的顧問。參見《我就中法建交達成協議事給我各駐外使館、代辦處的通報、我駐瑞士使館關于中法建交的幾點體會》(1964年1月18日至3月9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97-10。由于戴高樂在中國問題上確實很倚重富爾的意見,而且在越南局勢緊張的情況下極欲改善對華關系,富爾的中國之行又具有了某種必然的性質。富爾本人曾兩度出任總理,資歷深、地位高,在戴高樂政府中雖無官職,卻是戴高樂政治圈子里的要員,深得戴高樂的信任;而在對華關系上,富爾一直主張對華友好,并同中國領導人建立了聯系;再加上富爾律師出身,能言善辯,是個談判能手。這一切,使得富爾自然成為“擔負秘密使命的適宜人選”。②張錫昌:《親歷中法建交》,《春華秋實四十年——中法建交回憶錄》,第11頁。
第四,富爾訪華使命的最終順利完成,也是中法雙方在平等的基礎上協商的結果。這種平等,既體現在禮遇等形式上,也體現在協商的實質內容上。雖然富爾并未攜帶“特使”證書,但中方始終以此身份來接待他,在出行、住房、談話中基本上都給予了戴高樂特使的禮遇。③如派專機接送富爾,就是相當于總理的待遇,富爾對此也很清楚,并向中方表示感謝。參見《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接見法國前總理富爾談中法有步驟建交方案》(1963年10月31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1982-13。在實質內容上,雖然中方在驅蔣的具體方式上作了一些讓步,但在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上,中方并未有任何改變。以三項默契為基礎的“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實際上也是法國在中法建交中所需要承擔的義務。可以說,中法兩國在反對“兩個中國”問題上所取得的共識,乃是富爾北京之行最終成功的必要前提。也正是在這一前提下,中法雙方經過數次平等的、艱苦的協商,終于找到“驅蔣”的辦法。這也說明,只要兩個國家互相尊重對方核心利益,總可以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找出改善雙邊關系的恰當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