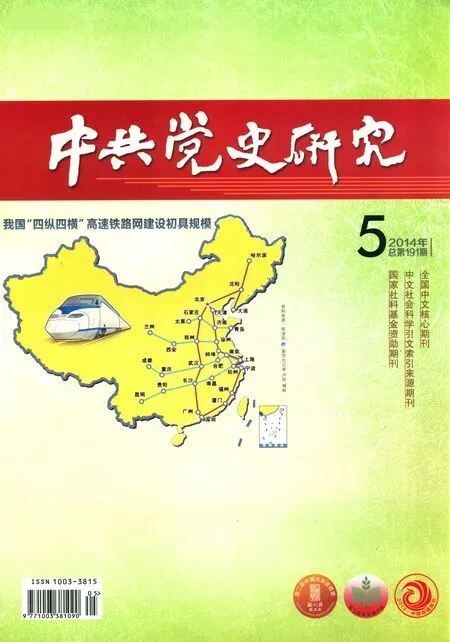民團、農民武裝與陜甘邊紅軍的建立及影響
黃正林 溫 艷
(本文作者 黃正林,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西安 710062;溫艷,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后、陜西理工學院教授漢中 723000)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劉志丹、謝子長等中共黨人在陜西、甘肅交界地區建立了陜甘邊蘇維埃政權,在第二次反“圍剿”之后,與陜北蘇區連成一片,成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碩果僅存的根據地,因而成為中共中央和南方各路紅軍的落腳點。在近些年的中共黨史研究中,陜甘邊根據地史研究頗受重視,也取得了一些比較重要的研究成果①如李仲立、曲濤:《隴東老區政權史》,蘭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隴東老區紅軍史》是研究陜甘邊紅軍和根據地比較重要的著作);劉鳳閣:《陜甘邊紅二十六軍探源》,中共慶陽地委黨史辦:《慶陽黨史論文集》,2001年印行;曲濤:《紅色足跡——隴東老區重大事件述評》,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李東朗: 《簡論陳家坡會議》, 《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3期等;這基本可以代表陜甘邊歷史當前的研究水平。。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主要從“革命史”的角度考察陜甘邊的歷史,缺乏對相關歷史事件文獻的挖掘與求證,對許多問題的討論價值判斷大于實際判斷,把復雜的歷史問題一并歸為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斗爭,缺乏對復雜歷史問題實事求是的考察。
近年來隨著史學研究的深化,一方面,對如何研究革命史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討,提出了“新革命史”研究范式,主張將中共革命與鄉村社會的相互聯接和互動為切點,“將為中共革命的歷史進程提供一個新的解釋構架,從而實現中共歷史研究的突破”①李金錚:《向“新革命史”轉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突破》,《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期。。一方面,對問題的討論也越來越深入,就中共蘇維埃時期歷史研究而言,黃道炫的《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 (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所有這些,都為我們研究陜甘邊蘇維埃政權的歷史提供了理論基礎與范本。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本文主要利用當下能夠看到的文獻,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陜甘地區社會生態入手,對陜甘邊紅軍建立過程中收編民團、農民武裝以及所產生的影響等問題進行探討。
一、陜甘邊界地區的民團與農民武裝
陜甘邊界民團與農民武裝的形成,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陜甘政治與自然生態有直接的關系。民國建立后,在地方軍閥的統治下,陜甘鄉村政治生態面臨著嚴重的問題,軍閥為了擴充地盤和實力“不停地打仗,無情地吮吸農民的膏脂,稅收高到最大限度”②〔美〕馬克·塞爾登著,魏曉明、馮崇義譯:《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3—14頁。。農民不僅要承擔傳統的田賦和正稅,且還要承擔日益繁雜的田賦附加和各種捐稅。陜西各種捐稅即達30余種,如特征產業稅、民團費、房捐、車馬費、青苗費、契稅附加、省銀行股本捐 (銀行的股本,隨時征收,但征而不還)、省府庫捐、畜稅、屠稅、牙稅、雜稅、斗捐、秤捐、預征田賦 (每年兩三次不等)、教育費附加、建設費附加、借征房租、登記費 (不登記則房屋和田地充公)、煙畝費、煙畝附加、指煙借款 (無論種煙與否都得交納)、車捐 (鄉村馬車與人力車出入城內)、軍隊維持費、剿匪費、子彈費、偵探費、修械費、花捐 (明暗娼妓納捐才能接客)、煙燈捐、賭捐,此外還有催款費及省府派往各縣催款人員的招待費等,如時人所言“自民國成立以來,苛捐雜稅,巧立名目,五花八門,光怪陸離”③何挺杰:《陜西農村之破產及趨勢》, 《中國經濟》第1卷第4—5期合刊,1933年8月25日。。據統計,與陜北相鄰的甘肅慶陽縣1906年始征百貨統捐,稅率不過5%。民國以后改為百貨征收局,1914年開征包裹稅;1926年開征皮毛、公買商畜、藥材、駝捐、慶環煙酒、董志牲畜稅;1927年兼征卷煙特捐稅;1928年兼征屠宰、散茶稅;1929年兼征大布統捐、印花分銷等,征收的稅種達20余種④張精義:《慶陽縣志》卷6《財賦志·稅捐》,1931年修。。除各種捐稅外,居民還要負擔駐軍或過往軍隊的各種糧餉,如慶陽縣每年承擔隨糧丁攤派的軍款達48000元,鎮原達6萬元,超過丁糧的3倍,正寧負擔有軍部提糧、借糧、軍款3項,每年達29100元⑤王智:《廿一年甘肅民眾負擔概算》,《拓荒》第2卷第1期,1934年3月。。隨著大量攤款接踵而至,“遂產生大批提款委員會,車騎四出,雞犬皆驚,每區有攤派至數千元不等,每縣有攤派至數萬元不等”⑥孫左齊:《中國田賦問題》,新生命書局,1935年,第258—259頁。。軍閥造成的政治混亂,大量的糧食被搜刮去養活軍隊,導致農村經濟的崩潰和農民的貧困。
就在苛捐雜稅壓得農民喘不過氣來的時候,1928年至1930年西北發生了大旱災,陜甘地區成為重災區,各地產生了大量的災民。如慶陽縣遭災待賑的難民有62000余人,占全縣人口的71%,⑦《甘肅省慶陽縣民國十七年災情一覽表》,手抄本,甘肅省圖書館藏。寧縣災民達8.7萬余人⑧《甘肅省寧縣民國十七年災情一覽表》,手抄本,甘肅省圖書館藏。。1929年災情繼續擴大,甘肅居民無糧無種者達80%⑨季嘯風、沈友益主編: 《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第43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504頁。。陜西涇陽、三原、耀縣、富平、蒲城、大荔6縣“無衣無食災民共達四十萬”⑩浪波:《西北災情的實況及其救濟的方策》,《西北》1930年第11期。。據1929年中國國際饑荒救濟委員會估計,饑荒造成陜西250萬人死亡,幾乎占全省人口的1/3,另有50萬人逃荒到其他省份?〔美〕馬克·塞爾登著,魏曉明、馮崇義譯:《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第14頁。。旱災把陜甘地區農民推上了生存的絕路。大部分地方“富戶變為貧戶,家貧者流于乞丐”①《甘肅省寧縣民國十七年災情一覽表》,手抄本,甘肅省圖書館藏。;環縣“年富力強者或逃走鄰縣,或乞丐度日,或傭工以茍全性命”,②《甘肅省環縣民國十七年災情一覽表》,手抄本,甘肅省圖書館藏。合水縣“年壯之人,欲苦力傭工以覓食,到處無活可做”③《甘肅省合水縣民國十七年災情一覽表》,手抄本,甘肅省圖書館藏。。定邊、靖邊居民生活無法維持,而以樹皮、草根為食,但“此種物品,亦因天氣亢旱,無從獲得。面黃肌瘦,甚至身腫殞命于道旁街市者,觸目皆是,人獸相食,駭人聽聞”。④季嘯風、沈友益主編: 《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第43冊,第511、521頁。大旱災使陜甘農民生活雪上加霜。
由于鄉村政治與自然生態的惡化,陜甘農民生活艱難到了不能忍受的邊緣。20世紀二三十年代,陜甘“農民面對最要緊的問題包括饑餓、戰爭和土匪的破壞、長期惡化的債務、租佃增多、離鄉城居地主的出現、沉重的稅收和土壤的干燥。這些情況促使農村秩序破壞,滿足不了人們生存的最低需要”。⑤〔美〕馬克·塞爾登著,魏曉明、馮崇義譯:《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第13頁。因此,有的農民鋌而走險,被逼走上了與官府對抗的道路,有的則放棄家園上山投靠“山大王”落草為寇。從民國建立到30年代,陜甘地區民變此起彼伏。1915年8月,寧縣北區農民5000余人圍攻縣城,“反對新稅,歸交農具”⑥寧縣志編輯委員會: 《寧縣志》,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00—401頁。;環縣民團團總利用農民對賦稅的不滿,殺死新任縣長李祎,發動起義⑦蔡屏藩:《陜西革命先烈事略》,臺北1962年印行,第113頁。;陜西藍田農民因不堪苛捐雜稅,包圍縣城進行“交農抗稅”斗爭⑧政協藍田縣委員會: 《討袁期間藍田縣的一次“交農”運動》, 《陜西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1962年,第112—114頁。。1924年4月,合水縣3000多名農民包圍縣城;次年寧縣平子鎮發生民變,進行抗稅斗爭⑨陶繼堯、沈滿:《合水農民的一次抗稅斗爭》,《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0—133頁;魏紹武:《張兆鉀盤踞隴東》,《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3頁。。1926年6月,周至農民舉行反對軍閥吳新田暴動⑩政協周至縣委員會:《盩厔農民反抗吳新田的武裝斗爭》,《陜西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963年印行,第84—91頁。。1928年至1930年西北大旱災把陜甘民眾推到了生死邊緣,陜甘地區隨著災民的增多,無依無靠的災民或加入民團,或落草為寇。據統計,1931年前后,位于子午嶺山麓的正寧縣有民團10余股,合水縣有民團20余股?慶陽地區志編纂委員會:《慶陽地區志》第4卷《軍事志》,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48頁。。慶陽縣以北部子午嶺深山的南梁為中心,活動著許多饑民武裝,每股少則10多人,多則幾十人?華池縣志編纂委員會:《華池縣志》,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06頁。。子長縣形成了四大民團,即北區的折可達民團、東區黃天錫民團、西區李丕成民團、南區宋應昌民團,團總均為當地大地主?子長縣志編纂委員會:《子長縣志》,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5頁。。20世紀30年代初,清澗縣較大的民團白秀珍、張云、惠樹藩、拓守清、李成善、黃維漢、白瑞珠、邱樹楷等8支民團?清澗縣志編纂委員會:《清澗縣志》,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0頁。。為反對官府與軍閥勒索,僅落草在黃龍山地區的農民武裝就有十余股之多,如河南貧民樊老二 (鐘秀)、河南難民馬永旺、郭寶珊以及本地賈德功、梁占奎、楊謀子、李志英等?劉在時: 《黃龍山區“山大王”去向記 (1912—1938)》, 《黃龍文史資料》第2輯,1990年2月,第157—162頁。。這些民團、農民武裝成為災民的歸宿,如陳珪璋勢力大增的主要原因是饑民“蜂附其部以求食活命”,時稱“跟陳珪璋吃大戶”。寧縣四鄉幾乎村村有人投奔陳氏,甚至是整村投靠,如良平傅家、賈家兩莊跟陳吃大戶的農民有“賈一連、傅一團”之稱。?寧縣志編輯委員會:《寧縣志》,第411頁。
30年代初,隨著土匪的增多,一些地方農民自發組成民團,試圖保護一方平安。如寧縣有上五社民團、中五社民團、北八社民團、東三社民團等,每個民團都有一個群眾舉薦的團頭。這種民團無事人各在家中,一旦有事,幾個團頭商量后,擊鼓為號,就會把民團集中起來。①《李志合1984年5月20日談農民自發斗爭》,劉鳳閣、任愚公主編: 《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345頁。這些民團又被地方軍閥看中,成為擴充實力的目標。如隴東軍閥譚世霖為擴充實力,給活動在慶陽各村鎮的民團“××營”的番號,“一律歸他管轄”②《黃金貴談太白收槍》,劉鳳閣、任愚公主編:《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第330—331頁。。不僅使這些民團有了“合法”的外衣,也可以從地方軍閥那里獲得一些彈藥和給養補充。
美國中共黨史研究學者馬克·塞爾登說:陜甘交界的黃土高原“遠離省內主要權力中心,長久以來成為武裝流寇的理想之地”③〔美〕馬克·塞爾登著,魏曉明、馮崇義譯:《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第11—12頁。。因此,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民團、農民武裝是占據陜甘鄉村社會的核心力量,中共陜甘邊政權和紅軍的建立,既利用了這里溝壑縱橫的地理環境,也利用了在這里興起的民團與農民武裝。
二、民團、農民武裝與陜甘邊紅軍的建立
關于民團與農民武裝,毛澤東指出:“游民無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斗,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④《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頁。在中共建軍初期,就比較重視對民團和農民武裝的改造。1927年9月27日,中共陜西省委針對改造農民武裝問題指出:“土匪原來是破產的農民,被鄉村封建階級不斷的經濟壓迫,不得已才上山的。只要運用得當,他們的確是貧農的好朋友,是農村階級斗爭中別動的生力軍。應擇其可以引上革命途徑的誠懇的與之聯絡。”⑤中央檔案館等: 《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7—1929》,甲2,1992年1月印行,第198頁。1929年6月,中共中央要求陜西省委“加緊土匪中的工作,因目前大批的災民都投入土匪中去,黨要深入群眾中去,獲得群眾,使之變成農村的武裝”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頁。。劉志丹在建立陜甘邊紅軍的過程中也指出:“現成的辦法是把各種民間的武裝和敵人的武裝變成革命的武裝。”⑦《劉志丹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77頁。因此,爭取民團和農民武裝是中共創建軍隊時的主要策略,也是陜甘紅軍創建過程中的主要方式。
1929年四五月,中共陜北特委在紅石峽召開會議,指出武裝斗爭有三種形式,即白色的(兵運)、灰色的 (改造土匪)、紅色的 (建立革命武裝)。會議決定派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打入國民軍隊進行兵運工作。⑧《劉志丹紀念文集》,第622頁。劉志丹在擔任陜北特委軍委書記期間 (1928年秋至1930年秋),動員大批中共黨團員和外圍青年,打入陜北高自清、楊庚午,甘肅譚世麟,寧夏蘇雨生等地方民團部隊中,進行兵運活動。1930年春,蘇雨生投靠楊虎城,劉志丹、謝子長離開了蘇雨生。在此前后,謝子長、劉林圃、習仲勛等分別發動了靖遠兵變、乾縣兵變、兩當兵變等,先后都失敗了。習仲勛在總結兩當兵變失敗原因時指出:“政治上不懂得聯合政策,沒有和當地的哥老會、有進步傾向的軍隊、民團搞聯合,走到一個地方連雞狗都跑光了,陷于孤立。”⑨中共陜西省委、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第246頁。經過多次兵運失敗后,劉志丹等人把建立軍隊的重點放在收編地方軍閥、民團及農民武裝方面。
1929年秋,劉志丹、王子宜等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合法取得了保安縣 (今志丹)民團的領導權,⑩《劉志丹紀念文集》,第248頁。馬克·塞爾登對這件事情做了十分有趣的描述:“劉志丹在王子宜和曹力如的支持下著手軍事問題,尋求在他的家鄉控制民團。劉的當地人事關系,使他可以直接和縣長談話。精心策劃的談判之后,通過游說當地學生,獲得大戶地主人家的支持被證明是關鍵性的。劉志丹變成了民團司令,曹力如成為副司令。” 〔美〕馬克·塞爾登著,魏曉明、馮崇義譯: 《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第45頁。在以后的多次軍事活動中都是以保安縣民團為骨干力量。1930年春,劉志丹離開蘇雨生部后,“準備在甘肅民團隊伍中搞點勢力”。①《馬錫五1959年4月23日談劉志丹的革命活動》,《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第306頁。劉志丹把目標盯在隴東民團譚世麟和由民團發展起來的地方軍閥陳珪璋部。當時,譚世麟任隴東民團司令,急于擴大實力。劉志丹的黃埔軍校出身深得譚世麟青睞,劉志丹利用這層關系與譚進行談判,譚給劉志丹以補充第2團的名分,謝子長任團長。部隊由自己組建,謝子長從楊庚午拉出來的周維琪1個營,靖邊張廷芝民團1個營,劉志丹控制的保安民團1個營②《姜兆瑩1985年9月9日談陜甘邊革命武裝的創建》,《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 (上),第320頁。。不久發生三道川事件③1930年夏季,剛剛組建起來的隴東民團補充團駐在慶陽北部三道川,張廷芝設計收繳了周維琪營的槍,又襲擊了劉志丹營,以保安縣民團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武裝在這次事件中遭受巨大損失。,劉志丹利用譚世麟民團發展隊伍的計劃受挫。
三道川事件后,1930年10月1日,劉志丹打著隴東民團譚世麟騎兵第6營的旗號,以到合水縣太白鎮補充糧草為名,從保安縣民團中抽調了幾名骨干,收繳了隴東民團第24營的槍,打死營長黃毓麟,獲得了50余支槍和10余匹騾馬,這是一次比較成功的收槍活動,為組建南梁游擊隊奠定了基礎④最近幾年的研究中,把這次行動稱之“太白起義”,甚至稱是“打響了反對國民黨在隴東反動統治的第一槍”。其實,這就是一次收槍行動。第一,這次行動沒有任何政治綱領,就是利用譚世麟騎兵第6營的名義,獲得黃毓麟的信任,收繳了該營的槍支與馬匹,收槍之后也沒有打出共產黨和紅軍游擊隊的旗號,故不具備起義的特質。第二,黃毓麟民團并不是國民黨的部隊,只是在動亂年代成立的地方民團,被譚世麟委以隴東民團第24營番號。故打死黃毓麟,收繳該營槍支,根本談不上是“打響隴東地區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
1930年前后,活動在陜甘邊界的農民武裝主要有趙連璧 (即趙二娃)、楊培盛、賈生財和唐清山等。趙連璧與劉志丹是姑表親戚,年幼喪父母,在劉家當雇工11年,后被張廷芝民團拉去,逃跑后又在陳珪璋部下當兵,搞了幾支槍回家要與劉志丹一起干。劉志丹讓他到合水太白一帶活動。趙連璧的膽子大,槍法好,有活動能力,南梁一帶土匪、民團“都歸他管”。⑤《王世泰同志在邊區歷史座談會上的講話》(1945年7月17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陜甘邊區·隴東部分》,中共慶陽地委黨史辦1986年5月印行,第110頁。楊培盛、同守孝兩人是米脂人,以販皮貨為生。楊培盛在皮貨遭到民團搶劫后,與同守孝組織了一支100余人的武裝,活動在慶陽南梁、二將川一帶。⑥《楊培盛1985年8月談南梁游擊隊》,《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第338頁。賈生財是橫山人,逃荒到合水縣蒿咀鋪,先在隴東民團當兵,先后任班長、排長,后來自己拉起了四五十人的民團,一直與劉志丹保持著聯系。唐清山原籍河南,逃荒到西華池附近,組織的饑民武裝活動在合水瓦崗川一帶。⑦《張占榮1985年4月11日談陜甘邊革命武裝的創建》,《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第327—328頁。這幾股農民武裝的領導人與劉志丹關系密切,劉屢次派他們出去搞武裝,故“每當志丹的武裝活動失敗后,還有趙二娃等的武裝可以依靠,于是很快地就又搞起來了”⑧《馬錫五1959年4月28日談劉志丹的革命活動》,《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第310頁。。
1931年初,劉志丹聚攏的民團與農民武裝被謝牛打散后,趙二娃、楊培盛、賈生財等再次回到陜甘交界地區活動,又發展起來了。其中趙連璧、同守孝有200余人,楊培盛有幾十人,賈生財利用社會關系在合水東區搞到民團團總的合法名義,駐在蒿咀鋪。⑨《劉景范1983年5月16日談陜甘邊早期革命武裝斗爭》,《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第314頁。劉志丹在合水脫險后,先到賈生財民團,后又到趙連璧部隊,接著又到平定川倒水灣楊培盛的駐地。在這里通知趙連璧等舊部前來匯合,并進行了整編,將全部人馬編為3個大隊,趙連璧、楊培盛、賈生財分別擔任大隊長,劉志丹任總指揮,全部人馬大約有400人,300多條槍。這支由民團、農民武裝組成的隊伍是南梁游擊隊最基本的力量。
活動在陜北的“土客隊”(保護鴉片貿易的武裝)也加入到中共領導的隊伍中來。1931年9月,原來活動在山西呂梁山區的晉西游擊 隊30余人,在黃子文等人帶領下渡過黃河,到達陜北。10月,在安定 (今子長)縣北區遇到從山西來到陜北楊琪、師儲杰等的“土客隊”,因閻紅彥、白錫林曾在“土客”中做過工作。①山西省社科院歷史所:《山西革命回憶錄》第2輯,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8頁。因此,楊、師要求與晉西游擊隊一同活動,在接受了約法三章 (一是聽從隊委領導;二是不搶窮人東西;三是不強奸婦女)后,與晉西游擊隊合并行動,共約300余人,師儲杰任大隊長②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黨史資料專題研究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131—132頁。。10月底,師儲杰大隊到南梁與劉志丹的南梁游擊隊會合,共計有700余人。為了解決部隊給養和立足的問題,劉志丹、謝子長等領導本想掛靠在陳珪璋部,但陳表示冷淡,“沒搞得成”,③《馬錫五1959年4月28日談劉志丹的革命活動》,《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 (上),第310頁。另據劉景范講述,1931年11月,謝子長與高崗從平涼來到南梁,謝子長與陳珪璋進行了談判,把部隊編為陳部第11旅,謝當旅長,劉當副旅長,部隊編為兩個團,1團長師儲杰,2團長劉志丹兼任,并派馬云澤到平涼辦理編制與軍服事項。當時,接到中共陜西省的指示,獨立建立武裝,決定成立西北反帝同盟軍。參見《劉景范1983年5月16日談陜甘邊早期革命武裝斗爭》,《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第315頁。又據吳岱峰回憶,是“劉志丹當時在自稱隴東綏靖司令的陳珪璋部補了個十一旅旅長的名義。這時,陳珪璋派劉寶瑩 (系陳珪璋某旅副旅長)來南梁找劉志丹,企圖收編南梁一帶的武裝。劉志丹利用這個機會,派馬云澤為他的代表,到甘肅平涼與陳珪璋交涉,并借機要些服裝,以解決部隊的過冬問題”。參見吳岱峰:《陜甘邊革命武裝的創建和發展》, 《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第422頁。這件事究竟是謝子長的建議還是劉志丹的想法,還需要進一步考證。就活動在陜甘交界地區,以打土豪保障部隊給養。以這支隊伍為基礎,1932年1月,在甘肅寧縣柴橋子成立了西北反帝同盟軍。
紅26軍建立后,不僅面臨著國民黨地方武裝力量的威脅,也面臨著活動在陜甘邊界地區民團和農民武裝的威脅。因此爭取和改變周邊民團、農民武裝是紅26軍的主要政策。爭取黃龍山農民武裝郭寶珊部可稱典范。郭寶珊原籍河南南樂,逃難到陜西洛川縣落戶,由于受到官府和豪強欺凌,1931年2月,拉了一些貧民投靠黃龍山土匪梁占魁、賈德功,被封為營長,“但與賈、梁貌合神離,自成系統”。1932年,劉志丹、謝子長等率部打韓城時,黃龍的“山大王”也參加了戰斗,這時郭寶珊已經了解到紅軍是打富濟貧的,劉志丹專為窮人做事,就產生了與劉“交朋友的念頭”。④黃羅武口述,張俊祥整理:《從“土匪”到司令》,《黃龍文史資料》第1輯,第29頁。郭寶珊認為“紅軍是打富濟貧,反對苛捐雜稅,殺貪官污吏,和我的想法一致,思想上有向往之意”,于是他的隊伍自立為“義勇軍”⑤郭寶珊:《我的起義經過》,《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第610頁。。他讓部屬仿效紅軍只打“大戶”“財東”,決不允許損害貧苦百姓⑥王世泰:《陜甘邊根據地的武裝斗爭》,《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第357頁。。他也同情紅軍,同年6月紅軍南下失敗后,一些紅軍戰士、傷員返回照金,郭寶珊不但沒有為難,而且給予了方便。次年春,賈德功民團小頭目魏八娃帶領100余人到甘泉、富縣一帶搶劫,被紅26軍3團繳械,劉志丹給他們講了紅軍的政策,發給路費,放他們回家。魏八娃返回黃龍山后,大肆宣傳劉志丹“夠朋友,講義氣”,對郭寶珊影響很深。⑦楊茂堂:《回憶西北抗日義勇軍》,《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第613頁。1934年農歷六月初,劉志丹、王世泰派黃羅武去黃龍山與郭寶珊接觸,希望他能夠與紅26軍合作⑧黃羅武口述,張俊祥整理:《從“土匪”到司令》,《黃龍文史資料》第1輯,第25—43頁。。當時,郭寶珊也想投靠國民黨軍隊,“當正牌軍官”,對紅軍的收編舉棋不定。是年秋,楊虎城部馮欽哉第24師“圍剿”黃龍山,郭寶珊撤離黃龍山。當郭到達合水時,劉志丹派馬錫五送去了慰問品和3匹馬。⑨郭寶珊:《我的起義經過》,《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第610—611頁。10月20日夜郭寶珊到達慶陽北部,宣布參加紅軍,其部被編為“西北抗日義勇軍”。在郭寶珊的影響下,其他一些土匪也投靠了紅軍。⑩《馬佩勛談西北抗日義勇軍》,《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第379頁。
除了郭寶珊外,陜甘邊紅軍還收編了一些小股民團和農民武裝。1933年9月,寧縣農民何炳在平子鎮殺了縣政府催糧官及團丁后,組織了一支農民武裝,打富濟貧,被紅軍收編后,組建了陜甘邊工農紅軍第三路游擊指揮部第4支隊,①《李德祿、羅金財、劉永康談平子游擊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陜甘邊區·隴東部分》,1986年印行,第220頁。次年夏編入紅26軍第1團。1933年7月,中共耀縣縣委組織農民群眾,收繳了北區趙連璧民團的槍,遣散了民團,組成了耀縣游擊隊,有百余人,旋即編入陜甘工農紅軍游擊隊第3支隊,同年11月編入紅26軍第3團。②張邦英:《照金根據地及耀縣武裝斗爭情況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 (下),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685頁;耀縣志編纂委員會:《耀縣志》,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年,第310頁。寧縣平子鎮在抗捐抗稅中建立的農民武裝有六七十人,1933年11月,槍殺當地地主趙新玉兄弟后,投奔紅軍,編為陜甘紅軍第三路游擊隊寧縣第三支隊③劉永培:《回憶紅軍游擊隊寧縣第三支隊》,《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下),第838—845頁。。同年10月至1934年春節,紅軍先后繳了南梁寨子劉團頭、閻洼李家溝門趙福奎、東華池張世弟、林錦廟馬建有、慶陽城壕川王洼子地主武裝、義正川高臺寨子高團總、洛河川旦八寨子曹俊章等民團槍④劉約三:《西北紅軍的創建》,《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下),第809頁。。春節前后,劉志丹率紅軍突襲耀縣,在路途收編了黃龍山土匪楊謀子部五六十人⑤王世泰:《回憶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下),第717頁。。夏季,中共地下黨欒新春、賀吉祥等打入子長縣折可達民團,并使其民團一部分嘩變,組建了紅軍游擊隊第8支隊;秋季,地下黨員李廣生、苗海水等人將該民團所剩40余人全部拉出,編入紅軍陜北獨立1團3連;12月,打入黃天錫民團內部的紅軍封德俊組織嘩變,打死黃天錫及其兒子,率團兵投奔紅軍,編入陜北獨立1團⑥強鐵牛:《子長國共軍隊及戰斗概況》,《子長文史資料》第2輯,1990年8月,第71—72頁。。這些民團、農民武裝的收編或繳槍,不僅解決了部隊裝備的問題,也壯大了紅軍隊伍。
劉志丹是把活動在陜甘交界處一些民團和農民武裝引向革命的關鍵人物,因他是土生土長的陜北人,熟知陜甘交界地區的社會情況與民風,知道如何同地方政府與軍閥、民間會社(如哥老會)和民團、土匪打交道,采取靈活多變的方式維系著這支部隊。如《大公報》記者范長江也說:劉“最熟悉地方農民痛苦,他同時受過黃埔時代新的政治訓練,并受過共產黨組織的熏陶,所以他的活動,有目標、有方法、有組織,把個人主義的綠林運動,變為與社會合為一致〔的〕社會運動。”⑦范長江: 《中國的西北角》,天津大公報館,1936年,第118頁。有兩件事情能說明劉志丹在這方面的能力,第一件事情是1931年初,在給養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劉志丹利用他與哥老會的關系⑧為了使陜甘邊紅軍有更大的生存空間,劉志丹和一些哥老會大爺交了朋友,哥老會的人見了劉志丹都稱“劉大爺”,見面也行哥老會的拜見禮。參見張策:《共產黨人的光輝榜樣——為紀念劉志丹同志犧牲五十周年而作》,中共慶陽地委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群眾領袖 民族英雄》,1986年印行,第19頁。,派馬錫五 (哥老會的行衣大爺)聯系到當地哥老會大爺羅連城,送給羅200兩大煙土,羅幫助劉志丹隊伍購買了許多子彈、大米、白面,⑨《劉景范1983年5月16日談陜甘邊早期革命武裝斗爭》,《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第313頁。不僅使處于危險中的弱小隊伍轉危為安,而且與其建立了“互不侵犯”的統戰關系。第二件事情是西北反帝同盟軍成立后,部隊來源復雜,既有閻紅彥、楊重遠等從山西帶來的晉西游擊隊的骨干力量,又有楊琪和師儲杰等土客武裝,還有一些劉志丹收編的民團、農民武裝。在這種情況下,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等商議,決定采用“拜把子”⑩在陜甘邊紅軍初創時期,“拜把子”是維系部隊關系和建立紅軍武裝的方式之一。1930年5月,劉志丹在陳珪璋暫編13師做兵運工作時,就與陳珪璋、謝子長、劉寶堂等18人結為異姓兄弟,劉志丹起草了《結盟誓詞》:“我兄弟情投意合,結為金蘭。在中國革命戰線上,共同奮斗,始終不渝。如有中途背叛者,天誅地滅。此誓。”參見《劉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頁。又如閻紅彥曾與靖邊土匪頭子張廷芝也“結拜過金蘭兄弟”。參見王子宜:《和劉志丹相處的日子》, 《劉志丹紀念文集》,第250頁。的舊形式來團結各方面的力量。按照年齡排列了“八大兄弟”,即師儲杰、楊琪、楊仲遠、謝子長、劉寶堂、劉志丹、馬云澤、閻紅彥。①馬云澤:《創建陜甘革命武裝的回憶》,《紅軍初創時期游擊戰爭·回憶史料》,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第628頁。這種方式在當時是比較管用而且可行的策略。
總之,中共在陜甘邊領導的最早的游擊隊就是由活動在南梁的民團、農民武裝和活動在陜北的“土客隊”組成的;紅26軍建立后,先后收編了黃龍山的“山大王”郭寶珊以及一些小股農民武裝。這些民團、農民武裝是組成陜甘邊紅軍最基本的力量。1934年11月7日,在紀念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日子,成立了陜甘邊蘇維埃政府。此時陜甘邊紅26軍擁有4個正規團1000余人,游擊隊也發展到1500余人。②吳志淵:《西北根據地的歷史地位》,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50頁。
三、對陜甘邊紅軍的影響
在陜甘邊紅軍初創和壯大的過程中,兵源主要是民團、農民武裝,部隊的成分十分復雜。據對紅26軍調查,在部隊的成分中工人占5%,雇工占50%,貧農占20%至30%,其他占20%,“因為部隊工人成分很少,所以農民意識特別濃厚”③《紅26軍1934年6月20日給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第262頁。。這支隊伍人員五花八門,思想也不一致,有想真正跟著干革命的,有想發財的,“也有借這個攤子哭他的恓惶”的④《姜兆瑩1985年9月9日談陜甘邊革命武裝的創建》,《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第324頁。。這支以收編民團、農民武裝組成的部隊,面臨著兩個最主要的問題。一是部隊的紀律問題。個別原來民團和農民武裝的頭目,有吃、喝、嫖、賭、抽、搶的習氣,對紅軍的紀律、宗旨和政策不了解,故紀律成為這支隊伍的要害問題。二是紅軍給養的問題。陜甘邊紅軍初建過程中,給養主要通過兩個途徑獲取,一個是在沒有打出紅軍旗號前,為了獲得糧餉和裝備,數次與陳珪璋談判,求其收編;一個是通過打土豪的辦法獲得補給,但初建的游擊隊與紅軍對土豪的標準不甚了了,多次發生見財物就搶的情況。
因此,在紅軍初建時期,部隊屢屢發生違反紀律甚至搶劫、殺害民眾的事件。1931年臘月初,剛剛會師不久的部隊路過寧縣盤客任家堡子時,遇到當地民眾的抵抗,還沒有等到部隊領導下命令,士兵就一窩蜂似地攻入了堡子,“結果打、砸、搶了個一塌糊涂。堡子里的男人打死打傷不少,女人被強奸,大姑娘嚇得用煤煙子把臉抹得黑黑的”⑤馬佩勛:《深切懷念子長同志》,《子長文史資料》第2輯,第142—143頁;又據張占榮回憶,在這次行動中一支隊殺了荏掌堡子 (任家堡子)里的21名群眾,高崗對此事進行追查,是一支隊戰士郭立本帶頭干的。參見《張占榮1985年4月11日談陜甘邊革命武裝的創建》,《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第329頁。。部隊駐陜甘交界的新堡、柴橋子、三嘉原期間,第2支隊不斷發生夜間外出搶劫事件,商店、腳戶、客商、糧食、布匹、騾馬等“什么都往回拿”,甚至“不分貧富見財就搶,見婦女就強奸,群眾怨聲載道,旬邑縣地方黨也有反映”⑥李維鈞:《戰斗中成長的陜甘游擊隊》,《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第490—491頁。。臘月二十四日,為了解決部隊糧食問題,派人出去打土豪,趙連璧在打土豪的過程中搶了永和集,“在雙佛堂一帶連一般老百姓的豬肉吊子都提來了”,還拉了100多頭毛驢回來,群眾找部隊領導反映:“趙連璧搶了他們的毛驢,見誰的拉誰的”⑦《張占榮1985年4月11日談陜甘邊革命武裝的創建》,《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 (上),第329頁;雷恩鈞: 《從晉西游擊隊到西北反帝同盟軍回顧》,《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第486頁。。紅軍陜甘游擊隊成立后,也不時發生搶劫事件。1932年7月,在陜甘邊界遭到“圍剿”后,游擊隊到了陜北“將群眾吃的一掃而光”,所過路途,“群眾望風遠逃”,“百姓罵為土匪”⑧《高崗1932年11月29日關于陜甘游擊隊情況給陜西省委的報告》, 《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第213頁。。在陜北,從黃龍山收編來的農民武裝紀律也比較差,“每住一個地方,殺豬、宰羊,擾得百姓不得安寧”⑨《王四海1986年11月6日談保安游擊隊、紅二團》,《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第374頁。。這些事件的發生,說明早期游擊隊有傳統農民起義和綠林習氣①其實,這種現象并不完全發生在陜甘邊游擊隊身上,在鄂豫皖紅軍建立的早期,“存在相當多誘奸甚至強奸婦女的行為,而且這種行為還發生在很多高級干部身上”。參見張永:《鄂豫皖蘇區肅反問題新探》,《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正如馬克·塞爾登所言:“共產黨領導的農村游擊隊與陜北山里眾多反叛和秘密社會小團體,不僅僅在不滿軍閥和地主權勢上一致,特別是在較早年月,他們經常從事綠林好漢行動——劫富濟貧。他們的突襲策略和撤返山區與其他反叛團體并無二致。”②〔美〕馬克·塞爾登著,魏曉明、馮崇義譯:《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第50頁。這種與民團和農民武裝“并無二致”的做法,把劉志丹等紅軍領導人推到了最尷尬的地步,并且產生了嚴重的后果。
第一,游擊隊兩位主要領導人劉志丹與謝子長之間發生了嚴重的爭執與分歧。爭執與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核心問題上。第一個核心問題是要不要打紅旗。根據閻紅彥的說法,劉志丹主張不打紅旗,理由是“當時條件不成熟,時機未到,自身力量還小,公開打紅旗會引來敵人的進攻……利用軍閥名義,發展自己的力量,等到時機成熟了再打紅旗”。謝子長主張打紅旗,理由是“采取這種依靠民團、土匪武裝,在軍隊中搞上層活動的方法,黨的武裝始終是搞不起來的”,并認為當時有成立紅軍的條件,“堅決主張公開打紅旗,用鮮明的旗幟,號召群眾,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在爭論中,支持謝子長意見的是少數,支持劉志丹意見占多數。③閻紅彥:《關于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和繳劉志丹的槍的關系與事實經過》 (1963年12月23日),陜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4434/13/12/73。因此,1932年1月,這支部隊改名為“西北反帝同盟軍”,中共陜西省委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成立西北反帝同盟軍“完全是他們自己干的,并不是根據省委指示”。為什么叫反帝同盟軍?陜西省委給中共中央的解釋是:“因各部隊太復雜,都是過去的土匪、流氓無產階級,到處充滿亂搶亂燒,不敢揭出工農游擊隊和‘紅軍’等名義,恐怕在群眾中信仰倒地。”④中央檔案館、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2年2月15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2年 (一),1992年印行,第16頁。
第二個核心問題是如何整頓這支部隊的紀律。劉志丹、謝子長都認識到新組建的隊伍需要整頓,但分歧在于如何整頓。劉志丹主張“采取教育、改造為主的辦法,不堪改造的個別清理”;謝子長主張“對那些成分復雜不可靠的部隊,該繳械的繳械,該解散的解散,該槍斃的槍斃”⑤《劉景范1983年5月16日談陜甘邊早期革命武裝斗爭》,《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上),第316頁。。關于打不打紅旗、如何改造部隊的問題上,在與劉志丹談不攏的情況下,發生了劉志丹部下趙二娃搶劫群眾的惡性事件。為了解決部隊紀律問題,謝子長召開了中共黨員組成的隊委會,未讓劉志丹參加。會議認為:“劉志丹部則多是本地人,土匪、民團、哥老會、大煙鬼較多,到處拉票搶人,紀律很壞,雖然有幾個黨員 (如魏佑民、劉約三等),但都沒有實際權力,加上志丹同志堅決不同意打紅旗,對這個部隊,一點把握都沒有。因此就決定先解決劉志丹部趙二娃、楊培勝 [盛]等人的槍。”如何來解決劉志丹領導的第二支隊?會議研究決定:“在駐地三嘉原,以集合部隊出發為名,出發前由總指揮謝子長講話,講話結束后立即繳劉志丹部的槍,并規定對志丹同志不能出問題,只打死趙二娃一人,其他不動。”⑥閻紅彥:《關于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和繳劉志丹的槍的關系與事實經過》 (1963年12月23日),陜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4434/13/12/73。這是一次由謝子長主持召開的解決劉志丹第2支隊的秘密會議,因布置嚴密,劉志丹等毫無察覺。由于收編來的民團、農民武裝屢屢發生搶劫事件,引發了打不打紅旗與如何改造部隊的問題,兩位主要領導人發生了嚴重的分歧。1932年2月6日,發生了三嘉原事件,謝子長繳了劉志丹第2支隊的槍。⑦黃正林:《1935年陜甘邊蘇區和紅26軍肅反問題考論》,《史學月刊》2011年第6期。
第二,影響了中共陜西省委、中共北方局對劉志丹和陜甘邊紅軍的評判。三嘉原繳槍事件發生后,陜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報告:劉志丹的“第二支隊純系土匪集合而成……時常防備其嘩變偷走,而各大隊土匪都占絕大多數,在第二大隊有洋煙燈八十余架,這些即可證明成分的好壞”;第2支隊“時常外出搶人,奸淫婦女,與土匪毫無分別”①《陜甘游擊隊材料之六 (二月十二日至三月二十日)》, 《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2年 (一),第118—119頁。。在中共陜西省委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把西北反帝同盟軍第2支隊完全定位為土匪,因此肯定了這次繳槍行動。即便陜甘邊紅軍游擊隊成立后,中共陜西省委在各種場合也認為這是一支由土匪組成的隊伍,批評之聲不絕于耳。1932年6月,中共北方局召開會議,中共陜西省委代表在會議上講:劉志丹部都是土匪, “劉是同志,黃浦 [埔]學生,渭華暴動時任過總指揮,軍事委員會主席,陜北特委書記,以后和黨無形脫離關系”。三嘉原繳槍后成立的紅軍陜甘游擊隊,“除在旬邑吸收了很少數的一部分農民以外,大部分還是老土匪,直到現在土匪還占二分之一以上”。②《陜西代表杜勵君在北方會議上的報告——關于陜甘游擊隊產生、“四二六”罷課與黨的策略、白軍兵變、士兵工作、省委及各地的工作概況等》(1932年6月2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2年 (一),第200—202頁。9月17日,中共陜西省委批評游擊隊的嚴重錯誤與弱點時,指出“干部的提拔不是從可靠的工農分子與共產黨員而是純粹軍事作戰上的老土匪”③《陜西省委關于邊區軍事計劃——粉碎敵人對陜甘邊的四次“圍剿”》(193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收文時間),《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2年 (二),1992年印行,第59頁。。因此,中共陜西省委要求:“堅決的立刻撤換現在游擊隊中的土匪流氓、公開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指揮員。對于現在游擊隊中的土匪成分,應該毫不遲疑淘汰出去。”④《陜西省委關于帝國主義國民黨四次“圍剿”,創造陜甘邊新蘇區及紅二十六軍決議案》 (1932年8月25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2年 (一),第444頁。在中共陜西省委領導看來,這支隊伍充其量是一支得到群眾贊揚的“好土匪”而已⑤《陜西省委關于陜甘邊境游擊隊指示信》 (1932年1月20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2年 (一),第3頁。。
紅軍陜甘游擊隊改編為紅26軍后,并沒有改變中共陜西省委對紅26軍的“壞印象”。紅26軍大多數成員來源于原西北反帝同盟軍和紅軍陜甘游擊隊,中共陜西省委認為這些人“出身”不好,不能執行黨的路線,多次要求中共中央派軍事、政治干部到紅26軍工作。就在紅26軍成立之初,“因為勵君 (即杜衡)對軍事不懂,團長 (即王世泰)對領導也沒辦法,整個形成了志丹參謀長個人意見,所以建議省委很快的派遣政治軍事人才到部隊來”。⑥《金理科給省委的報告 (第一號)——關于紅二十六軍及邊區工作概況》(1933年□月2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3年1—3月,1992年印行,第143頁。1933年3月23日,中共陜西省委向中央提出“最好派三個得力軍政干部來,做政委、團長與參謀長”⑦《中共陜西省委關于改造省委與紅二十六軍干部問題向中央的請示報告》(1933年3月23日),《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第188頁。。盡管劉志丹留在部隊中,但陜西省委認為他不適合做上述三個職務。劉志丹在紅軍和民團、農民武裝中有很高的威信,所以在渭北開展工作時,收編了當地一些農民武裝為地方游擊隊。⑧《渭北特派員拓夫關于渭北黨的工作情況給省委的報告》(1933年2月6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3年1—3月,第185頁。但受到中共陜西省委的指責,認為“用改編土匪的辦法代替了在斗爭基礎上組織游擊隊工作。當時在游擊隊指揮部下有十幾個游擊隊,這些游擊隊是怎樣 (的)東西呢?都用[是]游擊隊用委任狀改編的土匪,不論什么人來一報名,于是就給他一張委任狀,編為多少多少支隊,因此,雖在名義上有幾十隊,但有很些[多]指揮部根本就沒有見過。這些土匪部隊利用我們的紅旗到處隨意勒索群眾,奸淫擄掠無所不為,群眾謂之‘假紅軍’”。⑨《陜西省委給中央的工作報告》1933年11月25日(收文時間),《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3年4月—1936年,1992年印行,第244頁。這些成為中共上級機關評判陜甘邊紅軍時抹不去的陰影。
1934年6月,中共駐北方代表對以劉志丹為核心的紅26軍領導集體并不滿意,認為紅42師有兩個最嚴重的問題:一是“現在干部能力最差,一般同志政治水平低”;二是“脫離省委領導與地方黨沒有聯系”,因此“要求中央派軍事、政治干部來加強紅四十二師的領導”①《中共上海中央局駐北方代表關于紅二十六軍情況向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匯報》(1934年6月20日),《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第223頁。。同年7月,陜甘邊與陜北黨政軍在南梁閻洼子召開的聯席會議上,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的信中指責紅26軍是“右傾機會主義” “逃跑主義”“梢山主義” “槍桿子萬能”,有“濃厚的土匪色彩”②郭洪濤:《郭洪濤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第46頁;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74頁。。會后不久,謝子長寫信給中央駐北方代表,一方面指責“四十二師一貫的是軍事亂竄,不能在艱苦的群眾工作中完成西北蘇區的任務”,一方面“要求中央派軍、政同志領導四十二師,把老右傾同志另外調換工作,才是根本轉變二十六軍的辦法”③《謝子長致中央駐北方代表的信》 (1934年9月5日),《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第232—233頁。。陜北特委書記郭洪濤批評紅26軍的游擊隊是“招兵買馬拉土匪流氓”建立起來的,陜甘邊特委執行富農路線,“對于政治形勢的估計不足和一貫右傾”等④郭洪濤:《紅二十六軍長期斗爭的主要教訓》(1934年8月),陜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5412/13/23/24。。1935年1月,陜北特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再次指責紅26軍執行的是“土匪路線”,“不能正確地站在勞苦群眾利益上開展群眾斗爭,吸收最好的勞苦群眾參加,所以征收的戰斗員許多是流亡 [氓]分子,經常把槍扛上跑了”⑤《陜北特委給中央的報告——關于政治經濟、群眾斗爭及游擊隊情形、黨團組織等問題》 (1935年1月24日),《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3年4月—1936年,第444頁。。上海臨時中央認為劉志丹“思想很右”,于是7月至8月間,中共駐北方代表派朱理治、聶洪鈞到陜甘邊根據地,解決陜甘蘇區“右派反革命問題”⑥聶洪鈞:《劉志丹同志冤案的產生》,《革命史資料》第1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第112頁;朱理治:《往事回憶》,《朱理治紀念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443頁。。由此可以看出,在陜甘邊紅軍和蘇維埃建立的過程中,由于與上級和中共中央溝通存在問題,加之劉志丹領導的紅26軍主體是在改編和吸收了大量的民團、農民武裝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成長過程中發生了一系列違紀乃至搶劫事件,嚴重影響了上級領導對劉志丹和紅26軍的評判。
綜合上述,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陜甘大旱災,迫使一些無法生存的農民或組織民團自保,或落草為寇以謀生計。陜甘邊蘇區紅軍創始人劉志丹等利用自己在當地的特殊身分,收編了部分民團和農民武裝,使其成為陜甘邊蘇區初創時期紅軍游擊隊和紅26軍的主要兵源。但是這些收編來的民團和農民武裝在最初的革命活動中,出現了違反紅軍紀律的行為,猶如斯諾所言:“從我能收集到的一切超然的證據來看,似乎沒有疑問,在陜西頭一兩年的斗爭中,對官僚、稅吏、地主的殺戮是過分的。武裝起來的農民長期積壓的怒火一旦爆發出來,就到處打家劫舍,扣在他們的山寨里勒索贖金。”⑦〔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 《西行漫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64頁。正因為這樣,紅軍創始人和紅26軍被上級領導機關誤判,常常受到指責。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在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長征來到陜北之前,中共陜西省委、北方局乃至中央幾乎都把劉志丹和他的團隊看做是“右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梢山主義”“槍桿子萬能”,有“濃厚的土匪色彩”等,最后派代表親自到陜甘邊和紅26軍來解決劉志丹等人存在的問題,肅反的發生也就成歷史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