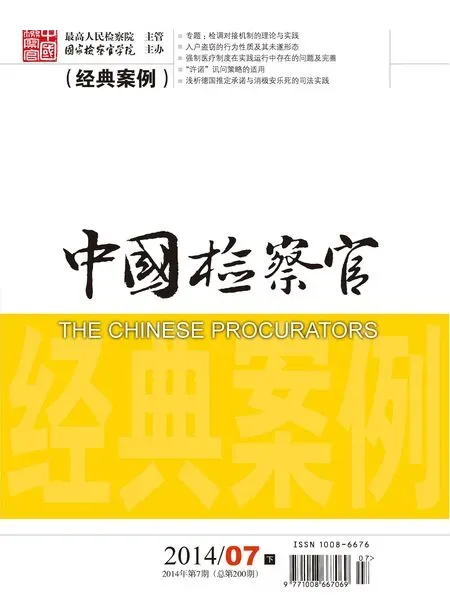機關單位聘用人員虛報冒領稿件獎勵費如何定性
文◎盛贊賀珊珊
機關單位聘用人員虛報冒領稿件獎勵費如何定性
文◎盛贊*賀珊珊*
一、基本案情
2008年1月,被告人劉某受臺州市某區公安分局聘用,協助該局宣教科從事宣傳稿件的撰寫、攝影、攝像等工作。2011年5月至2012年8月間,劉某利用單位報銷稿件獎勵費的有關規定(該局對宣傳稿件采用積分制,不同媒體錄用的稿件計分不同,每分獎勵5元,每位宣傳員根據每季度所發表稿件的積分領取獎勵費),虛填本人稿費獎勵費報銷單6張,合計人民幣61710元;虛填其他宣教員稿費獎勵費報銷單52張,合計人民幣305550元,并偽造審核人(宣教科長)的簽名,騙取分管局領導在報銷單上簽署同意報銷后,再以本人和順代其他宣傳員一并報銷稿件獎勵費的名義通過財務報銷,共非法獲取人民幣367260元。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劉某的行為構成貪污罪。主要理由是:劉某雖為國家機關單位聘用人員,但在國家機關單位從事宣傳報道等公務性工作,根據《刑法》第93條及2003年《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第1條“雖未列入國家機關人員編制但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視為國家工作人員”之規定。劉某受國家機關單位聘用從事宣傳報道等公務工作期間,利用單位稿件被媒體錄用后可以按照規定報銷稿件獎勵費的有關規定,通過虛構和偽造事實,騙取本單位財物合計人民幣367260元,利用了管理公共財物的職務之便,構成貪污罪。
第二種觀點認為,被告人劉某的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主要理由是:劉某系國家機關單位聘用的的勞務工,作為單位通訊員使用,從事的是撰寫新聞稿件等工作,沒有相應的職權,不具有行政管理職權,屬勞務行為,不宜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其利用該勞務工作之便,騙取本單位財物的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
第三種觀點認為,被告人劉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主要理由是:劉某系國家機關單位聘用的工作人員,在國家機關中從事文字宣教工作,撰寫新聞稿子,其利用工作形成的便利條件,虛構、偽造事實,虛報稿件獎勵費,騙取本單位錢物的行為,構成詐騙罪。
第四種觀點認為,被告人劉某的行為分別構成貪污罪和詐騙罪,應予數罪并罰。主要理由是:劉某系國家機關單位聘用的工作人員,在機關單位中從事宣傳報道等公務活動,其依照本單位規定報銷稿件獎勵費的制度,虛構、偽造事實,以本人報銷的名義騙取單位財物,計人民幣61710元的行為,構成貪污罪。而其虛構、偽造事實,以順代其他同事一并報銷稿件獎勵費的名義,騙取單位財物,計人民幣305550元的行為,是利用了其工作所形成的便利條件,其行為構成詐騙罪。故應以貪污罪、詐騙罪數罪并罰追究其刑事責任。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四種觀點,被告人劉某的行為分別構成貪污罪和詐騙罪,應予數罪并罰。
(一)被告人劉某由派遣公司派遣到國家機關從事宣傳報道等工作,屬于從事公務行為而非勞務行為,應視為國家工作人員
根據《刑法》第93條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從上述規定不難看出,國家工作人員的界定以是否從事公務為標準,而不再強調必須具備國家干部身份,也不以其是按照何種人事管理系列列編為標準。也就是說,如果行為人從事的是公務,雖不具有國家干部的身份也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反之,即使具有國家干部身份,但其從事的不是公務活動,也不能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
對于何為從事公務,《刑法》沒有明確規定,實踐中存在不同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同樣也沒有對公務的概念作出明確的界定,僅明確“從事公務是指代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履行組織、領導、管理、監督等職責”,強調“公務主要表現為與職權相聯系的公共事務以及監督、管理國有財產的職務活動”,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履行職責等。實踐中,判斷相關人員是否從事公務,主要看其對國有財物是否具有一定管理支配權,而不能單純審查其人事管理列編情況。也就是說,無論是國家機關中的人員,還是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的人員,或是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單位中的人員,都必須是從事公務才能認定為刑法概念上的國家工作人員。認定行為人是否是國家工作人員,能否以國家工作人員論,關鍵的是看他從事的是不是“公務”。
在刑法理論中,公務一直是與勞務相對而言的一個概念。所謂勞務,通常是指直接從事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活動和服務活動,是一種職業活動,而不是職務活動,它不具有國家的權力性、職能性和管理性。從理論上講兩者好像界限很清晰,但在實踐中,相當多的案件,仍然存在著行為人從事的到底是公務還是勞務的激烈爭議。
國家機關單位聘用人員從事本單位宣傳報道等活動是一種從事與職權相聯系的公共事務的行為。首先,本案中被告人劉某不是“獨立的撰稿人”,而是以所屬單位的名義從事業務活動,其從事的采訪報道、撰寫宣傳稿件等活動屬于職務行為,這在相關法律法規中有明確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16條的規定,公民為完成法人或者非法人單位工作任務所創作的作品是職務作品。據此,劉某經過采訪撰寫的宣傳稿子應屬于職務作品,其從事的本單位宣傳報道等業務活動,絕不是單純的“個體性的勞務”,而是以所屬單位名義進行的職務活動。其次,劉某從事的宣傳報道等工作,按照國家機關單位提出的新聞報道和宣傳要求從事采訪報道工作,與單位所代表的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息息相關,其行使的采訪、報道以及監督等權利的職務活動無疑是具備公務性質的。故劉某應視為國家工作人員,其實施的非法占有本單位財物的行為不宜認定為職務侵占罪。
(二)被告人劉某的行為分別利用了其本人依職責所賦予的職務之便和日常工作中所形成的工作之便
所謂“利用職務之便”,是指行為人利用自己在本單位所具有的一定職務、職責,即主管、管理、經手本單位財物的便利條件。“主管”,是指行為人對本單位的財物具有調撥、安排、使用的決定權,如單位負責人在職權范圍內對本單位財物進行處置。“管理”,是指行為人對本單位的財物直接負有保管、處理、使用的職責,即對單位財物具有一定的處置權,如單位的工作人員為履行職務行為所使用、產生的費用。“經手”,是指行為人既沒有對單位財物進行調撥、統籌、使用的決定權,也不具有管理、處置本單位財物的職權,但行為人對本單位財物具有實際控制權,如出納員直接收取、支付本單位現金。
所謂“利用工作之便”,是指行為人在日常工作過程中形成的為順利實現目的行為而產生的便利條件,如熟悉工作環境,出入方便等。這種便利不是職務本身所具有的,而是在履行職務過程中所形成的,稱為“工作上的便利”。
劉某受聘在國家機關單位中從事宣傳報道等工作,其對在開展宣傳報道等公務活動而產生的費用(包括報銷稿件獎勵費、差旅費等)享有一定的使用、處分的權利,是屬于對單位財物的一種管理行為,劉某以此利用職務之便虛構撰寫宣傳稿件被有關媒體錄用的事實,虛填6份本人稿件獎勵報銷單,偽造審核人的簽名,騙取分管財物的領導簽字后從財務處領取人民幣61710元據為己有的行為,構成貪污罪。
另根據聘用劉某機關單位的相關財務制度和該單位報銷稿件獎勵費的有關規定:報銷稿件獎勵費是要求各宣傳人員本人填寫,負責宣傳的部門領導核實審簽,統一報分管領導簽字同意后再到財務部門領取,劉某沒有代其他宣傳人員報銷稿件獎勵費的權限。而劉某利用實際報銷稿件獎勵費過程中,存在有宣傳員相互代填、帶簽、代領的現象和漏洞,利用熟悉獎勵費的報銷方式,了解相關人員存在不嚴格按照規定執行以及對其長期在單位工作形成的信任等便利條件,虛構同事撰寫宣傳稿子的事實,虛填52份同事稿件獎勵費報銷單,偽造審核人的簽名,以幫同事順代報銷的名義,騙取分管領導的簽名同意后,非法占有單位財物計人民幣305550元,其對該非法占有的財物并無直接控制與獨立支配的職責和權利,是利用了在工作中形成的便利條件而非本人職務上的便利,故劉某非法占有該305550元人民幣的行為構成詐騙罪。
綜上,被告人劉某的行為分別觸犯了《刑法》第266條、第382條之規定,構成詐騙罪、貪污罪,應予數罪并罰。
*浙江省臺州市椒江區人民檢察院[31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