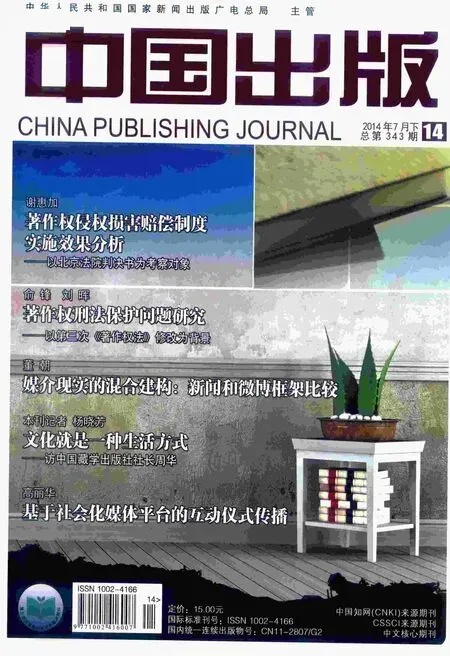涉外版權代理制與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
文/孟治剛
提升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是我國文化強國戰略建設的核心構成之一。作為國際版權貿易通行規則,涉外版權代理制能夠從版權貿易途徑配合版權宗主國國家文化戰略實施,推動版權文化產品國際輸出,擴大國際市場占有率,從而有助于體現國家意志在國際文化交流場域的表達力,獲得文化全球話語權,增強國際競爭文化資本優勢。因此其可以作為重要的文化貿易策略服務于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有效助推文化強國建設。
一、文化強國建設要善于依托涉外版權代理制
我國文化強國戰略建設的重要現實表征之一就是提升國家文化及價值觀念國際影響力,增強全球話語權優勢,增強國際競爭文化資本優勢,促進我國平等參與國際文化競爭交流合作。涉外版權代理制可以借助版權貿易方式將國家文化價值觀念內化至文化商品之中,并通過國際市場生產流通機制進行輸出,實現國家文化價值觀念的有效傳播與外擴。因而作為重要的文化戰略貿易實現策略,其可以有效承擔提升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的功能負載,是國家文化戰略在經濟貿易領域的隱性體現和運用。
1.涉外版權代理制的含義
根據我國國家版權局和國家工商管理總局共同制定的《著作權涉外代理機構管理暫行辦法》規定,我國著作權(版權)涉外代理即指著作權涉外代理機構以委托人的名義,在代理權限范圍內辦理涉外著作權中財產權的轉讓或許可使用以及其他有關涉外著作權事宜的民事法律行為。[1]涉外版權代理制是國際版權貿易高度市場化和產業化的結果,強調版權代理機構作為貿易行為主體之一,處于市場中心地位,在版權宗主國和輸入國的被代理人授權范圍內,對國際版權文化產品及資源進行整合協調,以版權被代理人名義從事對被代理人產生權利、義務的,包括版權許可使用與轉讓、版權法律咨詢、版權權益保障、資產營銷管理等在內的版權貿易業務活動。
2.提升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的必然選擇
首先,利用涉外版權代理制提升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已經成為國際通行慣例。從國際范圍看,主權國家提升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通常采取政治導向的直接文化輸出和經濟導向的文化貿易輸出兩種策略模式。前者一般由國家或政府機構直接擔任行為主體,意識形態特質明顯,使用不當可能會導致文化接受沖突,因而具有較強的國際文化和社會心理抗性;后者則通常以涉外版權代理制為中介,將負載文化價值觀念的版權文化產品以經濟貿易方式進行輸出,便于消解意識形態壁壘,顯示文化交流平等性,國際社會和異質文化認同度與接納度較高,往往被主權國家視為提升文化國際影響力的重要策略加以慣例化選擇實施。
其次,涉外版權代理制能夠為提升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提供專業化支撐。作為高度規范化和專業化的國際版權貿易規則,涉外版權代理制可以利用市場行為主體諳熟國際版權市場運行規則,了解貿易需求導向,擁有廣泛的市場和產品資源等專業優勢對市場區域、交易規模、實施過程等貿易要素進行控制管理,并在國家意志導向下進行資源整合、生產組織、產品配比、輸出效果監控等策略選擇,以保障在專業化支撐下實現國家文化價值觀念的系統性、規模化和高效率貿易輸出,從而促進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的提升。
再次,完善的涉外版權代理制本身就是展示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制度表征。作為國際版權貿易的重要運行規則,涉外版權代理制自身的發展完善程度、國際行業認可度與市場信用度是主權國家版權文化產業接軌國際版權貿易市場,進入國際生產流通體系,參與國際文化交流競爭的重要實力標志,它能夠從運行機制架構層面顯示主權國家對自身文化價值觀念的認知能力,對文化資源的整合協調能力以及利用文化貿易策略進行國家文化戰略實施的運作能力,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展示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制度表征。
二、涉外版權代理制策略運用的現實困境
相對于英美等文化輸出大國而言,我國現有涉外版權代理制具有發展歷史較短、行業理念認同度較低、基礎薄弱、體系不完善、專業化程度不高等缺點,使得利用版權文化貿易策略提升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的目標難以有效落實,涉外版權代理行業無法有效負擔提升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的社會職能。
1.國家層面缺乏理念認同
利用涉外版權代理制提升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已經成了國際共識和慣例,被主權國家作為實現國家文化戰略的重要文化貿易策略選擇。早在1961年10月,美國肯尼迪政府就以備忘錄形式明確要求美國電影國際版權代理公司進行海外影片輸出時應當配合政府“全球戰略”;而韓國政府建立的活力韓國、國家品牌委員會,日本政府酷日本室和民間內容產品海外流通促進機構等文化輸出機構也都緊密依托本國涉外版權代理機構,負責拓展國際文化市場,實現價值觀念國際輸出。布熱津斯基認為,“美國的民族文化吸引和很快同化了來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從而促進了國家力量的發展”。[2]而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國家層面對利用涉外版權代理制提升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缺乏理念認同,一直單純強調版權文化產品的意識形態屬性,對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策略的多元化特征缺乏認知,因而傾向于采納政治主導的直接文化輸出策略,往往依賴國家或政府行為進行國家文化價值觀念國際化輸出。但對由此帶來的意識形態阻滯性缺乏有效預測評估,往往難以獲得國際社會與異質文化的認同與接納,致使本國文化價值觀念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失語,削弱了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
2.涉外版權代理制尚未成為主導運營模式
英美等文化輸出大國一直重視構建完善的涉外版權代理制度,積極培育具有規模效益、高度專業化的涉外版權代理機構,以充分利用版權貿易策略進行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的國際輸出,提升本國文化國際影響力。例如,擁有700多家涉外版權代理公司的美國政府曾經4次通過修正《版權法》來鼓勵版權貿易和涉外代理機制發展;英國政府也通過出臺減免稅收等政策促進涉外版權代理發展,其涉外版權代理公司有200家左右。這些數量眾多、規模龐大及高度專業化的代理機構依據國家意志力,通過版權貿易方式有力推動了英美國家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提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依靠其經濟與軍事實力處于主導地位和霸權地位,他們力圖通過文化輸出與科技壟斷以及資本、技術、信息、市場等方面的優勢來維護一種持久的霸權”。[3]
而我國涉外版權代理制尚未成為版權貿易行業主導運營模式,無法介入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的具體實施。我國國際版權貿易缺乏專業化分工體系,市場運營行為大多由出版機構承擔,涉外版權代理機構被排除在市場機制之外,致使版權貿易成交額雖逐年遞增,但涉外版權代理機構業務并未實際擴展,涉外版權代理制尚未成為版權貿易行業主導運營模式。因此,在近年來“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中國電影海外推廣公司國際計劃”等重大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貿易項目中,市場行為主體仍然在國家導向下由出版機構直接擔任,涉外版權代理機構無法有效介入,難以以文化貿易市場行為主體身份承擔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的職責。
3.涉外版權代理行業基礎薄弱
提升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是高強度、大規模、系統性的重大國家文化戰略行為,往往需要依托那些具備規模優勢,組織完善、資金雄厚、人員充沛且能夠獨立有效行使國際版權貿易市場主體行為的機構負責運作。而我國現有版權代理機構僅30余家,從業人員不足100人,除中華版權代理總公司、廣西萬達版權代理公司等少數機構外,其他代理機構均實力較弱,無法形成行業規模效應。另外,我國涉外版權代理機構自誕生之初就被定位于出版附屬機構,掛靠在出版管理部門之下,除中華版權代理總公司、北京版權代理公司少數幾家是真正獨立法人和有限責任公司外,其余機構均大多依附于地方版權局或新聞出版局,在涉外版權貿易中僅扮演涉外聯系人角色,不具備獨立法人資格。這種規模劣勢和市場獨立主體缺位導致代理行業難以負載實施高強度、大規模、系統性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的文化戰略職能。
4.代理機構專業化程度較低
我國現有涉外代理機構專業化程度一直較低,無法為提升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提供常態業務運營支撐。首先,現有代理機構缺乏對國際版權貿易運營方式、市場規則、法律法規等層面的專業認知,在業務上與國際市場無法平等對接,難以為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提供針對性的專業化策略建議;其次,現有涉外版權代理業務大多僅圍繞圖書版權開展,而影視音像、相關版權衍生產品等領域都鮮有涉及,可控版權產品國際市場資源稀少,無法為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提供充分的價值負載平臺保障;再次,現有代理機構缺乏國際版權代理操作經驗,品牌效應薄弱;最后,行業整體缺乏國際市場信用機制,版權保護意識薄弱,易于造成國際版權貿易沖突,導致利用涉外代理機制實施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過程中經常遭遇貿易壁壘。
5.版權文化產業實力薄弱
英美等國利用涉外版權代理制提升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的前提條件是擁有強大的版權文化產業支撐,其能夠提供數量龐大、高品質的供全球文化市場消費的版權文化產品,為國家價值觀念提供多樣化負載平臺,使得涉外版權代理機構能夠在國家意志主導下將數量眾多、價值觀念明晰準確的版權文化產品輸入國際市場,提升國家文化影響力。“美國強大的文化產業不斷地傳播美國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不僅為美國帶來了巨額的經濟利益,而且也帶來了更重要的政治利益和國家文化利益”。[4]我國版權文化產業則受經濟科技等因素制約,未能實現生產規模效應,產品數量稀少,特別是生產主體對在商業文化產品中如何體現國家文化價值觀念表達力缺乏操作經驗,加之產品在內容形式、設計風格、表現手法等外在要素上不符合國際生產制作慣例,難以契合國際消費需求實際,導致能夠充分負載國家文化價值觀念的版權產品極為缺乏。受困于這種資源匱乏境況,現有版權代理機構只能將固有的、而非完全代表國家意志與文化價值觀念的版權文化產品進行被動性輸出,往往導致因為負載產品主體缺乏明確的文化價值觀念指向性而影響文化影響力提升效果,甚至可能由于所輸出文化產品中內化的價值觀念與國家意志立場相左,威脅國家利益。
三、利用涉外版權代理制的關鍵點
利用“涉外版權代理制”提升我國文化國際影響力,必須要從國家認知層面增強行業理念認同,實現行業高度市場化發展,完善行業運作制度建設與管理,推進文化創新和產業升級,從多個角度形成行業合力,使利用涉外版權代理制成為重要的國家文化戰略實施策略選擇。
1.確立國家理念認同與自我認知
采納多元化策略提升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已經成為文化強國建設的重要國家行為,因此,國家層面必須確立利用涉外版權代理制實現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的理念認同和自覺意識,將其與直接文化輸出同等視為國家文化戰略實現的慣習化策略選擇。國家層面應當主動介入對涉外版權代理制和版權貿易的管理控制,有效利用其創新國家文化價值觀念國際傳播擴展通道,讓版權文化貿易策略真正服務于國家文化戰略。另外,國家需要對自我職能定位進行明確認知,善于通過經濟方式對國家文化價值體系進行結構性控制,熟練運用版權貿易原則和市場價值規律機制來調控文化產品的社會生產、交換、分配等經濟活動,使國家文化形態的社會價值觀念內化于經濟文化產品市場商業運行體系之中。
2.實現涉外版權代理機制高度市場化運作
利用涉外版權代理制提升國家國際文化影響力的實質是國家意志使用市場機制和渠道對文化資源進行定向配比和價值控制,因此,實現高度市場化運作是利用這一策略的制度性先決條件。涉外版權代理制的規范運營必須確立獨立運行的市場主體,現有機構要擺脫對出版和行政管理機構在體制上的依附性,以獨立主體身份參與版權貿易及代理業務的市場經濟活動,這樣才能在高度專業化分工基礎上發揮代理機構市場主體性功能;涉外版權代理制還應當在遵循行業國際市場化規范和慣例條件下開展業務,這樣才能取得參與國際文化競爭交流的合法市場主體資格,能夠以國際市場為資源配置協調平臺,使國內版權貿易產業及其產品輸出與國際版權文化產品需求接軌,從而將負載本國文化價值觀念的產品推送至國際文化市場,以使其文化影響力的擴展成為可能。
3.構建國際化版權文化產業體系
利用涉外版權代理制推動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必須要以強大的版權文化產業為支撐。首先,必須將文化產業發展納入國際市場機制,突破其發展空間場域界限,實現專業分工、組織構架、生產流通等要素的國際化資源配置,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文化產業主體,實現規模優勢和集群效應,從生產機制層面保證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的價值負載資源基礎。其次,要促進實現版權文化產品生產標準和評價體系國際化,生產主體要依據國際市場文化消費需求實際,在產品生產研發層面接軌并執行國際標準,采取國際通行的制作流程和表現形式將國家文化價值觀念有效內化到商業文化產品生產之中,在產品屬性層面保證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的外在形式與價值內涵的結構性融合。
4.建立涉外版權代理行業準入制度
由涉外版權代理制支撐的文化貿易策略有著明顯的國家意志和國家文化戰略實現職能,因此必須建立涉外代理準入制度以確保其實施的可行性。政府職能部門應當通過批準和注冊,對版權代理產業準入機制進行管理,通過審核,選擇具備突出運營能力、市場資源廣泛、能夠憑借自身專業優勢進行國際版權貿易的代理機構作為實施版權文化貿易策略的主要承擔者,確保文化產品國際輸出的規模效益、范圍效益和經濟效率,使得負載國家文化價值理念的版權文化產品通過專業化貿易平臺進入國際文化消費市場,實現擴大文化價值觀念國際影響力的戰略目標。
5.建立涉外版權代理市場信任機制
涉外版權代理制是建立在版權委托人對受托人履約承諾及能力信任的基礎之上的,因而市場信任機制是國際版權代理及版權貿易可能發生實施的重要聲譽性和契約性基礎。建立良好的市場信任機制,可以取得國際版權市場、輸入國和出版機構對中國代理機構和版權文化產品的信任,降低版權文化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的交易成本,提高版權產品國際市場認同力與接納度,從而確保利用涉外版權代理制提升國家文化影響力實施成功概率。
6.發展內生性版權代理集體管理組織
自發的內生性版權代理集體管理組織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實施國家文化戰略的重要行業協調力量,這些行業聯合體由于規模巨大、權威性強,可以在國家意志導向下通過制定行業職業價值規范等方式從涉外版權代理行業內部形成國家利益價值觀念認同合力,消解行業純粹商業化傾向,以配合和支持國家文化戰略的實施。如美國的ASCAP、BMI和英國的CLA都曾在國家文化戰略中起到了重要的行業協調作用,因此我國可借鑒國外經驗,積極發展內生性版權代理集體管理組織,以便于從行業整體價值觀層面保證對利用版權代理制進行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策略實施的承載性。
[1]國家版權局、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著作權涉外代理機構管理暫行辦法,1998.
[2][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M],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34-38
[3]鄧珊妮.美國政府信息增值利用:經驗、模式及啟示[J].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1(3)
[4]楊明輝.美國文化產業與對外文化戰略[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6(5)
[5]陳長生.全球化與美國權利的世界化—對美國文化輸出的質疑[J].文藝理論與批評,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