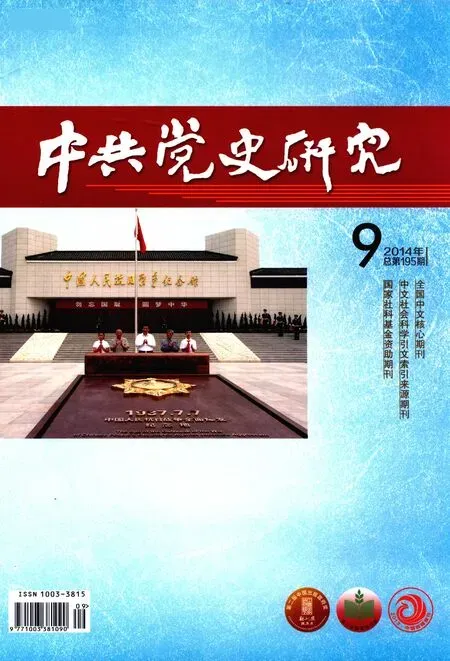計劃時期國企“父愛主義”的再認識——以單位子女就業政策為中心
2014-02-05 06:14:08田毅鵬李珮瑤
中共黨史研究 2014年9期
關鍵詞:制度
田毅鵬 李珮瑤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學界興起的對計劃主義的反思和批判中,父愛主義長期被視為計劃時期體制僵化和關系主義的最主要表現而備受詬病,但研究者很少對父愛主義的產生、發展以及走向制度化的具體歷史過程展開研究,對其運行所面臨的諸多復雜制約因素亦關注不夠。而通過對單位子女就業政策階段性演進的歷史考察,可以發現五六十年代的子女接班頂替主要是出于對因工死亡、致殘或年老體衰職工的社會保障而頒布的一種補償性和照顧性的福利政策,此后又陸續擴大到一些艱苦行業和特殊工種,但涉及面仍較窄,在實行條件和執行標準等方面有明確限定,社會影響不大,并始終未提升到制度層面,是一種有條件、有原則的父愛主義。70年代末,為解決“文革”時期積累的就業重壓,國營和集體企業職工的子女頂替政策被逐步大幅度放寬,廠辦大集體制度得到全面擴張,為解決企業子女就業問題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父愛主義的制度設計反映了社會主義國家以工人階級為階級基礎和領導階級的意識形態特征,它以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具有較強封閉性和自給性的單位共同體為制度性前提,也體現了“家國同構”的中國傳統文化因素。但具有自身利益訴求的企業在落實這一政策之際,往往采用“化大公為小公”的各種變通手段,導致子女頂替和內招制度弊端叢生,證明國企父愛主義的不可持續性。(吳志軍摘自《江海學刊》2014年第3期,全文約17000字)
猜你喜歡
遼金歷史與考古(2019年0期)2020-01-06 07:44:44
學術論壇(2018年4期)2018-11-12 11:48:50
法大研究生(2018年2期)2018-09-23 02:20:40
世界憲法評論(2017年0期)2017-12-06 09:10:10
中國衛生(2016年7期)2016-11-13 01:06:26
中國衛生(2016年11期)2016-11-12 13:29:18
中國衛生(2016年9期)2016-11-12 13:27:58
中財法律評論(2016年0期)2016-06-01 12:17:10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5年2期)2015-07-31 18:10:50
時代法學(2015年6期)2015-02-06 01:3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