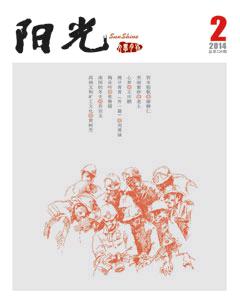老家很近又很遠
北喬
荊永鳴是一位生活型的作家,寫作是他參與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作品已經不是所謂的接地氣之作,而是從他生活體驗中自然生長出來的。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這個現實生活中的“外鄉人”,專注于遠離故鄉的漂泊者,書寫這些走入都市的打工者的生存境遇和精神歷程,比如《外地人》《北京候鳥》《大聲呼吸》等。而今,他又將故鄉從回憶中拽到現實,以長篇小說《老家有多遠》(作家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去直面故鄉當下的人情世事,狀寫夢中鄉村破碎后的現實老家。他沒有像一些游子那樣沉醉于夢中故鄉的美好,也沒有高高在上地斥責如今支離破碎的家園,而是以老家人身分回到老家,回到他曾經相當熟悉的鄉親們身邊,寫下他目光的顫抖和內心的糾結。《老家有多遠》,可以讓我們接觸真實的鄉土世界,近距離地端詳鄉村的現時生活。
與有些作家不同,荊永鳴沒有成為鄉村代言人的企圖,也沒有將自己包裝為“鄉村敘事者”,而是忠實于自己的內心和視角,以生活中的角色來注視當下的鄉村。可以說,作品中的“我”與荊永鳴在心理、情懷和精神內質上是同一個人。“我”幾乎是所有進城打工或生活的鄉村人的情感心理和文化立場的縮影。“我”生活在城里,但其實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城里人;“我”來自鄉村,是那種有“老家”的人,但我已經被鄉村人稱為“城里人”。離開鄉村的懷抱,“我”心中有濃濃的揮之不去的鄉情親情,而當鄉下的親戚真來到城里找“我”,我備感親近的同時,又有些嫌麻煩。有時,在鄉親們面前,“我”會不由自主地沾染上“城里人”對鄉村人的偏見、冷淡甚至是厭惡。而當城里人流露出對鄉村人的嘲笑和厭棄時,“我”又十分的反感。“我”其實是生活在鄉村與城市的夾縫之中,是鄉村人與城里人的混合體,會因為情境的變化而搖擺情感。老家的遠近,不再是時空的遠近,而取決于心靈與情感的濃淡。
記憶與夢中的故鄉是美好而溫暖的,但當“我”再次與鄉村在現實中遭遇時,那被親切地稱為“老家”的地方已是面目全非。當“我”懷揣溫暖的記憶和濃濃的鄉情走進現時的老家,所目睹和感受到的一切,才是《老家有多遠》最重的主題。對于敘述,這是一個有趣的視角,“我”既可以憑借親戚和鄉情適當進入鄉村內部,參與他們的生活;又可以“城里人”的眼光審視如今的鄉村,在某種距離感的支配下,更加客觀地看待鄉村的變遷和發展。現在的老家不再有田園牧歌、水清清鳥鳴唱,水土污染嚴重,處處是垃圾;私搭亂蓋橫七豎八的房屋,像傷疤一樣的道路;如地獄一樣的小煤窯吞噬著鮮活的生活,更在撕咬人性;那曾經令人陶醉的美麗家園正在荒蕪,像人一樣在蒼老。曾經和美的鄉村人,現在也是利益至上,爾虞我詐,小小的村干部也成了大官僚。世外桃源已經不存在,處處是物欲橫流、污濁遍地的世俗相和名利場。鄉村是在淪落還是在蛻變?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的酸楚與快樂,讓我們心痛,又無所適從。鄉村有些蒼茫,而我們的目光更加迷茫。
荊永鳴以誠實的筆法,帶著傷感與無奈,打碎了我們的故鄉,毫無保留地敘寫老家的丑陋與不幸。是的,他為鄉村的現實而嘆息無助,但他又不自以為是地指責,只是在憂愁中如實呈現,在詫異中舒緩敘述。鄉村的美麗、純樸、清新,已經被現代文明中的污穢所感染和侵蝕。這可能是文明進程的必經之路,正處在鳳凰涅槃的階段,但鄉村的呻吟讓人心痛。老家有多遠,不再是腳步的丈量,不再是情感的追問,而是一聲聲哀傷的呼號,撕裂心肺痛徹靈魂。
在荊永鳴心中,老家很遙遠了,曾經的老家已經無影無蹤。現實讓荊永鳴心痛地唱起鄉村的挽歌,遙望那他再也無法回去的老家。而我們每一個有老家的人,也會在閱讀中自問,我的老家有多遠了?答案大多數都是帶著憂傷與凄苦。鄉村,孕育了我們的文明,是我們的精神家園。如今,具象的鄉村漸漸消失了本來的面目,我們精神上的老家也在漸行漸遠。《老家有多遠》詠嘆的是鄉村,更是在哀嘆那已經或正在逝去的靈動的自然與純美的人性,那個曾經滋養了我們生命與靈魂的家園。
北 喬:文學評論家,作家,本名朱鋼,1968年4月生于江蘇,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紅巖》《芙蓉》《解放軍文藝》和《當代作家評論》等發表小說、散文和文學評論400余萬字。出版長篇小說《當兵》、系列散文《天下兵們》和文學評論專著《劉慶邦的女兒國》《貼著地面的飛翔》等9部。散文曾獲第十屆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大獎、文學評論曾獲第六屆全國煤礦文學烏金獎、中篇小說曾獲“99讀書人杯”世界之旅網文大賽金獎。系中國作家協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等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