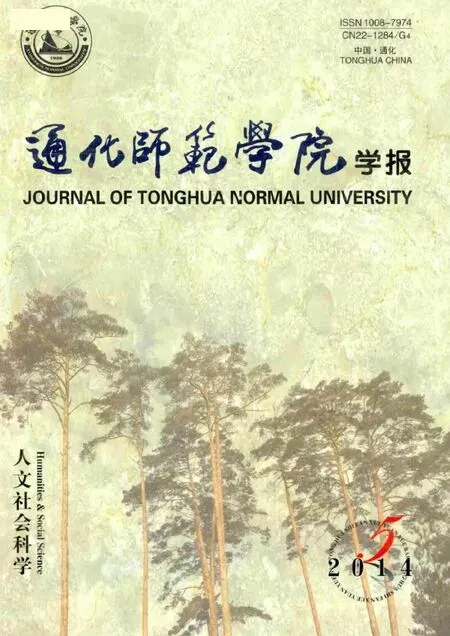好太王碑發(fā)現(xiàn)時間及相關(guān)問題研究
耿 黎
(通化師范學院 外語學院,吉林 通化 134002)
好太王碑文記載:“以甲寅年九月廿九日乙酉遷就山陵,於是立碑,銘記勛績。”學者們因此考證出好太王碑建于東晉安帝義熙十年——公元414年,至今正好1600年。經(jīng)歷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風風雨雨,保存完好,為我們留下了研究高句麗歷史與文化的珍貴文獻資料。經(jīng)過一百多年的研究,對于碑文的考釋及相關(guān)歷史的研究都取得不少成果。但是對于好太王碑重新發(fā)現(xiàn)的時間卻存在分歧。在紀念好太王碑建立1600年之際,有必要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并向各位前輩學習。
一、好太王碑發(fā)現(xiàn)于光緒三年——1877年
多年來,學者們對于好太王碑的發(fā)現(xiàn)形成了如下幾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同治末年說。以劉承干為代表。1922年他編成《海東金石苑補遺》,收入好太王碑釋文,后附了一段跋語:“此碑同治末年始傳入京師,吳縣潘文勤公祖蔭先得之。海東工人不善拓墨,但就石勾勒,才可辨字而已。光緒己丑(1889年)宗室伯羲祭酒盛昱始集資,令廠肆碑估李云從裹糧往拓,于是流傳稍廣。”
第二種意見,光緒元年說。以顧燮光為代表。1918年他發(fā)表了《夢碧簃石言》,文中記載:“戴君葵甫為余言:好太王碑在奉天省輯安縣東門外十里將軍墓南里許。光緒元年開墾東邊荒地始發(fā)見。”
第三種意見,光緒初年說。以談國桓、張延厚為代表。談國桓在《手札》中記載:“近得高句麗好太王碑,尚不惡,當在光緒初葉時所拓。1925年,張延厚在《跋語》中記載:“此碑在奉天省輯安縣鴨綠江濱,歷代金石家未有著錄。勝清光緒初,吳縣潘鄭安尚書始訪得之。”1930年印行的《輯安縣志》采用“光緒初年”說。
第四種意見,光緒六年說。以葉昌熾、歐陽輔為代表。1909年,葉昌熾《語石》一書印刷發(fā)行,收入《奉天一則》記載了好太王碑的發(fā)現(xiàn):“高句麗好太王碑,在奉天懷仁縣東三百九十里通溝口,高三丈余。其文四面環(huán)刻,略如平百濟碑。光緒六年,邊民斬山刊木始得之。”1923年,歐陽輔《集古求真》第三卷《高麗好太王碑》一文記載:“高麗好太王碑……石在奉天懷仁縣東四百里通溝口。光緒六年,邊民斬山刊木始得發(fā)現(xiàn),中土乃有拓本。”
經(jīng)過多年討論,學界否定了同治末年說,集中在光緒初年說上面。具體說來還有光緒元年、二年、三年、六年幾種說法。研讀諸家的記載和有關(guān)資料,我覺得光緒三年發(fā)現(xiàn)的證據(jù)是較為充分的。
第一條證據(jù)是王志修的 《高句麗永樂太王古碑歌》。王志修,字竹吾,號少廬,又號脩廬,山東諸城人,曾任奉天軍糧署同知,后調(diào)任金州廳海防同知、岫巖州知州等職。曾著有《奉天全省輿地圖說圖表》《脩廬詩草》等。[1]48好太王碑發(fā)現(xiàn)不久,王志修就曾到過現(xiàn)場進行考察。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他被委托考試奉天府所屬各衙署的青年吏員,就以好太王碑做歷史題目進行考試,自己先寫出范文《高句麗永樂太王古碑歌》,其中詩句有“我皇馭宇之三載,衽席黎首開邊疆。奇文自有鬼神護,逢時不敢名山藏。”已經(jīng)指明好太王碑是光緒三年(1877年)時發(fā)現(xiàn)。
第二條證據(jù)也是王志修的。他在考試諸生的同年,又寫出《高句麗永樂太王碑考》,與《高句麗永樂太王古碑歌》合成《高句麗永樂太王古碑歌考》一書,由奉天軍糧署石印刊行。在《高句麗永樂太王碑考》中記載:“碑在奉天東境,興京同知屬懷仁縣東三百六十里通溝口。光緒三年開邊禁,以通溝設(shè)巡檢。地有古城基尚存。碑立古城東北鴨綠江岸,東向,高二丈余,寬八尺強,厚得半。無赑屃盤螭飾。”這里“光緒三年開邊禁,以通溝設(shè)巡檢”正是好太王碑發(fā)現(xiàn)時間的又一次表述。連同“我皇馭宇之三載,衽席黎首開邊疆。奇文自有鬼神護,逢時不敢名山藏。”明確指出,好太王碑是在光緒三年發(fā)現(xiàn)的。這是國內(nèi)最早關(guān)于好太王碑發(fā)現(xiàn)時間的記錄,公布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距離好太王碑發(fā)現(xiàn)只有十八年。比起后來那些道聽途說、模棱兩可的記載還是真實可信的。
第三條證據(jù)是懷仁建縣的時間。談國桓在《手札》中記載:“近得高句麗好太王碑,尚不惡,當在光緒初葉時所拓。此碑最初歷史,弟有所知,致貢左右,籍備參考。奉天懷仁縣設(shè)治之時,首膺其選者為章君樾,字幼樵。幕中關(guān)君月山,癖于金石,公余訪諸野,獲此碑于荒煙蔓草中,喜欲狂,手拓數(shù)字,分贈同好,弟髫年猶及見之。字頗精整。”《手札》收錄于1925年金毓黻編的《遼東文獻征略》,其中批評了1909年《神州國光集》影印的碑文,因此不會早于1909年。后來很有代表性的學者佐伯有清、王建群、劉永智等[2],都認為懷仁縣書啟關(guān)月山是好太王碑的發(fā)現(xiàn)者。那么,懷仁設(shè)縣的時間就是關(guān)月山到任的時間,也就是好太王碑發(fā)現(xiàn)時間的上限。據(jù)《奉天通志》載光緒三年奏稿:七月,增設(shè)奉天東邊道及寬甸、懷仁、通化等縣。“留奉補用知縣章樾,材具明敏,辦事安詳,堪以試署懷仁縣知縣。”《桓仁縣志》亦載章樾于光緒三年任知縣。《奉天通志·職官》記載更詳盡:懷仁縣知縣,光緒三年七月設(shè)。“章樾,河南祥符人,監(jiān)生,三年任設(shè)治委員,四年五月試署,五年二月補,八年正月調(diào)署懷德。”因此,光緒三年七月以后,關(guān)月山發(fā)現(xiàn)好太王碑是順理成章的。對于一位“癖于金石”的人,年內(nèi)會有“公余訪諸野”的機會,“獲此碑于荒煙蔓草中”。正如王志修的記載,光緒三年,關(guān)月山發(fā)現(xiàn)了好太王碑。
當然,也許有人會說,關(guān)月山是光緒八年離開懷仁的,光緒八年前每年都可能是發(fā)現(xiàn)好太王碑的時間。要知道,好太王碑發(fā)現(xiàn)后,碑身長滿青苔,要拓出完整拓本,必須除去青苔。那么,火焚除苔的時間就成了好太王碑發(fā)現(xiàn)時間的下限。
二、火焚除苔的事實及時間
好太王碑發(fā)現(xiàn)以后,碑身長滿青苔,為了捶拓完整碑文,經(jīng)歷過火焚除苔。記載火焚除苔的資料很多,按發(fā)表時間順序整理如下:
1.1909年,葉昌熾的《語石》刊行,其中《奉天一則》記載:“光緒六年,邊民斬山刊木始得之。……苔蘚封蝕,其坳垤之處,拓者又以意描畫,往往失真。……聞石質(zhì)粗駁,又經(jīng)野燒,今已漸剝損矣。”
2.1909年,楊守敬的《寰宇貞石圖》再版,收入《高麗好太王碑》,記載:“碑出遼東鳳凰城。十余年前傳來拓本,或云是庚子中日之役覓得。……曹君云:碑初出時,人爭拓之,土人以其踐踏禾苗,以牛糞涂其上,用火燒之,故剝蝕乃爾。”
3.1914年,關(guān)野貞在《滿洲輯安和平壤附近的高句麗遺跡》一文中記載:“(初天富)三十年前就住在此地,受當時知縣之命,捶制拓本。因碑面有長華(苔蘚),曾以火燒碑,致使隅角損缺。”[3]
4.1915年,今西龍《關(guān)于廣開土境好太王碑》一文中記載:“此碑三十年前,碑面長滿長華(苔蘚),文字遺存與否,無法弄清。他(指初天富)奉知縣之命,燒去長華,露出文字。當燒碑之時,使碑一部分毀損。 ”[4]
5.1918年,顧燮光的《夢碧簃石言》記載:“光緒元年開墾東邊荒地始發(fā)見。碑面為蒼苔漫沒,剔除極難。土人以糞涂碑面,俟干,縱火焚之。蒼苔去而碑裂矣。”
6.1925年,談國桓的《手札》記載:“聞此碑數(shù)年前有傖父某,以苔蘚過厚,不易拓,用馬矢燒之。而碑石本粗劣,經(jīng)此煅煉,恒片片墜。碑乃自此毀矣!物成敗有數(shù),惜哉!”
7.1925年,張延厚的《跋語》記載:“此碑在奉天省輯安縣鴨綠江濱,歷代金石家未有著錄。盛清光緒初,吳縣潘鄭安尚書始訪得之。……又聞寅卯間,碑下截毀于火,為惋惜久之。”
8.1930年出版的《輯安縣志》記載:“惜多歷年所,風雨侵蝕,已漸剝損,清晰處尚堪入目。光緒初年,拓者因石上多苔蘚,用牛糞敷其上,燒之,以致剝削太多。”
9.1983年,王健群在《好太王碑的發(fā)現(xiàn)和捶拓》一文中,引用了當?shù)乩先说恼{(diào)查記錄,楊維才介紹:“初大碑(指初天富之子初均德)還說:過去碑上青苔挺老厚。后來在青苔上抹上牛糞,牛糞干了放火燒,把青苔燒掉才拓出字來。燒的時候,大碑爆了一塊。”辛文厚講道:“聽說碑上原來長滿青苔,后來說沈陽來人要看字。老初頭想出了個法子,在碑上涂上牛糞,牛糞干了倒上火油燒。青苔去掉了,碑也崩了一塊。”李清太也講過:“聽老人說,以前由于碑身長滿青苔,不好拓字,在碑上抹上馬糞(當時左近無牛),干了用火燒,把碑燒裂了。”[5]
從上面中外學者和當?shù)乩先说慕榻B可知,好太王碑發(fā)現(xiàn)以后火焚除苔的事確實存在。這一點從碑石仍然清晰的幾處裂痕也可以得到證實。一般說來,像好太王碑這樣的角礫凝灰?guī)r,自然界的風雨只會使表面有少許磨蝕,而不會出現(xiàn)如第一面和第二面轉(zhuǎn)角距底部2.85米處那樣大的裂痕。綜合考察之后,得出的結(jié)論只能是經(jīng)過火焚造成的。還有其它幾處裂痕和較大的剝落,也都是當年火焚留下的。[6]16至于火焚的時間,只有張延厚在《跋語》中提到:“又聞寅卯間,碑下截毀于火,為惋惜久之。”光緒年間有寅卯三對:
光緒四年 戊寅 1878年 光緒五年 己卯1879年
光緒十六年 庚寅 1890年 光緒十七年 辛卯 1891年
光緒廿八年 壬寅 1902年 光緒廿九年癸卯 1903年
榮禧在《高句麗永樂太王墓碑讕言》中寫道:“余于光緒八年壬午(1882年),曾倩山東布衣亓丹山往拓,得獲完璧。”光緒八年得到了好太王碑完整拓本,火焚除苔應(yīng)該在此之前。以上的寅卯年只能是光緒四五年了。這么多證據(jù)絕不會是巧合。說明關(guān)月山發(fā)現(xiàn)好太王碑一定是在火焚除苔的光緒四五年前。那么光緒三年秋發(fā)現(xiàn)好太王碑,轉(zhuǎn)年經(jīng)知縣同意火焚除苔就完全合乎情理了。
三、光緒六年是完整拓本出現(xiàn)的時間
時至今日,光緒三年發(fā)現(xiàn)好太王碑,不僅有最早的現(xiàn)場調(diào)查者記錄可證,還有懷仁建縣的時間可證,更有火焚除苔的時間限定,應(yīng)該是符合事實的、可信的結(jié)論。可是仍然有少數(shù)日本學者堅持“光緒六年發(fā)現(xiàn)”的說法。他們依據(jù)的是葉昌熾《語石》中收錄的《奉天一則》,全文如下:
高句麗好太王碑,在奉天懷仁縣東三百九十里通溝口,高三丈余。其碑文四面環(huán)刻,略如平百濟碑。光緒六年,邊民斬山刊木始得之。窮邊無紙墨,土人以徑尺皮紙,搗煤汁拓之。苔蘚封蝕,其坳垤之處,拓者又以意描畫,往往失真。乙酉年(光緒十一年,1885年),中江李眉生丈得兩本,以其一贈潘文勤師,共三四十紙,屬余為排比考釋,竭旬日之力未能連綴。其后,碑估李云從裹糧挾紙墨,跋涉數(shù)千里,再往返,始得精拓本。聞石質(zhì)粗駁,又經(jīng)野燒,今已漸剝損矣。碑字大如碗,方嚴質(zhì)厚,在隸楷之間,考其時,當晉義熙十年所記。高麗開國武功甚備。此真海東第一瑰寶也。
葉昌熾(1849~1917)字蘭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號緣督廬主人。原籍是浙江紹興,后來入籍江蘇常州。葉昌熾是清末著名藏書家和金石學家,是第一位確認出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寶藏價值的人。葉昌熾學識淵博,著有《語石》《緣督廬日記》《藏書紀事詩》《滂喜齋藏書記》等。《語石》成書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宣統(tǒng)元年(1909年)始由蘇州振新書社印刷發(fā)行,后收入《國學基本叢書》和《萬有文庫》。《奉天一則》收在《語石》中。全文不長,記錄好太王碑所在位置,拓本的出現(xiàn)、拓本狀況、文字狀況等。其中“光緒六年,邊民斬山刊木始得之”講的并不是好太王碑發(fā)現(xiàn)的時間,而是拓本出現(xiàn)的時間。很明顯,如果說好太王碑發(fā)現(xiàn),一定會有發(fā)現(xiàn)人,這個發(fā)現(xiàn)人需要認定碑的性質(zhì)時代,如關(guān)月山那樣明確為高句麗的好太王碑。而一般邊民做不到這一點,或許邊民只是看見,而不能稱作發(fā)現(xiàn),只要寫“邊民得見”或“邊民見之”就可以了。如果需要“斬山刊木”才能“得之”,得到的也只能是拓本。關(guān)月山發(fā)現(xiàn)好太王碑時,附近已有人家,根本不需要“斬山刊木”就能見到,經(jīng)過考察,知道是高句麗時期的好太王碑。好太王碑高6.39米,不搭架子根本得不到完整拓本。因此,王志修詩句 “伐林架木拓碑出,得者寶之同琳瑯”,說的也是拓本的出現(xiàn)。“光緒六年,邊民斬山刊木始得之。”后面接著的文字說的也是拓本:“窮邊無紙墨,土人以徑尺皮紙,搗煤汁拓之。苔蘚封蝕,其坳垤之處,拓者又以意描畫,往往失真。”前兩年,學院得到的好太王碑拓本正是用“徑尺皮紙”拓出的。日本學者對中國文獻的閱讀和理解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因此才將拓本的得到誤認為碑石的發(fā)現(xiàn)。正像集安冉牟墓志,墓主人是冉牟,以冉牟墓名之才準確。日本學者卻用寫墓志的人牟頭婁作為墓名,其實墓里埋的不是牟頭婁,而是冉牟。很有意思的是,他們卻堅持類似錯誤,至今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