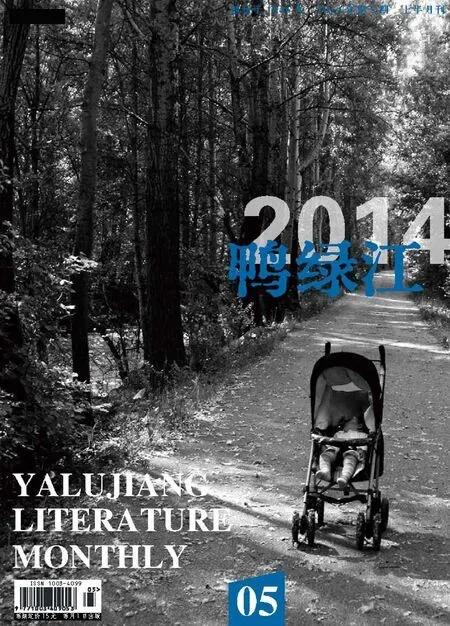《耶路撒冷》節選
《耶路撒冷》節選
到五月,樓里出來散步的人就多了。天開始熱,燥了一天的風涼下來,吹到身上很舒服;小區對面的萬泉河公園很寬敞,有花有草,有噴泉和假山,還有很多長條椅可供休息,坐下來,躺著,風一吹人就睡著了;到九點多鐘醒過來,哆嗦兩下往家走,排著隊堵在電梯門口要進來。八點半到十點之間,電梯得上上下下不停地跑,福小忙著按按鈕、和人說話,十八層樓的居民都認識。今晚安靜,過了八點電梯就不動了,因為剛下了一陣雨,溫度立馬降下來,都待在家里不露頭了。北京就這樣,天氣稍有點兒風吹草動人就亂。眼看著滿大街出租跑空車,只要落了五分鐘的雨,想打到一輛車比你現造一輛都難,到處都是驚慌逃竄的人,所有車都在摁喇叭。社會心理學的專家們認為,這是因為大城市里的生活缺少安全感。福小不知道這論斷是否科學,以她的經驗,小地方對雨雪等天氣突變倒是有過剩的平常心,大雨瓢潑也照樣光著腦袋在外面走。照專家的推論,那些偏遠的小鄉鎮就該有充沛的安全感;在貧困落后的生活中心安理得,這個論斷要推過去好像不太容易。

福小在工作服里面加了一件長袖T恤,坐下來不動的時候才覺得正好。天氣預報又放了空炮。她剛從收音機里聽到,今天下午平谷區的山里還下了一毫米半的雪;五月飛雪,反常的自然現象是在進一步強調我們的生活缺少安全感么?安全感的確相當奢侈,傍晚時候,一個中年男人跟著房產公司的中介到十三樓看房子,上下電梯都在抱怨,房價高成這樣,還想不想讓人活。讓房主今晚就定奪,別明天早上一覺醒來,價錢又上去了。中介說,放心,這絕對是跳樓價。顧客回答,是你跳還是我跳?中介說,價錢跳。顧客哼了一聲,你說的是價錢從十二樓往十三樓跳吧?他們離開后,電梯繼續上行,纜繩碰巧在十二樓往十三樓上升的時候嘎吱嘎吱響了幾下,福小想,房價上漲的聲音可能就這樣。
最后一個乘客是十五樓,下了以后電梯就停在那里。福小不喜歡懸在半空的那種上不能頂天、下不能立地的感覺,于是將電梯運行到一樓,在一樓她更有安全感。沒人的時候她也不喜歡將電梯門敞開,那樣她也覺得沒有安全感。她的安全感在于,在一樓但關上門,別人看不見她,而一旦天送出了事,她打開門就可以往家跑。這個時候天送只能一個人在家,四歲零兩個月的孩子,一個人爬上床,拉上被子,滅掉燈,閉上眼睡覺。福小上小夜班,傍晚六點到午夜十二點,這其間只能偶爾回去一趟,看一眼天送就往回跑。五分鐘前,她正做數獨,天送打來電話,說:
“媽媽,我想跟你說完最后一句話就睡。”
“不是已經跟媽媽說過了嗎?”
“那是倒數第二句,現在才是倒數第一句。”
“那你說吧。”
“媽媽,我想跟你說,你要在電梯里害怕了,就給我打電話。”
福小當時眼淚就往下掉,掛了電話在電梯里想天送。這孩子養得值——值不值都得養。第一次在初平陽拍到的照片中看見小家伙時,她覺得他眼神里有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初平陽剛考上博士,跟著導師和同學做一個社會福利方面的課題,把北京周圍的養老院和孤兒院轉著圈子考察了一遍,最遠的已經考察到了河北地界,收集了不少文字和音像資料。楊杰婚后一直沒孩子,一直在猶豫是否要收養一個,初平陽就把他在孤兒院帶回來的信息發給他看,照片里有天送。那時候天送叫藍石頭,負責他們幾個男孩的阿姨姓藍,藍阿姨喜歡他,希望這孩子能像石頭一樣健康、堅強、有棱有角。在一次楊杰召集的一次聚會中,初平陽把這些照片帶到知春路上的無名居,在這家淮揚菜館里,楊杰夫婦希望初平陽、易長安和秦福小能給他們出出主意:領養還是不領養;若領養,領養什么樣的孩子。在眾多孩子照片中,福小看見了藍石頭。一歲多的藍石頭小細胳膊小細腿,頂著顆大腦袋,躲在一群孩子的后面,大眼睛里那種與生俱來的憂郁讓福小的腸胃驟然扭結了一下;這疼痛只有在她想到死去的弟弟天賜的時候才會有,二十年來,只要天賜的名字和嘴角上翹的笑臉出現在她頭腦里,腸胃就要扭結。但這事很快就過去了,照片里的藍石頭占的空間很小,眼睛更小,是否有福小認為的憂郁都很難說;即使有,也不稀奇,這世上有多少人,每個人瞇縫小眼以后表情都會顯得很深沉。
一周后,他們驅車河北的那家孤兒院。在鄉下,離最近的村子半里路,一個大院子里有前后三排紅瓦房,院子后面是條水流向西的河。這地方原來是養老院,一個做家具生意發了財的老板建的,最多時有過二十三個老人;經營了三年,老板生意砸了,養老院也掙不了幾個錢,老板決定把院子賣掉,老人們從哪里來回哪里去,轉手之后成了孤兒院,政府出錢來維持。福小在院子里的小操場上看見了藍石頭,怯怯地靠著滑梯,半張臉躲在陰影里。他們給孩子們帶去糖果和巧克力,分發的時候楊杰老婆問福小,你覺得哪一個孩子最好?福小說,都好。的確都好。她看他們高興覺得好,她看他們羞怯、難過也覺得好;那些有殘疾和缺陷的孩子,她也覺得好,是讓她心疼的好。這么小的小東西,她抱著他們,捏著他們肉肉的小屁股蛋,覺得這些都是剛長出來的果子,新鮮得讓人不知道怎么才好。
楊杰兩口子在離開時孤兒院時沒表態,他們還在躊躇。領養孩子是一輩子的事,必須慎之又慎。易長安從開始就不贊成領養,他連自己生孩子都嫌麻煩,要什么孩子嘛,能把自己喂飽整快活了已經不容易了。他喋喋不休一路,讓楊杰和崔曉萱心里浮上來的幾個目標又慢慢沉下去。回到北京,晚上沒事的時候福小翻看數碼相機里的照片,但凡有藍石頭的鏡頭,她都在自己身體里聽見咯噔一聲,仿佛一扇沉重的鐵門被打開。他們倆在發黑的紅磚圍墻下有張合影,福小蹲著,攬著藍石頭的小身體,藍石頭很不情愿地將右手搭在她肩膀上。福小覺得肩膀上的那個位置現在還熱著。圍墻固執、強硬,傲慢地充滿整個鏡頭,在想象的空間里可以無限延伸,直到成為藍石頭的世界的隱喻。她盯著照片里的藍石頭看,在他的臉上看見了天賜。天賜被一道墻隔在另外一個世界。凌晨兩點半,她在近百次輾轉反側之后,起床給初平陽打電話,如果她要領養一個孩子可不可以。
“你瘋了?”初平陽從中英文對照的《圣經》上抬起頭,兩眼酸澀,“這事首先得問你男朋友。”
“你只要跟我說,沒結婚的女孩子可不可以領養。”
“當然可以。”
“沒年齡限制?”
“無配偶的男性收養女性時,年齡限制才比較嚴格: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的年齡要相差四十周歲以上。”
“那好,我要領養藍石頭。明天你陪我去。”
初平陽抽了一口涼氣,福小還是原來那個福小,就算把天下走遍了,她也不會改。她從十七歲離家出走,在中國的版圖上從東走到西,從南走到北,在北京停下來,她還是秦福小。
第二天陰雨,一大早找楊杰,楊杰關機,易長安開著他的尼桑越野帶他們倆去了孤兒院。手續繁復,要體檢,要出示很多證明,填很多表格,簽很多字,條條款款都得過一遍,關鍵是這個流程中的負責官員不是你不在就是他缺席,全等齊了,手續辦好,晚飯都吃過很長時間了。北京的雨一直下到河北,又從河北下回來。車在泥濘的野地里暢行無阻,易長安跟初平陽說,你還說我買越野車得瑟,這要楊杰的寶馬來跑,早趴泥坑里歇著了。藍石頭瞪大眼看著雨線抽打車窗,在福小懷里恐懼得一動不動,他把哭聲憋在肚子里,帶著恐懼睡著了。等他再睜開眼,躺在福小的床上,看見的是北京明亮的陽光,他哇的一聲哭起來,要藍阿姨。福小把他抱起來,說:
“乖,從昨天晚上開始,我就是你媽媽了。”
楊杰和崔曉萱一周半之后決定領養那個大腦袋的男孩。初平陽告訴他們,藍石頭已經成了福小的兒子,改叫景天送。崔曉萱當即在電話那頭叫起來,這叫什么事,參謀成了挖墻腳的!楊杰你他媽的都找了些什么人!
“不發瘋會死么?”楊杰說崔曉萱,然后問初平陽:“平陽,她怎么會領養孩子?”
“她說,”初平陽心事重重地說,“藍石頭像天賜。”
楊杰在那頭沒吭聲,半天才說:“沒看出多像啊。”
“她說像。”
“像個鬼!她就是不想讓我們好!”崔曉萱的討伐里帶了哭腔。我們都能理解,為了要孩子她把北京所有醫院和專家都看遍了,也做過無數次艱難的嘗試,最后一個老教授跟她說,孩子,認了吧。她花了一年時間才接受這結果,又花了一年時間接受領養一個孩子的建議,因為楊杰希望有個孩子,現在她失眠十個夜晚之后終于決定領養一個男孩,被秦福小撬了墻腳。多少年里她其實就挺煩這個女人,只要一提起秦福小和景天賜,楊杰那沉痛和游移的眼神就讓她不舒服。除了有點嫻靜和堅定的姿色,她就沒看出這個十幾年來漂泊全國各地、干過無數匪夷所思的工作的女人究竟有什么好,讓楊杰、易長安和初平陽言談舉止中都小心翼翼地護衛著。“像什么像!她就誠心跟我們找別扭!”
“真讓他姓景?”楊杰把電話免提關掉,崔曉萱消失了。
“福小親口說的。景天送。”初平陽說。
“這名字好。”楊杰點上煙,“像么?”
那個時候的確沒那么像。但是現在,三年過去了,所有見過天賜的人都不得不承認,天送簡直就是天賜的翻版。初平陽他們見了,后背直冒冷汗,像到了骨頭里。接著他們慚愧,在藍石頭的臉上和眼神里看見景天賜的,只有福小,而不是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
福小坐在電梯里。數獨是做不下去了,晚報上今天的數獨題很難,就算心平氣和她也未必做得出來。看上去就那么幾十個不起眼的小格子,要把數字不重樣地擺對位置,讓任何兩個方向的數字總和都相同,難得要死。福小是數獨高手,起碼在物業公司的所有電梯工里沒人玩得過她。電梯工都愛玩這個,一道題能把一個晚上都打發掉,還不覺得煩。資源也豐富,報紙訂戶喜歡讓郵遞員直接將報紙送到電梯里,下班時懶得開信箱,順手就從電梯工的小桌上取走了;很多報紙后頭都有數獨題,隨便做,反正人頭都熟。
很多同事和朋友向福小請教數獨的心得,福小說,沒心得,就是直覺,然后就是讓自己的思維跳起來:三級跳你們都知道,一跳,再跳,又跳,在頭腦和眼睛里給數字留下開闊的變換空間,別讓它們擠在一塊兒打架。同事和朋友照此方法試驗,回頭苦著一張臉對她,數字跳不起來,腦子里的空間不夠。福小說,那就沒辦法了。
她沒說實話。在她頭腦里三級跳的不是數字,而是地名和工作;虛擬的空間的確足夠大,但那空間不是為數字準備的,而是中國的版圖,她因為流浪和謀生曾不得不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跳來跳去。從南京到杭州到九江到長沙到云南到潮州到深圳到鄭州到西安到石家莊到銀川到成都到北京。她在數獨的小格子里看見了一個個城市,她正在從一個城市奔赴另一個城市的路上。助跑、起跳、騰空、落地;助跑、起跳、騰空、落地。每一個動作都很艱難,每一次都仿佛連根拔起,每一次也都成功地助跑、起跳、騰空、落地;吃了多少苦,忘了,時光流逝就到了今天。她做的是地理學式的數獨,這其中包含了一條比數理更堅強和有效的邏輯。說實話也沒用,他們沒法理解。
709室的訂戶出長差,他的《京華晚報》已經在福小的桌子底下積了一摞,這段時間福小就盯著晚報做。讓每一行的數字加起來都等于29,跟讓每一行數字加起來等于92一樣艱難。福小覺得自己在城市之間跑累了,助跑、起跳、騰空、落地的動作都開始變形,腿腳不聽使喚,很像噩夢里跳起來懸在半空動不了,遲遲落不下來。她揉揉眼,翻開報紙,看到初平陽的專欄,“我們這一代”,文章標題是:到世界去。
責任編輯 曉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