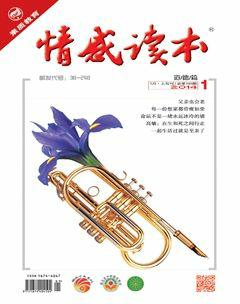讓愛成為一種習慣
漱玉
我看著女兒,
我知道,
愛,
已成為一種習慣。
當愛成為一種習慣,
再改掉,
也是不容易的了。
童年,愛的種子播進心田
小時候,父親在工作組忙活,母親在生產隊忙活,姐姐上學,基本上無人看管幼小的我。我從會走路開始,就天天一個人在胡同里“串門”,串到誰家,就玩到誰家,也就吃到誰家。母親從生產隊回來,往往天已大黑,她在胡同里喊一嗓子我的小名兒,就有人出了門來回一嗓子:“在俺家里咧!睡咧!”母親遂到這家里把我抱回。
就這樣,我吃百家飯,睡百家床,逐漸長大。
長到七八歲,開始替母親干一些活計,其中有一項,就是給大家送吃的。那時候,父親開始在制衣廠當領導,家里條件好一些了。每做了好吃的,例如餃子、包子、燉肉之類,有時候還有一些過年的干貨,母親都打發我送一大碗給鄰居。有時候是前面大奶奶家;有時候是后面老奶奶家;有時候是新村的大嬸子家;有時候居然是離家三四里的姑奶奶家。我撅著嘴不情愿地問:“為什么那么大老遠的還要送?”母親說:“你還好意思說來,你串門都串到好幾個莊子了!那一年,你自己跑到柴汶河橋上了,天黑回不了家,在那哭,虧了你姑奶奶把你帶回去,吃了飯又把你送回來。不然,你這小命早被橋下的老馬猴子給叼走了。”
每次聽到這個故事我都特興奮,又有點不好意思,感覺自己特了不起,居然一個人走到那么遠的柴汶河橋上去,那可能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遠足,同時又為自己的魯莽感到害羞,真是夠淘氣的。我更是特別感激那個救我回去的姑奶奶。于是,就懷著格外的感恩之情去送母親備好的吃食。
所有的人拿到這些吃食,都樂呵呵地咧著嘴笑,開開心心、大大方方地接受了,如果這家有好吃的還要讓我捎回些。我勝利完成了使命,有時候還會滿載而歸。那個年代,送吃的是一種時尚,剛剛過上飽腹的生活,也只有吃食是最好的禮物,才可以表達愛的心意。
就這樣,一份份包涵著愛的吃食在我家與大家的家門之間來回傳遞著。往往是傍晚,我手里提著熱氣騰騰的竹菜盒,包子、餃子等美食在里面安靜地等待著,身后跟著一條大黑狗,在魯中腹地那種悠長而寬闊的胡同里穿過。有時候,我會穿過種著大白菜、碧綠韭菜和菠菜的菜園,穿過廣闊蔥蘢的原野,穿過傍晚村莊里飄出來的輕柔的炊煙,穿過夕陽照耀著的美麗的柴汶河,才能到達目的地。這一路的心情,是多么雀躍,多么歡快。因為,去到的人家,都是曾那么愛過我哺育過我的人家,都是幫助過我們的人家,都是我們的親人和朋友。
我送去的是我們一家人一腔的感恩和愛意,我看到的是一張張熟悉的笑臉,聽到的是感激的話語,觸摸到的,是一雙雙溫暖的大手。
所以,有點好吃的,就要送給誰家一起嘗嘗,這成了我們家的一種傳統,一種習慣。
城市,冷漠讓人生如此寂寥
離開養育我的村莊來到了大都市——北京生活。我體會到了大都市的熱鬧非凡和流光溢彩,體會到了都市生活中衣食住行的方便,但在一年又一年時光長河的流逝里,也感覺到了一種如絲如縷而又深不可測的落寞。
在一個公司里共同工作了好幾年的同事,分開之后最深的痕跡就是留在MSN或者QQ上那一個個頭像和名稱,彼此在網上見著了也很少打個招呼,除非有什么事情需要對方幫忙,否則就一直這么互相沉默著,直到老死。
我曾經在一個很偶然的時候得知夢夢離婚了,目前一個人帶著孩子過。當年我們一起在一家網絡公司就職,同為部門經理,兩人朝夕相處了三年多,同一個辦公室只隔一個檔板,同一個碗里吃過飯,同一個床上就過寢,可說是無話不談。這樣的姐妹情意按說不可謂不深了。但是分手幾年后我們忙于工作、買房、結婚、生子,就像上緊了發條的鐘表,只按自己的軌跡轉動,根本無暇顧及他人的生活。我們一直很少聯系。
當我得知她離婚的消息,很擔憂,第一時間給她發去短信,我只是試探地問候了一下,因為幾年不聯系,我不太了解她現在的性格。她回了一條短信來:“玉,我買房了,四環120平米,全款,恭喜我吧!”我真心地為她高興,要知道,在北京,四環,買到120平米的房子,還是全款,那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回了一句熱烈祝賀的話。她又回:“我生的是兒子,5歲了,特可愛!”我趕緊發了一句發自肺腑的話:“太好了,你一直喜歡男孩!”她又回:“我買車了!上個月提的新車!”我又發了一個大大的開心的表情,并附帶上一句:“你還發生過一些不高興的事嗎?不開心就跟我說一說啊?”這條短信發過去之后,我的手機就沉默了一個下午,到了晚上,她回短信了:“我很好。沒事。”
這句話,把我們的距離再次拉遠。我知道,當年那個率真熱情的女孩子已患上了大城市里人們慣有的那種病;物質化冷漠病(我自定的一種病)。她已不愿向人打開她的心,她已被這城市的冷漠給浸染、滲透、融合。這些人衣著光鮮,穿著高檔,開著高級橋車,出入于高級寫字樓和環境上乘的住房小區,他們講究言談舉止的優雅,講究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質生活的超前,他們一到放假就花上幾萬十幾萬去國外旅游,但是你要問起同他們住了十來年的對門鄰居姓什么,他們一定呈現給你一臉的茫然。
城市越龐大,越繁華,物質化冷漠病患者就越多。冷漠的氣息穿梭在都市的每一個空間里,每一段時間里,流淌在每一個人的眼睛里,心靈里。當大部分人習慣了這種病征,大家就都不認為自己或別人是病人。
我的當年的朋友夢夢,從那次聯系之后就斷了聯系。我們都太忙了。
用心,讓愛成為一種習慣
十幾年前,當我第一次敲開對門鄰居的家,給他們送上我親手做的肉菜包子,他們那一臉的驚詫,讓我至今難以忘懷。
女兒從出生就看到這個現象:每每做了面食,我都會送一些去對門家。對門的張叔叔,患有胃病,醫生讓多吃面食,老伴是南方人,不太會做。我經常自己發面做包子,做發面餅,手藝自詡不錯,也十分愿意拿來炫耀。更為的是增進一點鄰里的聯系。我發現,每次送一點吃食出去,我都會感覺那如絲如縷而又深不可測的落寞減卻了不少,代之的是一種興奮,一種快樂,一種充實。我想,童年送吃食的那種習慣已經像種子一像種在我的血管里了。是種子,總是要發芽成長的。
女兒大點了,我讓她去給鄰居送吃的,她不去,說:“為什么要送他們呀?”我說:“好吃的要與別人分享呀,分享才會快樂!”女兒還是不去,我去了,開心地去,開心地回。她還太小,不太懂得分享是一種什么樣的快樂,也不會懂得為娘的一片來自童年的感恩之心。
后來,對門的叔叔也送吃的來了,端午節他們包的肉粽子,南方鄉下的梅干菜,都成了我家的飯桌上的佳肴。都是出奇的香美,女兒大口地吃著,贊不絕口。我每次舉箸必不忘記說:“這是鄰居爺爺奶奶送的,我們有好吃的也要送去啊!”每次說完,都感覺這話很熟悉,其實這是我父母當年對我們講過的話。
我一直在等著女兒“覺悟”的一天。3歲時,我送什么給別人,她都說:是我的!5歲時,我送什么給別人,她說:不許給!我從來都是對她說:別人送我們那么多好吃的,我們有好吃的也要送給別人啊!每次說過都要去送。她很不理解地撅著小嘴。
她7歲了,有一天,我蒸了一鍋大包子,出籠時,白白胖胖,香氣四溢,她幫我把包子拿出來,我餓得很,拿一個就吃,她說:“媽媽,你還沒有給鄰居爺爺送吶!”我一驚,說:“我吃完這一個就去送!”她樂了。
出門去送包子,女兒在后面說:“媽媽,我也一起去!”
任建歡摘自《女子世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