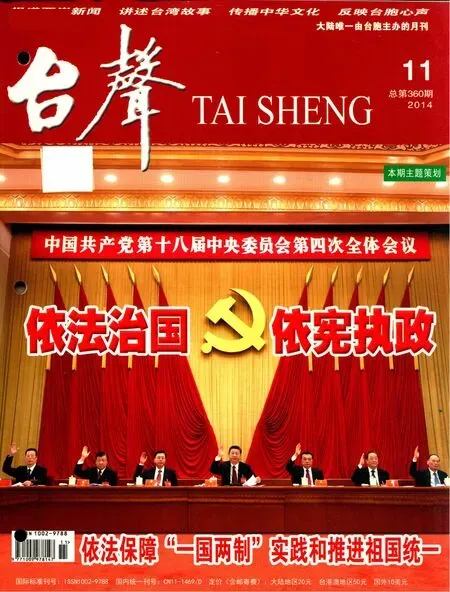老兵后人的心里話
文丨王睿 臺灣自由撰稿人 編輯丨安東 郵箱丨E-mail:Anthon83122@gmail.com
今年甲午海戰120周年。大陸在一系列紀念緬懷活動中,不但肯定清朝抗日軍人,也肯定國民黨的抗日軍人。換言之,只要為了近代國家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奉獻犧牲的中國軍人都應受到肯定。反觀臺灣島內除了極少數團體舉辦史料展覽和研討會之外,大多數人對甲午年這個對兩岸中國人而言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無感、無知、無視。
記得2011年,那陣子,島內長年被謔稱為“老芋仔”的來臺大陸老兵,忽然間被吹捧為“捍衛臺灣的勇者”。在長達近60年兩岸分隔之后,等到這些老兵盡幾昏聵失能、凋零殆盡之時,幡然有人追奉他們是“臺灣現代化的開創者”了。甚至還拍了部紀錄片,說是對他們“一個溫柔的敬禮”云云。仿佛半個多世紀來,除了選舉熱季,他們不曾存在過。而為了需要,他們才給人拿出來當作敬禮道具。這群被歷史遺忘的來臺大陸老兵們,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慢慢接受自己被歷史遺忘的事實。或許還因為,他們自己也想忘了自己的過去。可他們無人希望國家分裂對立,無人希望帝國主義染指中國主權領土,無人不以中國軍人自居。他們憤恨日本軍國主義,亦對美國對臺軍售無感;他們畢生素樸,沒去過百貨公司與咖啡廳,不懂得股票與投資;他們人單勢孤,除了國家和平統一、兩岸自由往來的孤獨愿望。他們看過對“林毅夫叛逃案”高談軍人武德與氣節的“國防部長”,聽過這位不曾參與抗戰,自外于中國歷史,否認國民革命軍亦是中國軍人的言語,又看著他因島內體訓致死的下士而黯然下臺的神情;他們還看過短短繼任6天的“國防部長”,因涉嫌抄襲而踉蹌下臺的狼狽;他們也風聞如今的島內“三軍統帥”對日本右翼政客說:“臺灣一直都支持《美日安保條約》,并認為這是東亞安定的基礎”,不知今天的“三軍統帥”是否還記得昔日自己年輕時的“保釣”歲月,釣魚島是120年來中華民族復興未競的標志啊!
有人說:“臺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但在所有美麗的臺灣人當中,只有一位作家陳映真,曾以小說《將軍族》、《累累》和《歸鄉》等作品,深刻而同情地關心過這些來臺底層大陸老兵的離散生涯。這些來臺大陸老兵們大多出身貧農家庭、故鄉在大陸農村。他們來臺后,因“反攻大陸”的需要,被“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暫調條例”和微薄的薪俸限制了婚姻的權利與條件,加上一張“授田證”和幾處“軍中樂園”耗光他們的青春與意志。我曾識得一位居住臺灣彰化榮民之家的老人,出生于重慶,國民政府在抗戰末期號召青年參軍之前,16歲的他輟學參加了杜聿明在昆明組建的傘兵團,后來擴編為3個團。來臺前夕,傘兵第三團選擇留在大陸,而他是一團的戰士。65歲那年,他初次回大陸返鄉探親。如今孤身一人的他,躺在榮民醫院長期照護病房里,插管呼吸,無意識地等待人生終點。作為晚輩,我無能為他的晚年或后事做點什么,連他在大陸的旁系血親來電打聽,我也幫不上什么忙,只因為他與我沒有親屬關系。但卻因為他,我才能知道曾與他相識的岳父的故鄉,位于河南新鄭市龍湖鎮的大司村。
我從沒見過岳父,他在我妻10歲時亡故,留下寡婦孤女。岳父在故鄉讀到高中,對家人說要出去干一番大事,原來是去參加抗戰。抗戰勝利后他離開部隊,卻也沒有回到故鄉,跟人輾轉來到臺灣開礦。后來礦場倒閉,兩岸也斷了聯系,回不去故鄉的岳父在臺灣成家,卻因一場車禍意外離別人世。沒有軍眷俸給的寡婦孤女自力更生,含辛茹苦,直到去年7月,已為人母的妻伴著年邁的岳母和一家大小,第一次來到我岳父的故鄉,豫劇團來村里整整唱了3天。我妻的堂弟曾在QQ里說:“姊,我爸生前說了,將來臺灣的親人回鄉,要唱3天大戲。這是他的臨終遺愿,我們都等著這一天。”聽說,岳父的母親臨死前還念念不忘她有個兒子在臺灣。類似的兩岸故事,也發生在今年離世的我父親身上。他生于湖南攸縣坪陽廟鄉的一個農村,15歲時虛報年齡參加防空兵,戰事結束仍不得返鄉。來臺后,由于遲婚的關系,我出生時,他已45歲,因而形成一種特別的世代鴻溝。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來臺大陸老兵與其后輩的世代鴻溝之所以巨大,實因為國家分斷的背景使然。隨著島內外的時勢變遷,這種背景不斷加大他們不被理解和不被接受的悲劇。深植我父輩意識里的中國人認知與價值,只是最素樸的民族情感與生活方式。他們以自己的生命遭遇,證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正當性與政治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