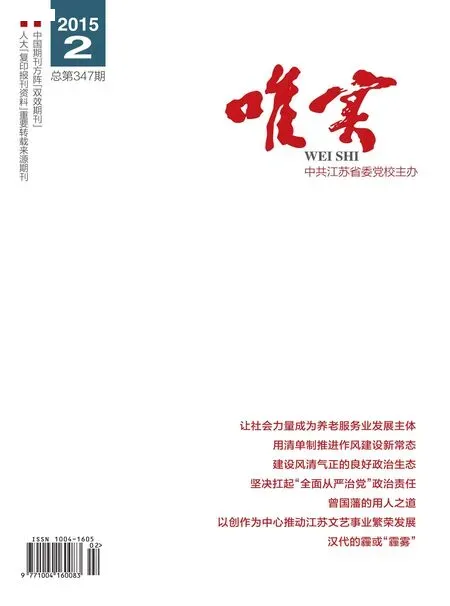晚年陳獨秀對中國基本國情的判斷
劉艷
早在青年時期,陳獨秀對中國的社會現狀就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在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后,他對基本國情的把握趨于正確。然而,大革命失敗后,陳獨秀在對中國社會性質及其發展階段、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務的判斷上卻得出一些錯誤的結論。
一、晚年陳獨秀認為中國的社會是一個“初期資本主義的國家”
大革命失敗后,陳獨秀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產生了重大變化。陳獨秀以為,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半殖民地”社會,中國革命有兩種趨向。其一,武力與工農群眾及革命化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結合,打倒國內一切黑暗反動勢力,建立革命的民眾政權,發展國民經濟;其二,武力與反革命的大商、買辦、官僚地主、土豪劣紳及懦弱妥協的資產階級結合,同國內外一切黑暗反動勢力調和,在政治上建立壓迫工農群眾的法西斯式軍事獨裁政權,在經濟上輸入道威斯式的資本主義。根據這種觀點,陳獨秀認為大革命的失敗,是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反革命派奪取了全國政權,這正好印證了他預計的第二個趨勢。
1929年8月5日,陳獨秀給中共中央寫信,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和革命策略進行了分析,錯誤地認為大革命“主要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增加了它的階級力量值比重”。[1]438他批評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觀點,他在重慶民生公司的講演中說:“我們觀察各國的經濟,要估計是哪一種經濟成分居領導地位,來確認它是哪一種社會。”他認為,中國社會的經濟成分沒有什么一半一半之說,占主導地位的乃是資本主義,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封建勢力在中國的存在是因為資產階級受了工農革命勢力的威嚇而與之妥協,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封建勢力也必須努力使自身資本主義化。
但是,他認為中國比起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來說還只能算是一個“初期資本主義的國家”,因為商業資本未完全工業化,農業之工業化則更談不上,統一的國內市場還未形成,工業生產也不發達。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針對中國共產黨抗日持久戰的戰略,陳獨秀在1938年6月8日的《我們為什么而戰?》一文中指出,如果中國真如共產黨所說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那么“封建或半封建”的中國與資本主義的日本的戰爭則是不必要的,因為兩者“對于資本主義之發展,還沒有勢不兩立的致命沖突”。他還認為,如果中國還是一個半封建的社會,則以封建半封建的農業國之經濟和軍事實力,絕對沒有與工業國進行戰爭的能力,尤其不能進行長期的戰爭。他認為自一戰以來,中國的資本主義工業,一直處在緩慢的發展過程中,中國社會性質并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認為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否認持久戰的合理性。
二、晚年陳獨秀認為中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與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
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群眾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陳獨秀早就認識到了這種矛盾。在大革命失敗前,陳獨秀已經看到無產階級、廣大人民群眾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正在上升,所以陳獨秀才向國民黨乃至整個國民革命提出質疑。他認為資產階級固有的階級性決定它在革命過程中一旦遇到下層民眾的獨立行動,就會與封建勢力妥協,甚至也“不會排斥帝國主義”。1929年10月10日,他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說:“想用階級聯盟的政策來貫徹革命目的,只是癡人說夢,這不能走到社會主義大道路,并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不過,陳獨秀還是承認封建勢力的存在,只是它已經降為次要反動勢力。所以他認為參加中國革命的農民,除了反對封建地主階級外,商業資產階級、買辦階級以及富農都是革命的對象。
應當指出,陳獨秀并沒有因此而忽略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并在時局的過程中承認這一矛盾會上升并據主導地位。他在1929年10月26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說:“帝國主義者為伸張其在中國的支配力量,除了鉗制中國經濟發展,還要操縱利用中國統治階級內部的沖突。” “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開始上升,陳獨秀在1932年托派常委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中提出了抗日反蔣的主張,主張在抗日和反蔣問題上,可以與自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黨派“共同行動”,這意味著陳獨秀開始放棄大革命失敗后全盤拋棄資產階級的觀點,肯定了在一定條件下與資產階級聯合的可能性。在全面抗戰爆發以后,陳獨秀立足于愛國主義的立場,放下與國民黨蔣介石的個人恩怨,支持國共合作、一致抗日,這表明陳獨秀承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三、晚年陳獨秀認為中國社會發展的根本任務應當是“開展經濟斗爭”,發展資本主義,準備走向社會主義
大革命失敗后,陳獨秀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不是組織武裝暴動,而是專心做反帝運動。在中共五大上,陳獨秀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迅速開展農民土地革命,大力武裝農民,建立農村革命政權,以挽救革命的建議”[3]261,仍舊堅持以城市為中心開展革命活動。1927年7月底,陳獨秀給中共臨時中央局寫信,提出了三點建議:“(一)把一切工會、農會及政權機關轉移給國民黨左派;(二)我們在國民黨左派政權下進行下層工作;(三)暫時專做反帝運動,工農運動不要有所動作,以回避大的犧牲和破壞。”[2]276 1927年11月12日,陳獨秀再次給黨中央寫信,認為當前的局勢,“以群眾力量掃蕩他們、奪取政權的時機尚未到。在實際行動上若取時機過早的政策,更是錯誤”[2]279-280,所以主張“開展經濟斗爭,來代替‘以暴動取得政權的‘幻想”[2]280。中日矛盾開始上升后,陳獨秀認為中國革命的根本任務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陳獨秀號召“組織及參加各地工人、農民、城市貧民的義勇軍運動,使之堅決地舉起反日反國民黨的旗幟,并要在正式軍隊做分化工作,是指脫離國民黨的支配,而成立反日反國民黨的義勇軍……在已有農民蘇維埃的省份,城市蘇維埃義勇軍一經成立,立即匯合蘇維埃區域的紅軍占領城市”[2]322。同時,原本力量就弱小的中國無產階級,由于大革命的失敗和中國革命策略上的失誤,“中國工人在數量上,在物質上,在精神上,都退回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狀況”[1]478。endprint
陳獨秀認為,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的革命形勢不是中共所言的“革命高潮時期”,而是“兩個高潮間的過渡時期”,因而應采取“退守政策”,不應采取“直接進攻政策”[1]435-436。1930年3月1日,陳獨秀在《無產者》創刊號上發表《我們在現階段政治斗爭的策略問題》,認為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正在走向統一和穩定,新軍閥混戰的結果,不是資產階級的政權走向崩潰,而是走向逐步的統一與相當的穩定,而“通常資產階級政治上的同意與穩定,乃是其經濟復興之可能的前提”。在資產階級已經掌握了政權的情況下,中國革命要進行的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而不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建立的政權也應該是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工農民主政府。他認為在當時的革命形勢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和“蘇維埃政權”的口號都是不符合實際的,提倡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來開展革命活動。在這里,陳獨秀仍認為中國革命的前途應當是社會主義。
但是,在陳獨秀看來,實現社會主義有“循序進化的路”和“跳躍進化的路”兩條道路。前者必須以內部經濟的政治的成熟為條件,后者則必須以外部的影響(刺激與援助)及內部政治的成熟為條件。但是,陳獨秀認為,這兩種條件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都不具備。他在《資本主義在中國——在重慶民生公司講演》中指出:“相當力量的工業無產階級及政黨,只有在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夠生長起來,沒有相當力量的工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自然談不上政治的成熟,外部的影響,目前還在等待時期。”而隨著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陳獨秀認為世界發展大勢可能因法西斯勢力的干擾而進入一個法西斯專政的時期。1942年3月,陳獨秀發表《再論世界大勢》,他設計了一個人類進化史表:上古世界(氏族社會民主制)→大地主大軍事首領的專制→古代世界(城市市民的民主制)→封建諸侯及其末期的君主專制→近代世界(資產階級民主制)→法西斯蒂專制→未來世界(無產階級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據此,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可能要進入法西斯蒂專制時期。
大革命的失敗,使陳獨秀身心俱損,革命信念和理念都發生重大變化。他認為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是卻完成了中國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在20世紀30年代社會性質論戰期間,陳獨秀提出,從歷史演進的角度進一步證明中國社會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陳獨秀承認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但否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聯盟的可能性,強調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的矛盾,這就在對中國主要矛盾問題的認識上出現了錯誤。但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陳獨秀基于民族利益贊成國共再次合作,這表明他仍不失為一個愛國主義者。陳獨秀認為中國社會的主要任務是發展資本主義,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任務仍舊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他的這種觀點并不是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只是認為當時中國落后的經濟現實無法超越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階段,而且力量弱小的無產階級也需要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積蓄能量,以準備在將來的革命中爆發。
參考文獻:
[1]水如.陳獨秀書信集[C].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
[2]王光遠. 陳獨秀書信集[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
[本文作者系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委托項目(11JD2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
責任編輯:彭安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