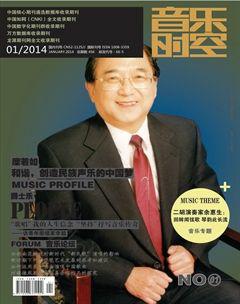從《八佾》看孔子的禮樂思想
董靜怡
摘要:通過對《八佾》篇部分文獻進行分析,從審美規范、審美態度和審美理想三個層面對孔子的禮樂思想進行詮釋。
關鍵詞:《八佾》 禮制 禮樂
先秦時期,周天子分封天下,為維護以周天子為中心的和諧統治,周公旦制禮作樂,成為各級貴族的政治和生活準則以及維護宗法制度必不可少的工具。統治者常用禮樂為手段以求達到尊卑有序的統治目的,因此禮樂制度在這一時期得到最完善的發展,而孔子則是周禮最偉大的擁護者之一。
作為教育家,他擁護制禮作樂的禮樂思想,常以音樂培養學生,強調音樂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并在音樂實踐的基礎上,進行理論概括,提出自己的主張。其思想受禮的制約,為政治服務,主張恢復周禮,重返周王政治權威下的社會秩序。《論語》是一部記錄了孔子的言行和思想的偉大作品,同時也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它反映出他在政治上崇尚“以政以德”,音樂應當受禮制的約束,為政治服務,并且強調音樂從道德上感化人的作用。其中《八佾》篇對孔子的禮樂思想有較為全面的展示,是其整體音樂美學思想的一個縮影,從文章中可以看出孔子的禮樂思想與周公的禮樂思想有所不同,他將禮樂施用的對象擴充為全體社會成員,并且在傳統禮樂的影響下,把周公宣傳的外在倫理關系內化為普通民眾的道德自省與“克己復禮”的主體自覺。下面本文將從審美規范,審美態度和審美理想三個層面對其禮樂思想進行詮釋。
一、審美規范: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這句話表達了對季氏享用禮樂規格僭越的強烈不滿。統治階級為了鞏固權利制定了一整套十分煩瑣的禮儀以及與之相配合的音樂。除八佾制外,不同場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禮儀有別,享用的音樂也不一樣。所有這些關于禮樂的規定,都是為了加強人們的等級觀念,最后達到鞏固其統治的政治目的。
“八佾”是古代的一種禮樂用舞,一佾八人,八行八列,共六十四人。《白虎通·禮樂篇》提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①按照禮樂制度,只有天子才能享用這個級別的樂舞。在禮樂制度中不同的級別享用不同規模的樂舞。諸侯用六佾,即六行,四十八人。大夫用四佾,三十二人。季氏屬于大夫級別卻使用了天子級別的規模,孔子認為此行為屬于僭越,是不可寬恕的。由此可見,“佾”的數量代表的是禮儀規范,社會的尊卑等級秩序正是通過“佾”這套禮儀得以體現。
禮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嚴密的社會秩序,從而劃分不同等級來規范社會。《通志·樂略》中提到,先秦時期“禮樂相須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由此可見禮與樂之間緊密的關系。《論語·季氏》中記載“不能詩,于禮繆;不能樂,于禮素”。一個國家的大型活動在“制禮”的同時必須“作樂”,進行與國家機構規模匹配的樂舞。對于統治者來說,禮樂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國家的興旺,因為“樂以象政”,也只有禮樂相和,才能規范人們的行為,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中國古代禮樂制度控制了中國幾千年來的音樂格局。它在制定初期的確維護了統治階級的政權,但隨著東周王權的衰落,周天子只能依靠諸侯的支持。而諸侯的強大同時對天子的地位也是一種極大的威脅,再加上僵化的禮樂制度并不是長久有效的治理手段,不能控制諸侯對其他音樂的追求以及對禮制的藐視,“禮崩樂壞”的時代逐漸到來。
二、審美態度:“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孔子音樂審美的準則之一。孔子的禮制思想是以禮為核心,強調人的情感培養,將情感體驗作為存在感的基礎和本源。在禮樂制度下,音樂表現的情感要具備道德上的純潔性和崇高性,還要受到理智的節制,不可過于放縱、任其泛濫,要講究適度、平和。除了《八佾》中貫穿孔子的音樂審美思想,《關雎》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音樂表達也強調了孔子倡導的“中和之美”,其情緒愉快而不放縱,悲哀而不悲痛,情感的表達才恰到好處。這樣“中和”的音樂審美才符合孔子“以情為本”的復禮之道。
孔子十分尊崇“禮制”,他認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人的一切行為都要符合禮制。其禮樂思想不僅強調個體內心世界的反省,還強調對性格情感的引導,除了要求音樂中情感的表達要有節制,不可放縱欲望,還在音樂審美上第一次區分了內容美和形式美,要求兩者要達到完美統一。孔子講“中和”強調事物對立雙方要保持平衡的狀態,即“禮之用,和為貴”,是“禮”中尊卑等級關系的“和”。 他主張情感在“樂”中的表現應當是適度和有節制的,“鄭聲”在孔子的審美標準下是“無節制的”,所以被斥為“淫”聲,因此他深“惡鄭聲以亂雅樂”。
三、審美理想:“盡善盡美”
《八佾》中記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孔子認為《韶》與《武》就樂舞表現形式來講都是美的,音樂都是符合美感的。但在內容上,《韶》樂舞表現舜以德治理天下,以禪讓選舉王,符合孔子的社會政治理想;而《武》樂舞表現的是周武王討伐商紂得天下的內容,盡管是正義之戰,但由于運用了武力不符合孔子的道德審美。所以孔說《韶》“盡善”《武》“未盡善”。“美”與“善”相比,孔子認為善是根本,是內容,也是審美價值的基本標準。由此可見,孔子眼中的音樂不是單純的藝術,而是被賦予了政治倫理內容的表現形式。
孔子“盡善盡美”的審美標準除在《八佾》篇中有體現,在《雍也》也有提及:“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這兩條語錄表明,孔子認為“質勝文”則“野”,是粗鄙的,而“文勝質”則“史”,是虛浮,華而不實的。只有“文質彬彬”,相配得當,相得益彰,這樣才能做到“盡善盡美”,達到維護禮制的目的。這一觀點是他對藝術美的追求,也是孔子審美理想的集中反映。
《禮記·樂記》中提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和則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②孔子對音樂的理念也如此,認為音樂應當“樂者天地之和”,保持和諧高尚的境界。根據《論語·八佾》中,可看出孔子的基本禮樂思想。孔子堅定不移的維護周禮,是希望通過“克己復禮”完成自己的文化使命。他在“禮崩樂壞”的時代下依然堅持周公禮制,認為禮的本質是“仁”。除此之外,他還認為禮樂本是一體,本質內容相同,“立于禮,成于樂”,并將禮升華為樂,認為樂是人的最高境界。孔子在繼承先王“禮樂”文化的基礎上,將其核心內容定位為社會秩序之上的“人倫和諧”,將禮樂提升到了文化的高度。他創新原有的先王禮樂文化,從其社會政治功能出發,進一步把傳統禮樂文化塑造為以社會秩序和人倫和諧為目的,以禮教和樂教為內容,以政治倫理平民化為途徑的禮樂教化論,并且以“仁”解釋禮樂,發掘先王禮樂文化的內在人性和心理基礎。更重要的是,孔子所謂的社會秩序和人倫和諧的觀念,是以政治倫理的平民化和普及化為平臺,來體現仁、敬等人性本質。由此可見,孔子的復禮思想,不能簡單地看成對周公制禮作樂思想的照搬,而是創造性的發展,并對先秦的禮樂思想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注釋:
①楊寬:《古史新探》,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②楊樹達:《論語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