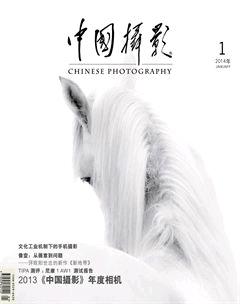被算計的攝影與世界
羅布


江湖上盛傳:手機攝影的時代即將來臨;傳統(tǒng)斷,經典絕,大師離場,影像狂歡,歷史重寫……手機攝影如此之快地兵臨城下,讓沉溺于傳統(tǒng)精英攝影趣味的人有點不知所措。
20世紀,膠片相機雄霸百年。進入21世紀,數碼相機風頭正健,沒曾想嬰兒的一聲啼哭,庶幾使得數碼夢斷。
嬰兒的這聲啼哭是在1997年6月11日。那天,美國硅谷的工程師菲利普·卡恩(Philippe Kahn)在醫(yī)院產房外陪伴待產的妻子,隨身攜帶了筆記本電腦、數碼相機和手機:準備等孩子一出生,就拍下照片,連上網,把孩子的照片傳給親友——在當時,這還是個很新潮、也比較麻煩的事兒。無聊之際,他突發(fā)奇想:能不能把手機和數碼相機連在一起,弄一個類似“拍照手機”的玩意兒,直接用手機拍照、發(fā)送,那不快多了嗎?
工程師的強項就是動手能力。幾個小時之后,一臺“手機+數碼相機”的新奇玩意兒就誕生了——拍照手機在產房里邁出了第一步。
真正具有商業(yè)意義的第一臺拍照手機,是2000年9月由日本第三大移動運營商J-Phone(即現在的沃達豐)與夏普合作推出的J-SH04,其內置的11萬像素攝像頭在當時還沒有引起重視,更多地被認為是一個“概念機”。但其此后的發(fā)展讓人瞠目結舌:2003年,夏普推出了百萬像素級手機;2004年,200萬像素級手機問世;2006年,1000萬像素級手機問世……今天,大街上隨便叫住一個人問他手機的像素,也在600萬以上。更重要的是,這些攝影手機并不是在閑著,而是隨時隨地都在拍照。以手機攝影為中心的各類攝影活動,比如論壇、展覽、比賽也火了起來。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攝影》雜志在2013年夏天,與中國通信攝影協會和中國電信決定聯合舉辦一個使用手機拍攝照片的攝影大展,也就是首屆“天翼手機杯”全國手機攝影大展(獲獎作品選登見后;更多作品和關于手機攝影的更多實用資訊,可見本刊2013年增刊第二期),以推動影像文化的發(fā)展,促進攝影活動的普及,引導大家使用手機拍攝出更好的照片,用影像來豐富文化生活。短短三個月,來稿數量達到80000幅,其中不乏佳作——手機攝影的熱度和手機影像所能達到的精致度,可見一斑。
而在專業(yè)攝影領域,比如報道攝影,手機攝影也在扮演著日漸重要的角色。諾基亞公司去年10月宣布,將每年的10月20日定為“國際移動攝影節(jié)”,該公司還將其旗艦手機Lumia 1020(2013年7月發(fā)布,像素達到4100萬)直接發(fā)給美聯社的攝影記者使用,意在搶占報道攝影手機時代的先機——而在這之前,就已經有不少攝影記者在一些極端情況下(比如戰(zhàn)地或一些中東國家的街頭沖突)成功地使用手機做報道。2010年,戴蒙 · 溫特(《紐約時報》攝影師)的手機報道攝影《阿富汗士兵的日常生活》在美國新聞攝影界精英薈萃的“國際年度照片大賽“(PoYi)中獲三等獎,此后,手機拍攝的新聞照片成為國際主流媒體上的常客。
所以,說攝影進入了手機時代并非囈語。
手機攝影不僅指向外部世界,也指向人的內心。鏡頭如眼睛一樣,天生具有好奇心,它獵取的每一個影像,都是在滿足人潛在的觀看欲望,但手機的貼身性和隱秘性,使得手機攝影對這種觀看欲望的滿足更加直接、露骨。不僅如此,手機攝影還打造了屬于自己的觀看方式:共時性觀看。在膠片攝影年代,一幅照片從拍攝到發(fā)表,短的需要幾小時,長的需要幾周甚至幾個月;讀者的互動就需要更長時間。在這個時段,攝影師可掌控每一個環(huán)節(jié),有充分的時間玩味攝影過程(包括與對象的交流、自己內心的感動等各種細膩因素),讓攝影五味入心。那樣的照片都有特殊的“光韻”。鮑德里亞說,濕版時代的攝影師不是拍照片,而是直接“住進照片里”,能將鏡頭前的“人及其頭顱所頂戴的命運” 一同呈現出來。因而,傳統(tǒng)攝影對應的是一種歷時性的觀看方式。在手機攝影時代,從你按下快門到通過微博或“面書”(Facebook)、推特(Twitter)呈現在世界面前,可能用不了一分鐘;那些大V們的“粉絲”隨之而來的“贊”,也許只要幾秒鐘——手機攝影時代,影像的獵取與分享幾乎是在瞬間完成,對應的是共時性觀看。
這種共時性依靠的是完備的當代科技。攝影術本身就是現代科技的產物,但它從沒有如今天這般與科技生死相依。今天的影像,早就像電視、冰箱一樣是無形的流水線上的工業(yè)產品;準確地說,屬于一種“文化工業(yè)”產品。
“文化工業(yè)”的概念,據當代馬克思主義藝術批評的大匠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德國人)回憶,是1940年代末他在《啟蒙辯證法》一書中首先使用,后來經“法蘭克福學派”不斷深化,遂成為解析后現代藝術最鋒利的手術刀之一(阿多諾:《文化工業(yè)再思考》)。在阿多諾的語境中,“后現代藝術”這個概念與他所謂的“當代資本主義藝術”可以通用,也與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提出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可以互通有無。阿多諾認為,“文化工業(yè)”完全是現代工業(yè)社會的產物,是資本尋找新機會的結果,它與娛樂、休閑、消費主義直接相關。在現代工業(yè)社會之前,娛樂休閑雖然也存在,但所占比重非常小,不是一種大眾性質的普遍需求。更重要的是,當時的社會生產方式沒有生產出一種機制,主動引導人們去放松和消費(即使有,力量也非常小,遠沒到主導社會生產方式的地步)。但現代社會就不一樣了,它不僅生產娛樂產品,而且源源不斷地生產娛樂需求和娛樂者本身。換句話說,你在娛樂消費的同時,你本身也成為消費對象——成為文化工業(yè)的消費對象。而文化工業(yè)對消費的引導,是通過提供設計出來專門讓人玩兒的產品來實現的,手機攝影就是一個絕佳案例。比方說吧,你有個手機,也許你根本就不需要它有照相功能,但廠家主動提供了照相功能;你根本不需要上網功能,但廠家主動提供了上網功能。結果就是,你會完全按照廠家的“貼心”設計來使用手機,并心甘情愿地為之付費——這些費用就成為文化工業(yè)(資本)的利潤。如果你堅持不照相不上網,他們還捏造了一套理論來嚇唬你,迫使你屈服,這個理論就是時尚理論:你不會手機上網,不會手機拍照,不用“面書”或推特,你就out了,是一個老古董土老帽鄉(xiāng)巴佬……很快,你“從”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