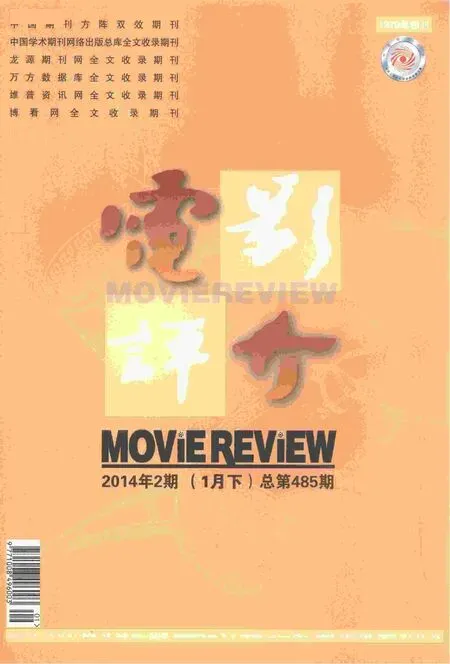《美麗中國》的詩意美境
□文/楊會,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藝術設計學院講師,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生

紀錄片《美麗中國》海報
《美麗中國》系列作品反映了中國人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簡樸、淡然的生活場景,讓我們在動人的細節與情節中感受造化的奇跡,人們以順應自然的方式與自然和諧地共生息。
一、形式手段
根據紀錄片總制片人連拜恩介紹,節目中使用大量的蒙太奇、慢鏡頭、長鏡頭、剪輯、特效來獲取最自然最美好的瞬間。制作組通過多種形式手段為觀眾奉獻出美輪美奐的畫面,創造了美麗中國的詩意畫境。
(一)蒙太奇創造節奏產生詩意
節奏是詩意得以產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紀錄片中,蒙太奇創造的節奏產生的意境大于所有意象之和,也使得影視作品的意境產生了動感和層次,它賦予了作品詩歌般的節奏和韻律,凸顯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境界。在青山綠水間,人們的衣食住行無不與自然息息相關,作品鏡頭轉向了平常的莊戶人家其樂融融的生活場景。在此場景中,以古老爹不同尋常的狀態設下懸念,古老爹專注思考的場景與因為燕子歸來忙碌的場景不斷交叉進行,在往復的交叉蒙太奇中交待出播種時節與燕子歸來的關系,人與萬物以順應自然規律的方式而存在著,在安然而忙綠的生活中傳達著詩意;深夜,湖面低旋的大足鼠耳蝙蝠不斷略過湖面,紅外鏡頭記錄下大足鼠耳蝙蝠張開半透明的雙翼與激蕩的湖水共舞的場景,極其優美,類似的飛舞慢鏡頭重復了多次,形成了很強的節奏感和韻律感,也創造了強烈的視覺沖擊力;荒涼的雪景中艱難生存的藏羚羊覓食的場景,由特寫到大遠景的連續過渡拍攝,自然而充滿情感,在荒瘠的群山中可以感受到點點生命的執著,充盈著靜穆的詩意。
(二)暫緩或暫停創造詩意
約翰·赫蘭德認為“各種各樣的停頓賦予詩歌以音樂性和魅力,而且停頓引導著讀者領悟這種美。”[1]同樣,在紀錄片中,長鏡頭、慢鏡頭、特寫等鏡頭的緩慢與冗長恰好使得時間的流逝與空間的移換存在于鏡頭內部,通過長時間的冷靜而沉默的暫緩或暫停,減少了信息的傳達,造成了默默凝視的效果,將世界的真實潛移默化地印照在觀眾的心底,在靜默的注視和舒緩的移動中,營造出了詩意氛圍,在對人和物的靜默關注中,恬淡而清醇地表達對困頓生命的揭示和對積極生命的頌揚。長鏡頭抒情氣氛較濃,作品在面對沙漠、雪山等很多場景時,均使用了長鏡頭拍攝,保持了時空的連續性和統一性,在節奏上比較緩慢,在凝神注視中,營造出孤立絕緣的詩心觀境;神秘的地下山洞間別有洞天,滴水濺落雕琢石筍的特寫慢鏡頭,水花飛濺,晶瑩如珠,輕盈如芒,從時空中關注水花這一微點并使之永恒化,如此常見的現象卻因陌生化的藝術手法表現而別有一番情趣;而特寫微觀鏡頭關注的動物的微觀世界生活,具有生活中不常見的特殊的視覺感受;在云南的潑水節場景中,人們在飛舞的水花中開心歡笑的模糊攝影營造了夢幻和浪漫的氣氛,造成了豐富多彩的虛化效果,更新了我們的視覺體驗,表達的想象空間更大,也更具新引力。
(三)奇異形式語言創造詩意
貝爾從視覺藝術出發,把線條、色彩與主體的審美情感結合起來,提出了有意味的形式。他說:“在各個不同的作品中,線條、色彩的關系和組合,這些給人以審美感受的形式,我們稱之為有意味的形式。”[2]有意味的形式追求的是純粹的美,是超現實的同時也是新奇而陌生的,這種充滿情感但陌生的形式表達中充盈著詩意的美。延時攝影將物體或者景物緩慢變化的過程壓縮到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呈現出平時用肉眼無法察覺的奇異精彩的景象。在凝縮的時光里展示著生長與變幻,作品中城鎮中人群的過往,竹筍的迅速生長;梯田在光影中的變幻闡釋了時光的變遷。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開始的多場景的無邏輯的剪輯展現出沙漠的線和面的構成美;美麗的丹頂鶴們在夕陽下引吭高歌翩翩起舞的優美剪影既凸顯了丹頂鶴的優雅身姿,也帶來了美的震撼和感動。
二、意象表達
詩意化的表達中,需借助具體可感知的形象來傳情達意。艾略特在《哈姆雷特及其問題》一文中,提出通過一系列實物、某種場景、一連串事件等“客觀對應物”[3]激發人們的情感。我們可以視“客觀對應物”為人們的“意中之象”,即意象。《美麗中國》作品由多個主題的序列組合而成,多個主題序列緊緊圍繞山、水、人、物之間的形象描摹展現出秀麗山河的詩意畫卷,也娓娓道出醇厚的中華情。
作品《美麗中國——錦繡華南》從美麗的漓江山水開始,星星點點漁火間,漁民撐桿而行,葉葉扁舟在黑夜中靜靜滑行,漁火、人、扁舟形成的點、線、面的構圖和諧而詩意。
隨后由雨水季節的黑色鸛鳥在水田覓食的場景轉入到南方人賴以生存的農作物:水稻的種植。在與自然協調的過程中,人們再次以充滿智慧的方式解決了生存問題,崇山疊巒之間的梯田是人們為天空準備的鏡子,陽光在梯田的水面燁燁生輝,光影的變換中隱喻著長久的耕種方式的綿延。不斷傳承的農耕文化中,體現了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
接下來的主題轉入重重山巒間的神秘地下世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創造了神奇的石鐘乳和石筍,帶來了新鮮而神秘的探險空間,也造就了無數稀有的地下生物的生存空間。
在山巒間自由攀爬的是黑葉猴,黑葉猴們相互梳理毛發;猴媽媽與小黑葉猴們在叢林間休息與嬉戲,并在夜間尋找安全棲息處等都很好地體現了傍山而居的黑葉猴們的生活狀態;當然依山而存的生物還有人類,很多孩子跋山涉水去往大山深處的學校:位于山洞中的學校,洞穴中不僅有學校,還有神奇的生物們:家畜、燕子、蝙蝠等,燕子們為人們準備好農作物的肥料;山洞深處還有黑暗中的舞者:大足鼠耳蝙蝠們馳騁于暗夜的湖面并獵食湖中的魚兒。
接下來鏡頭轉向浩瀚的湖面,人們撐桿滑行于湖面,飛鳥在湖面低旋,人們在傳統的捕魚生活中借助鸕鶿捕魚,鏡頭跟隨鸕鶿進入水底潛行獵魚,繼而跟隨魚兒浮出水面;傳統的獵魚方式還有草海中的地籠捕魚,在天水一色間,人們遠遠地點綴著詩意的山水。人們捕食魚類但也自發的保護著野生動物,這一行為使得瀕臨滅絕的物種的數量逐漸增加。
初升的太陽從云海間出現,在黃山迎客松間升起,山水畫般的朝陽初升的場景在眼前浮現,人們安詳地生活在田園牧歌般的生活里,人們在種植水稻的稻田里喂養鯉魚,在收獲的季節,開始了慶典,歡樂而輕松的生活場景在村落里年復一年的上演。
質樸的人們,自由的生物在青山綠水間,愜意而和諧地共存,《美麗中國》在客觀的敘述中展現出美麗中國的秀麗山河中執著、自由的生命體;以真誠而熱烈的態度關愛這一切,在生動的形象中傳達著情感,詩意的境界在情感和意象中契合,這一境界在瞬間見永恒,在細微中展現無限。
三、詩意美境
“中國人一直以來追求人與自然契合無間的人生境界和精神狀態,注重內在精神境界的追求。在審美特質上,主張從人與自然的契合中去探求美,追求宇宙精神和人的精神的契合,強調心與物、情與景、形與神、虛與實的統一,講究情、景、境無限融合的詩情畫意,重視自然之性及和諧之美。”[4]《美麗中國》作品中所展現的主題序列:桂林的漓江、元陽的梯田、西藏的雪山、新疆的大草原等,都是山、水、人、物的相依相存,“作品從自然的角度解讀人類,從全知的角度來觀察人類的行為,巧妙地將動物的世界擬人化并與人的世界進行關聯,用隱喻和警示的方法來審視人類的價值觀念及許多悖論性行為方式。”[5]在形象的表達中勾勒出整個意境,以形象的創造性表達,體現出“萬物有靈”的靈境,在山、水、人、物的情景交融中,展現出韻味無窮的美感特征,呈現生命律動的本質特征,集中體現了天人合一的審美理想,詩意化地表達出人類與自然及生物的和諧境地。
[1][3]黎志敏.詩學建構:形式與意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8,92.
[2]貝爾.藝術[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4.
[4]汪濤.中西詩學源頭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8.
[5]楊錚等.自然類紀錄片的思維品格[J].新聞愛好者,2010(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