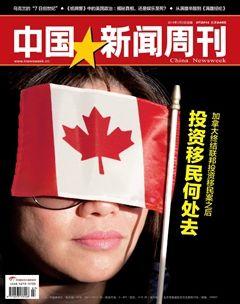《紙牌屋》中的美國政治:揭秘真相,還是娛樂至死?
劉思羽

《紙牌屋》第二季又火了。
新一季同樣13集一氣放出,延續第一季的話題效應,第二季上載第一天,觀劇人數就是第一季的八倍,其中不少人在周末一口氣看完該季13集。面對這種“全民觀劇”態勢,連美國總統奧巴馬都忍不住發推特專門“懇求”,先睹為快的人不要劇透。
也因第一季的火爆,搜狐視頻網站買下《紙牌屋》第二季在中國獨家播映權。相當一部分中國觀眾,認為該劇揭示了美國政治“腐朽而黑暗”的真相。其實,《紙牌屋》在美國引起的諸多爭議中,關于劇情是否反映現實,也是最為關鍵的一條。
《紙牌屋》真的是看清資本主義政治中心的窗口么?從第二季中幾條故事主線,來看看它們與現實的關聯。
白宮的“暗戰”
在第一季中,主人公弗蘭克·安德伍德是作為國會多數黨的黨鞭,所以劇情內容不管如何千變萬化,多是圍繞參、眾兩院和黨派政治斗爭展開;到了第二季,主角成功當上副總統、并繼續向更高目標前進,因而劇情的重心,順理成章地轉到了以白宮為中心的行政體系,以及白宮與國會之間不可避免的交鋒。
在第二季中,弗蘭克直接對觀眾拋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副總統有兩種類型:受氣包與斗牛士。你以為我是哪一類?”以副總統的身份、設計逼總統下臺,并取而代之,這就是第二季的劇本大綱;也可以說,正、副總統之間的關系,是本季最核心的劇情元素。
在現實中,根據美國憲法,副總統的確是總統職位的第一繼任人選,當在任的總統于任內死亡、辭職或者遭到彈劾時,副總統會繼任成為新的一任總統。從理論上說,副總統有“暗算”總統的可能。但這種理論至少得基于兩點假設:一、正、副總統之間不和,且上升到對立的程度;二、副總統有意通過如此“暗戰”的方式成為總統。
現實中要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并不是很容易。首先,作為競選伙伴,正、副總統是利益共同體。“陰謀論”者可以假設他們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但競選階段彼此的搭檔,已經是經過無數輪談判妥協的結果,以確保對方不會“背后使刀”。就算人心難測,在現實中當副總統的人善于偽裝,或者像弗蘭克這樣雖然明擺著野心極大、總統迫于形勢不得不任命他為副手的情形,但“副手逼宮”的代價依然太大,更不用提在法治相對完善條件下、設計害死現任總統那種極端不靠譜的手法了。
在美國歷史上,共有九位副總統接任了總統職位,其中八位是因總統死于任內繼任,只有福特是因為當時尼克松總統辭職而繼任的。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九位曾經的副總統,一手策劃了那些總統的死亡或者離任。
《紙牌屋》的編劇自然是熟悉美國歷史的,為什么還要將第二季主線如此設定?應當說,編導首先抓住了觀眾的獵奇心理:最沒有可能發生的事,從講故事的角度來說,恰恰也是最吸引人的。更何況,“擠走總統、取而代之”的決定,是符合第一季以來主角的性格設定:以弗蘭克的野心、性情與能力,在他已經做到副總統的時候,要繼續滿足他的權力欲,只能是自己做總統。
在受制于情節合理的邏輯下,編劇導演的功力體現在:不僅要讓主角的動機與行為“合乎情”(契合角色性格與心理),更要讓觀眾覺得“合理”,即弗蘭克的整個計劃與一系列行動,得在邏輯上能“自圓其說”。也就是從這一步開始,《紙牌屋》的手法就與“真實”不相干了:一切只為捏造得順利。因此,觀眾在看完第二季后,可能會感概:一是弗蘭克的運氣太好了,二是他的對手太弱了。當然,這種“不真實性”,很難用來質疑劇情的“不合邏輯”,畢竟,所有的故事框架和由頭都是人為設定的。
“99%的情節都是真的”?
在“繼任總統”這個總線索下,《紙牌屋》第二季依然有非常豐富的支線劇情。主演凱文·斯派西曾說該劇99%的情節都是真的。如果把他說的話,改成“都有真實(事件)作參考”,應該更為準確。即使如此,如果考察該劇是否反映了華盛頓決策圈的“真實面目”,單看事實本身是不夠的,還得看它援引事實的根據、以及在劇中處理的手段,是否能在現實環境中發生。
應該說,劇中還是有些情節,無論從緣起,還是表現過程,乃至最后解決方法,都與現實比較接近。比如,劇中表現的白宮與國會的預算之爭,以及可能引發的聯邦政府關門事件,在現實中奧巴馬任期內已發生,最后也的確是通過兩黨妥協而解決的。現實與電視劇唯一的不同,只在雙方妥協中各自用來交換的利益名目不同。
事實上,關于“參考”現實政治事件,《紙牌屋》系列的編劇標·維利蒙承認,劇中很多支線細節,并非一開始就規劃好的,而是在劇本寫作過程中,根據最近發生的熱門事件而 編排進去的。因此,關心時政的觀眾,在看該劇時,會覺得更加親切。
比如,由第一季延展過來的環保政治話題,雖說主要涉及弗蘭克的太太克萊爾,而且只集中在“水污染”這個比較窄的環境問題,但其中影射的環保政治現狀,還是與現實有很強的關聯度。不過,環保政治,說白了,和其他主題的政治活動一樣,其核心依然是利益斗爭、交換與妥協。現實中,水污染其實是七八十年代的環保話題,且后來通過立法已基本解決。
有心的觀眾,還是能通過《紙牌屋》中對這一主題的演繹,聯想到當今的幾個熱點問題,如氣候能源法案、Keystone輸油線路建設等。顯然,編導的這種手法,就是典型的“借古諷今”。
劇中另有相當一部分支線情節,只是用了現實中某些案例作為由頭,往下講述的,則都是虛構的故事。比如克萊爾在第四集中難得真情流露地“揭秘”,對應的是現實中美軍內部難以忽視的性侵害問題。不過,這種政治問題,在劇中只是作為角色其他活動的籌碼,并非直接表現的對象。
此外,劇中作為聯邦調查局“魚餌”的黑客那條線,很難不令人聯想到現實中的斯諾登事件,這種手法,是典型的“顧左而言他”。
有些情節,如第二季第11集中令人驚詫的“三人行”,這種權勢人物荒唐的性活動,讓人想起肯尼迪、克林頓等白宮首腦的風流韻事。只不過,在《紙牌屋》這里要表現得更為夸張。
值得一提的是,與中國有關的外交題材,成了第二季主要劇情線索之一。而編劇在經營這一線索時的手法與功力,足以管窺全劇。馮山德這位政治掮客,串起了劇中所有和中國有關的情節。至于那些具體的事件,從有現實參照的橋梁工程投資與中日東海摩擦、到“表層屬實、幕后難考”的匯率與稀土事件,再到基本上屬于異想天開的“賭資賄選”,盡管虛實不一,但這些情節都只是為了強化一個意思,即:中國,的確是美國在目前階段最關心的對手。與其說這種描繪反映了美國當前的政治現實,不如說它“迎合”了美國民眾對中國的看法。
事實上,整部《紙牌屋》都是這樣一種“迎合”。
作為一部以純粹描繪政治黑暗面為己任的娛樂作品,又經由精確算計用戶網民偏好的渠道商制作推出,都注定了該劇是以“娛樂”和“博取話題”為最主要目標。借用老狐貍弗蘭克的句式問一句:美劇有兩種形態:娛樂與更娛樂,你以為《紙牌屋》是哪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