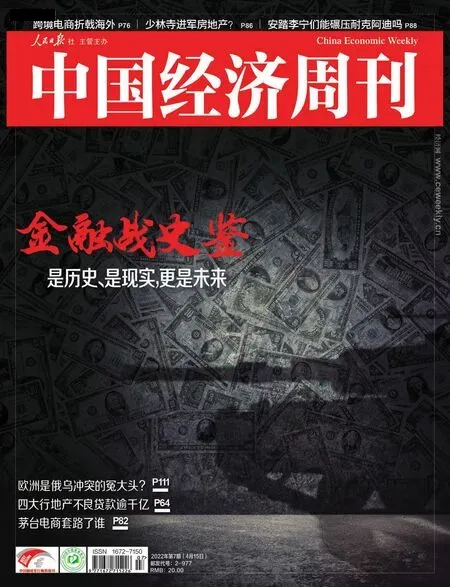上海報業集團的新媒體“野心”

一個多月前,解放日報報業大廈的九樓電梯口,張貼了針對下屬子報《新聞晚報》休刊的106個競聘崗位,基本覆蓋了待解決的采編人數。但有十幾個記者在反復討論榜單細節后,卻作出了同樣的判斷:真的“下崗”了。
這些來自《新聞晚報》財經部和經濟部的記者放榜前就有了心理準備。除了在財經報道著墨較多的《東方早報》,新成立的上海報業集團(由解放日報報業集團和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整合重組)素來缺乏財經“基因”。最后公示的榜單上,明確與之相關的記者崗位只有3個。
多數財經、經濟記者因此流失集團之外。不過,近幾天財經媒體圈熱傳的一份招聘啟事又喚起了這個出走團隊的“鄉愁”:上海報業集團高調宣布為籌備中的互聯網創業項目募集100個財經媒體人。
雖然許多人還抱著霧里看花的姿態,但這艘據說代號為“界面”的巨艦尚未出港,便已被貼上了“中國彭博社”、“雪球+華爾街日報”種種華麗標簽。剩下的問題似乎只有一個:盛名之下,它究竟能走多遠?
新項目的野心:
彭博社+華爾街日報
其實上海報業集團內部早就有過將做“增量”的傳聞,去年12月底甚至有一條消息稱,集團將辦一張財經報紙同城叫板上海東方傳媒集團(SMG,原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旗下的“第一財經系”。
而一個月前,虎嗅網和鈦媒體刊出兩篇“爆料文”,讓大家感覺到,鉚足了勁呈現一種新型經營思路的上海報業集團遠比坊間設想的更有想象力。
虎嗅網“爆料文”稱,上海報業集團將改變一財等傳統媒體的做法,打造“雪球+華爾街日報”,其描繪的圖景大大顛覆了媒體的定義:記者采寫的報道不再為廣告鋪墊,而以輿論干預的能量粘合一群真實投資者參與的類似雪球的社區;集團角色先由主導公共傳播的媒體搖身變成金融信息的提供商,再變身金融服務商,最終靠交易、數據和金融產品銷售賺錢。
聽起來確實耳目一新,不過在2月12日的招聘啟事亮相之前,這個眾方矚目的項目并不能算是真正面紗除盡、雛形初現。
“相比‘雪球+華爾街日報’的做法,上海報業集團的真實訴求更有野心,近似‘彭博社+華爾街日報’,做高質量通訊社的同時搭建一個龐大的金融數據庫。”執教于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的魏武揮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道。自上海報業集團成立后,他曾多次通過自媒體發聲、持續評點。其母正是與解放日報報業集團淵源頗深的知名財經媒體人賀宛男。
“彭博社的交易員客戶需要的信息最大訴求是簡短和快速,要的就是那幾秒鐘時差,所以它的報道并不側重對‘小道消息’的熱烈追逐,而是側重對流言的核實。”魏武揮解釋道。記者注意到,此次招聘啟事對主攻“財經原創資訊”的期權記者提出的第一點要求,即是“在上市公司擁有信息源,對重要財經新聞和商業事件具備信息核實能力”,與彭博社的思路高度吻合。
魏武揮認為,這也意味著未來呈現于這一新媒體的報道很可能以三五百字的快訊為主,注重閱讀體驗的新聞寫作退居次位,“多數報道將是寫給非常窄的專業受眾看的,而不是面向普通讀者。”據悉,計劃招募的60個“期權記者”更是突破“記者”的內涵邊際,來自金融機構和行業內部人士將大受歡迎。
“它看中的還有像彭博社那樣打造一個網上社區的高端平臺價值,招聘啟事中提到‘聯名專業投資網站提供上市公司分析報告’,‘激勵專業人士撰寫公司價值分析及提供商業信息’就是流露出打造一個凈化版雪球的意圖。”魏武揮如是說。
而“界面”對新聞的雄心也并未全部褪色,它比彭博社更有夢想的地方或許在于想追隨《華爾街日報》的步伐,依靠媒體影響力持續生產足以撼動股價的新聞,所以對“對重要財經新聞和商業事件具備敏銳洞察力”的傳統記者也拋出了橄欖枝。
遠學彭博社,
貼身PK萬得、大智慧
新項目事無巨細的戰略目標中,甚至還包括“為上市公司提供投資者關系服務”這樣的財經公關公司業務,被媒體人戲稱為“要將金融服務一網打盡的節奏”。不過,也有不少專業人士在受訪時對此持保守態度。
上海一家QFII操盤手Vincent對記者坦言,彭博社的成功并不是靠新聞團隊支撐起來的,復制又談何容易,“當年創始人彭博自己就是投行出身,盈利來自面向華爾街用戶高價出售和出租彭博終端機。”
作為彭博專線服務的用戶,Vincent認為彭博機的核心價值在于每天發布大量股票、債券行情和匯率、原料價格等實時資訊,以及專業度極高的操作手感,令機構愿意為年租金超過2萬美元的終端買單,“在擁有自己的新聞社之前,這種依托硬件的優勢就已經形成了文化,許多圈內人視使用彭博終端為一種身份的象征。”
一個具有說服力的例子是,2009年彭博社收購了《商業周刊》,將當時專訪亞馬遜掌門人的獨家稿件優先發布在終端機上,最終左右了操盤手們的拇指,令亞馬遜當天股價上升了5個百分點。“國內在機構用戶中比較有名氣的萬得資訊和大智慧,也都是先搭數據庫的路徑,上海報業集團的新產品要想拿到通訊社牌照不成問題,但如果一開始只靠媒體人來掌舵,可能在建庫方面經驗略顯不足。”
圈內盛傳,原《第一財經周刊》創始人何力團隊正是該項目的幕后操刀人。對此,何力則向媒體表示,目前還不方便透露。
從履歷上看,何本人是“土生土長”的媒體人。一位與新項目有過深入接觸的人士還透露,本次招聘以前,何力已從《第一財經周刊》挖走了多名骨干作為中層班底。
擁有10年財經報道經驗的上海媒體人老許也對“界面”持冷靜的旁觀姿態。“拋開運營層面不說,能否招募到一支穩定的高產能高質量的采編隊伍,招募到足夠滲入行業、能持續拿料的記者,也極富挑戰。”對于新奇的“期權記者”概念,老許直言“比較虛,在找到盈利保障之前,期權沒有什么意義”。他認為,未來可能更多依靠高薪酬向業內人士約稿的兼職模式。
魏武揮則表示,呱呱落地后,“界面”要直接迎擊大智慧和萬得這兩位“成名英雄”,也是優劣勢互見。根據截稿前最近一個交易日股價,大智慧市值為160億元左右。新項目即使最后敲定的投資額正如傳聞中那樣高達四五億美元,要拿這些錢做成一筆100多億的生意,也絕非易事。而在機構用戶中,萬得的市場份額幾乎形成了壟斷。
“不過,上海報業集團的行政資源也會是一大優點,比如可以和上海證券交易所談,先不說排他性,采購的時候能不能算上它一份?”魏武揮這樣分析,“前段時間《解放日報》的App‘上海觀察’一下子認購了10萬份訂戶,每份訂戶征收100元,這種資源形成的效率能量不是普通民營企業可以企及的。”
據悉,盡管攜手多方,上海報業集團仍將對新項目控股,官方口徑雖對合作伙伴三緘其口,但記者從權威渠道了解到,聯想旗下弘毅資本已經簽訂合同書,另外幾家審批流程較長,目前只進展到簽署意向書階段;除了小米、阿里巴巴、樂視等見諸報道的洽談者,騰訊也曾與集團有過親密接觸,可能躋身第二輪風投。而何力團隊本身也有所持股。
文人何力的新媒體考題
勞佳迪
在招聘啟事發布后的第二天,何力曾接受過資深媒體人羅昌平的自媒體采訪,用了“累死”兩個字形容當下的壓力。據記者了解,為了向“互聯網思維”致敬,他在醞釀這份聲勢浩大的招聘啟事時,都沒有選擇多年來在傳統媒體的“親隨”,而是求助一位在門戶網站有過長期報道和運營經驗的“外腦”之筆——這個微小舉動也透射出何力的壓力所在:盡快撕掉長期黏附在身上的紙媒標記。
從他以往的經歷看,早年確實從紙媒界獲得了相當認可,但新媒體的運營成績單仍是尷尬的空白。何力和胡舒立一樣系出《中華工商時報》,最為業界稱道的創業樣本還是2001年創辦《經濟觀察報》和2007年創刊《第一財經周刊》,一直被業內稱為“溫和改良派”。
2009年離開一財周刊后,何力似乎就開始了與自己的較勁。最讓他震動的經歷也許是2011年在創辦月刊《全球商業經典》時的戰績不佳:三年燒掉了4500萬元,卻讓大股東萬達集團敗走麥城,彼時的紙媒界已集體露出敗象。但在2013年轉戰武漢時,他依然難舍紙媒,經營漢網的同時還為《投資時報》招兵買馬,可惜應者寥寥。
追溯到《經濟觀察報》立刊的“理性、建設性”,《第一財經周刊》的“三不準定律”,以及公認人文氣息濃厚的《全球商業經典》,何力的文人情結都清晰可見,至于能否做出漂亮的新媒體成績單,還留待時間檢驗。
對于此時的何力來說,上海報業集團能夠給出的最好承諾,或許并不是知情人透露的1億元的啟動資金,而是足夠的運作自由。在這個傳統官方氣息濃厚的報業集團初次表態進軍新媒體時,就有四面八方的評論蜂擁而來,劍鋒直指體制的約束性。
不過,從已經掌握的信息看,上海報業集團對于何力團隊的運營介入并不深。“公司總部還是注冊在上海,但這次四地招聘都放在北京來操作。”一位了解籌備進展的知情人士對記者透露道。
“上海報業集團真正當自己牌來打的還是《東方早報》的新媒體項目,‘界面’項目只是由集團戰略發展部來推動,只謀求控股地位,而不牽扯具體運營,這對何力來說或許是一件好事。”不止一位受訪人士對記者表達了這層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