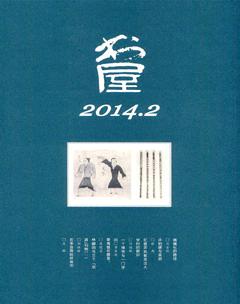《有竹居新評〈世說新語〉》篇評輯錄
杜預有《左傳》癖,余有《世說》癖,浸淫十余載,樂此不疲。前曾纂輯歷代評點,以《世說新語會評》之名付梓,其間幾度技癢,亦欲雪泥指爪,忝附諸賢驥尾,然自忖才學谫陋,唯恐有辱斯文,終于袖手。
辛亥年赴長沙,岳麓書社饒毅女史誠懇邀約,囑余對《世說》重加批評,體例風格,皆由自定。遂鼓起余勇,率爾操觚,雖隆冬時節,先父病榻之側,亦未嘗不忙里偷閑、時或點逗評騭也。歷時八月,乃告竣工。以今觀之,當年“會評”之書,似有意不乖體例,三緘其口,以作他日話頭耳。然是書雖有步武前賢之意,而終不敢以著述言之也。
是書撰成后,在師友間輾轉一年,其間得暇又補寫了三十六則篇評,篇幅遂又增加近兩萬字。今將篇評輯出,公諸同好,祈請博雅碩學、見道君子,不吝賜教云爾。
德行第一
○德行者,德性與品行之謂也。在內為德,在外為行。孔子教育弟子,以文、行、忠、信為四教,又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為四科;四科之中,德行居首,其余三科無不賴此以大以明。《論語·先進》皇侃疏引范寧語曰:“德行,謂百行之美也。”又《抱樸子·文行》:“德行者,本也;文章,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世說新語》三十六門,以“孔門四科”居首,頗有宗經、征圣之意,故有論者徑以“新論語”目之。然細讀《世說》可知,其旨歸趣向,又與《論語》大異其趣,而自有彼一時代之新精神與新風尚者在焉。蓋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變亂頻仍,儒學漸趨式微,老莊乘勢抬頭,又加佛教東漸,道教興起,諸種思潮交互影響,磨合激蕩,遂形成中華文明史上十分特出而別具光彩之玄學時代。故其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好尚,頗不同于周秦兩漢。即以《德行》一門而論,便有儒表道里、禮玄交織之況,如陳蕃以仕訪隱、叔度汪汪難測、管寧割席斷交、阮籍至慎玄遠、嵇康無喜慍之色、樂廣以名教中自有樂地、阮裕因人不借而焚車、謝安常自教兒、王恭作人無長物等,皆時代風氣作用于人物言行之證也。而《德行》門以仲舉禮賢事發端,亦頗可注意,蓋因名教與自然之角力,孔孟與老莊之消長,彼時已露端倪。換言之,若無東漢人物之風骨,則所謂魏晉風度實無從著落矣。此讀《世說》者不可不知也。
言語第二
○言語,善于辭令之謂也。《論語·先進》:“言語:宰我,子貢。”邢昺疏:“若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是知言語應對乃君子必備之能力,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然孔子于言語之巧又頗警惕,嘗謂:“辭,達而已矣。”“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仁者其言也讱。”甚至視伶牙俐齒者為“佞”,謂其“御人以口給,屢憎于人,……焉用佞?”蓋孔子以為言行之間,行重于言,故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從之。”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是知言語過巧而無實行,未可以言德行也。故夫子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此語正可為魏晉言語生態“傳神寫照”。又《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立德、立言既同屬不朽,不能立德者,則不妨立言。與前代重視言語之義、論辯之理者不同,魏晉乃是一重視語言之趣、應對之妙、修辭之美的時代,故《言語》門一百零八則,無不精彩雋永,如孔融“必當了了”之對、謝玄“芝蘭玉樹”之答,又如“孔雀楊梅”、“朱門蓬戶”之語,皆非泛泛所能道,讀之令人神往。蓋魏晉之際,雅尚清談,故錦心繡口,舌燦蓮花者所在多有,其發言遣詞,真如云興霞蔚,盡態極妍。明末曹臣撰有《舌華錄》,全書分為慧語、名語、豪語、狂語、傲語、冷語、諧語、謔語、清語、韻語、俊語、諷語、譏語、憤語、辯語、穎語、澆語、凄語等共十八門,實則《世說·言語》門之增廣也。然,似王祥輩“以德掩其言”者固有,而如王澄輩“終日妄語”者亦不乏其例,此可證夫子“聽其言而觀其行”之訓為不刊。瑕瑜良莠,取舍與奪,讀者明鑒。
政事第三
○此亦“孔門四科”之一。政事者,為政治國之事也。古語云:人道敏政,為政在人。孔子言政,主張“為政以德”,“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其反對殺伐,提倡垂范,嘗言:“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夫子亦提倡“無為而治”,嘗言:“無為而治者,其為舜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此正與老子“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為而無不為”之思想若合符節。夫漢末魏晉,天下方亂,群雄虎爭,為政之道亦從用重典、貴刑名向尚寬簡、務清靜漸次轉型。《政事》一門,首寫陳寔,次寫山濤,復次王承,至于王導、庾亮、桓溫、謝安諸宰輔,正可窺見此中消息。蓋正始以迄江左,玄學風行,為政者皆為清談人物,頗以老莊無為之道為旨歸,即豪杰剛猛如桓溫,亦“恥以威刑肅物”,故好為“察察之政”者如刁協、庾冰諸人,皆為時流所不屑,而王導之“憒憒之政”,反成時代之主流耳。又臨川王劉義慶編撰《世說》時,劉宋立國未久,皇室與藩王互相猜忌,為政不免嚴苛過當,故義慶以世路多艱,乃自求外鎮,終身不復跨馬,此正欲韜光養晦以求自保也。觀此篇二十六則故事,則義慶中年心事,宛然可見。夫仁政惠治,人人所慕,惟缺陷世界,不易可得也。
文學第四
○此“孔門四科”最后一科也。孔門之“文學”,蓋文獻、典章及學術之謂。《論語·公冶長》:“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同書《泰伯》:“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此兩處“文章”略與“文學”同義,亦指文獻、典章制度與學術,皆與今之所謂“純文學”者不同。文學漸次自學術中獨立,乃魏晉間事。曹丕《典論·論文》所謂“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之“文章”及陸機《文賦》所論之“文”,已與“孔門四科”之“文學”大不同,論者以魏晉為“文學自覺”之時代,良有以也。逮及劉宋文帝時,又立儒、玄、史、文四館,此“文學”正式獨立于學術之標志耳。《世說》正此一時代之產物,故《文學》一門,繼往開來,承前啟后,大可注意。夫《世說》各門所記,均按時序依次排列,一般先后漢,次三國,再次西晉,復次東晉,次序井然。獨《文學》一門為例外。該門前六十五則,照例以時為序,所記依次為經學、玄學、清談及佛學,儼然一部“學術流變史”。而至第六十六則,忽又自曹植“七步詩”寫起,直至篇末近四十則皆為詩、賦、文、筆,屬今之所謂“純文學”之類。此一體例之“突變”,明人王世懋謂之“一目中復分兩目”,此正時代思潮之顯影,文學獨立之折射也。至于此門中人物故事,無不斐然可觀,前半部好似“漢晉學案”,后半部則如“魏晉詩話”,欲窺中古學術文化之嬗變,領略彼時人物之文采風流,不可不讀,亦不可不知也。endprint
方正第五
○方正者,端方正直之謂也。《管子·形勢解》云:“人主身行方正……行發于身而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又《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可知方正實為德行之具體顯現,故而可以為楷則示范也。漢代選舉官吏,遂以方正為一科,與賢良、文學、孝廉、茂才等同受擢拔,成為品鑒人物之一大科目。《世說》乃一“品人”之書,以《方正》綴于“孔門四科”后,足見其在人物品藻風氣中深具影響。然通觀此篇,可知魏晉之際,“方正”之內涵漸趨復雜,既有彰顯儒家清操正節之舊意涵(如夏侯玄之拒鐘會,陳泰之諫誅賈充),又有門閥制度下士族自矜門第之新風氣(如王濛、劉惔不食小人所贈酒,王修齡不受陶范所饋米)。故方正之為方正,已非僅指群體公認之內在品性,而更擴展至于人己之間互相對待時之自我確認。此正魏晉士人標舉自我、張揚個性之具體表現,所謂“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故其人其事雖或有可商,其性其情則頗有可觀,讀者其詳之!
雅量第六
○雅量,即恢弘之氣度與過人之器量,乃魏晉名士心向神往之理想人格與生命境界。如謂方正乃處理人己關系之品格,雅量則為處理物我關系乃至天人關系之高標。簡言之,雅量乃是一從容恒定之人格狀態,即不以外在環境之變故,改變內在人格之穩定性。所謂臨危不亂,處變不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又所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也。以一己之“不變”,以應外物之“萬變”,雅量之為人格,猶置千鈞之重于鴻毛之輕,又如“高高山上立,深深海底行”,其壯其美,有可意會而不可言傳者焉。觀《雅量》一門所記,皆魏晉名士面臨各種變故時之卓絕表現,或白描直敘,或對比烘托,無不驚心動魄,溢彩流光。如嵇康臨刑東市而神色不變,索琴而奏《廣陵散》,人格何其偉岸!謝安大敵當前,閑敲棋子,氣定神閑,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風度又是何等瀟灑!至如羲之東床坦腹,以無待為達;顧和覓虱如故,以不求為高。凡此種種,正雅量人格嫵媚迷人處。是方正、雅量之間,方正乃代表自己與人對話,雅量則代表人類與上帝對話;故《雅量》雖處《方正》后,價值反在其上也。
夙惠第十二
○夙惠,即早慧。古時最重家學與家教,故神童天才層出不窮。《禮記·大學》云:“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又《顏氏家訓·勉學篇》:“士大夫之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向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為凡人。”同書《教子篇》云:“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可知古之家學家教,實兒童稚子啟蒙之始基,成才之坦途也。此門所記早慧兒童故事七則,無不出于家學淵源之簪纓世家、書香門第。如陳元方兄弟竊聽父輩論議,蒸飯作糜;司馬紹日近長安之對,問同答異;韓康伯捉熨斗而知冷暖,旨在慰母;司馬曜以晝動夜靜言養生,不減乃父:無不娓娓可聽,玲瓏可喜。噫!何今日再無此夙惠神童也哉?竊謂究而論之,其因有三:家學崩解,坐失幼教之良機,一也;父母無識,專以快樂為能事,放棄教育之責任,二也;學校為官方所壟斷,經典教育中斷有年,教材低幼,難收啟蒙祛蔽之效,三也。前引《顏氏家訓·勉學篇》云:“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后,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又古語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為人父母而不早施教者,真“賊夫人之子”也!
豪爽第十三
○豪爽者,豪邁俊爽之謂也。《世說》之門類設定,常兩兩相對,彼此呼應,如《識鑒》之于《賞譽》、《企羨》之于《品藻》、《捷悟》之于《夙惠》、《術解》之于《巧藝》、《任誕》之于《簡傲》、《規箴》之于《自新》、《排調》之于《輕詆》、《紕漏》之于《尤悔》、《假譎》之于《饞險》、《儉嗇》之于《汰侈》、《寵禮》之于《黜免》、《忿狷》之于《惑溺》,皆其例也。蓋編者以為,人之才性品類,或如陰陽之交錯,或如形影之相隨,常有粗看混沌、細察可辨者在焉。即如《豪爽》一門,實可與《雅量》并觀,其顯隱張弛,外放內斂,皆人格類型之兩極展現也。古語云:“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若謂《雅量》所關乃光風霽月之名士風流,則《豪爽》所標實為排山倒海之英雄本色。此門所記,如王敦、祖逖、桓溫、桓玄之流,多為亂世豪雄,其情其性或失之粗鄙,其言其行則率真疏放,一任天然。唯剝落道德之成見,方得人性之妙賞、審美之愉悅,《大學》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其斯之謂歟!
容止第十四
○容止,容儀舉止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有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做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孝經·圣治章》亦云:“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唐玄宗注:“容止,威儀也。”又《禮記·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兇災。”鄭玄注:“容止,猶動靜。”蓋容止者,君子所必備之禮容威儀也。漢末以迄魏晉,人物品藻之風大行其道,容止之內涵遂由尚禮容、重威儀向尚形貌、重風神轉變,而形神之間,又以神為主,故有“神超形越”之謂也。《容止》一門單獨立目,正欲彰顯彼時風氣之盛,人物之美。而其敘事寫人,又多用對比烘托法(如夏侯玄之于毛曾、潘岳之于左思)、自然象喻法(如嵇康孤松玉山、嵇紹鶴立雞群、王恭濯如春柳)、夸張傳奇法(如衛玠因美竟被“看殺”、庾亮因美而得“不殺”),要在出奇制勝,令人過目難忘耳。俗語云:愛美之心,人皆有之。讀此篇若不齒頰生香、流連忘倦者,不足與言美之為美也矣!
惑溺第三十五
○惑溺,迷惑陷溺之意。《論語·顏淵》:“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告子曰:“食色,性也。”又《禮記·禮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陷溺于情欲而不能自拔,是為惑溺。故孟子云:“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魏晉之際,風云突變,唯才是舉而輕德,風俗澆薄而重色。故干寶《晉紀·總論》云:“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于婢仆,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于古,修貞順于今,輔佐君子者哉?”《世說·惑溺》一門,記載魏晉七則情愛故事,或直或婉,或褒或貶,皆有可觀者。如荀粲思妻而殞,韓壽竊玉偷香,王戎夫妻私語,歷來膾炙人口,誠為筆記佳品也。
仇隙第三十六
○仇隙,猶言仇恨、嫌隙。古有復仇之禮。《禮記·曲禮上》云:“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友之仇,不同國。”又《禮記·檀弓下》:“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席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后。”此蓋言復仇亦須循禮制、有差等也。魏晉好奇任俠之風盛行,快意恩仇,睚眥必報,而況殺父奪兄之仇?故《世說·仇隙》一門,乃遍布陷阱機關、刀光劍影,可謂驚心動魄,險象環生。觀孫秀懷恨潘岳,終于借刀殺人,知小人報仇,亦可期以十年。司馬無忌本與王胡之為友,既明宿仇,仍可抽刀于轉瞬,必欲誅之而后快;雖曰“血氣方剛,戒之在斗”,然此種快人,亦可謂千古如生也。又如《晉書·桓溫傳》載,溫父桓彝為韓晃所害,涇縣令江播亦預此謀。時溫年僅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仇。值江播病卒,其子江彪兄弟三人守喪,溫乃袖內藏兵,喬裝以入,竟手刃江彪于喪廬,追殺二弟于歧路。溫亦由此而為時人所稱。俗語云:冤冤相報何時了。又有云:“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夫人性之中,本有此一往戾氣,如巖漿之蘊深海,一朝破冰而出,又豈可倉促收拾?故視仇隙之局促,乃知雅量之為高。此門之設,不惟標志吾國文學復仇主題之獨立,亦以竣成全書謀篇布局之藍圖,彰顯作者體察人性之深衷也。
(劉強:《有竹居新評〈世說新語〉》,岳麓書社2013年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