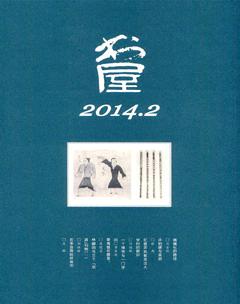記憶·思考·審美
孫德喜
2007年夏天,在上海同濟大學的丁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結識了年過八旬的來自北京的毛憲文先生。會后他不顧酷暑炎熱來到揚州游玩,我一路陪同,為他的精神所感動,并且與他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幾天前,毛先生給我寄來了他新近出版的三十七萬字的巨著《甲子集粹》(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我為毛先生在耄耋之年出版著作再次深深感動,于是花了幾天時間通讀了這部厚實的著作,覺得這是他自1952年大學畢業以來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的一個總結,體現了他在這一個甲子年里的記憶、思考以及對藝術美的審視。
毛憲文先生,蒙古族人,195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至今已過一個甲子。六十年來,毛憲文先生勤奮致力于文學創作和思考,寫下了為數可觀的文學評論文章與文學作品,現在他將這些結集出版。在他的這部著作中,首先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歷史記憶。毛憲文先生出生于1926年,不僅見證了六十多年來共和國的歷史,經歷了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時代的風風雨雨,而且由于他長期在魯迅文學院工作,接觸到許多著名作家,因而,他的歷史記憶包含著極其豐富的信息,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他在這部著作中對丁玲、鄧剛、樂黛云、劉紹棠、馬烽、黃秋耘、廢名、烏爾熱圖、李發模、趙本夫、胡正等數十位作家作了不同程度的記述,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對丁玲的回憶。我們對丁玲的坎坷人生與創作都有比較詳細的了解,但是對她創辦文學研究所培養文學新人方面則了解較少。毛憲文先生在書中詳細敘述了丁玲在輔導教育青年作家方面的具體事情,從而讓我們了解到作為文學教育家的丁玲。這樣,丁玲在讀者心目中的印象更加全面、具體和豐滿。與此同時,毛憲文先生還記述了丁玲與新加坡作家的交往以及她對新加坡華人文學的深刻影響,為中新文學交流史、比較史提供了非常具體而珍貴的史料。至于其他作家大大小小的逸事不僅讓我們了解到生活中的作家,而且對于研究這些作家的創作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在《甲子集粹》中,毛憲文先生還寫了長篇文章回顧自己從“九·一八”到“八·一五”的人生經歷,從個人視角敘述了中華民族的抗戰歷史。毛憲文的這些回顧性和懷念性的文章雖然并不系統,比較零碎,然而無疑是最具體鮮活的歷史呈現。
毛憲文先生既是一個作家又是一個學者,他不僅研究作家作品,而且善于對各種現象進行深入的思考,進而得出自己的結論。高洪波在《甲子集粹》的序中借用陳建功的話說,毛憲文先生的書中“不乏獨到見解”。而這“獨到見解”顯然是他獨立思考的結晶。從毛憲文的思考來看,他著力于從現實生活經驗出發,根據自己的人生經歷和體驗,具體地分析問題,進而提出自己的看法。這就使他有別于一些人玩弄概念,在空洞的理論間鉆來鉆去。所以,他由思考提出的意見還是給人以親切感,很容易讓人接受。在談到青年學者趙煥亭論丁玲的問題時,毛憲文先生覺得趙煥亭在研究中“沒有尖銳地毫不留情地指出:所謂丁玲晚年喪失創作個性特色的妄說,其目的是希望丁玲這樣的大作家不應該這樣去寫,而應該違心地迎合某些人的趣味”。毛憲文先生的這個看法雖然不一定為人們認可,卻也符合丁玲當時的心態。
在《甲子集粹》中,有相當一部分文章是對古今文學作品的評析。毛憲文先生的評析都很短小精悍,要言不煩,一語中的,揭示出古今文學名篇的思想內涵、文化意蘊以及藝術特色。毛憲文先生寫這些評析文章很可能是他在文學研究所(魯迅文學院)和中學任教時的講稿。而他的這些文稿寫得非常樸實,就同他的為人一樣,厚道而中肯。因而,他將自己的人格理想和人生追求融入到文學名篇的審美當中來,從而使他的審美別具一番風味。
毛憲文先生的《甲子集粹》讓我們看到與共和國一道成長的作家的信念和追求,個性和風采。從他的人生來看,他既受到極左政治的迫害,感慨于國家、民族以及個人的不幸,更看到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當他以真情真意投入寫作時,我們看到了他的獨特姿態。而且,我們還注意到,毛憲文的寫作顯然不同于那些大作家的自我表現,主要是他作為鋪路石的寫作,他無論是回憶歷史,還是思考問題,抑或是對于文學作品的審美評論,都是為了啟發青年,提攜后學,甘為他人作嫁衣,確實令我們敬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