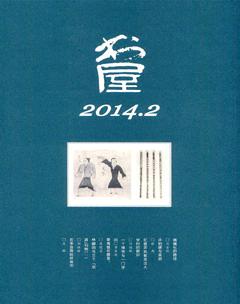林徽因與三個“京派”刊物(一)
劉淑玲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京派”文學的鼎盛時期,京派最重要的文學刊物大都是在這一時期創刊。林徽因的文學活動也始終與“京派”文學相伴。正如蕭乾所說:“她又寫、又編、又評,我甚至覺得她是京派的靈魂。”
“京派”有三個重要的文學刊物:《大公報》文藝副刊、《學文》和《文學雜志》。這三個刊物的刊頭與封面都是由林徽因設計,風格清新脫俗,古樸典雅,標明了“京派”作家的文學理想,留下了林徽因作為建筑師的風采,也成為不可復制的藝術樣板。
《大公報》文藝副刊
《大公報》文藝副刊創刊于1933年,同年8月沈從文從上海回到北平,9月就開始主編這個副刊。正如蕭乾所說,沈從文的北歸以及《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創刊,為“京派”文學劃出了一個歷史的坐標,它標志著“京派”作家群開始形成,并且有了自己最重要的刊物。此時,身在北平的林徽因很快成為“京派”文學的中心人物。在這個副刊的編輯過程中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勞動,也是這個刊物的主心骨。
《大公報》文藝副刊沒有發刊詞,創刊號上發表了楊振聲的《乞雨》和林徽因的《惟其是脆嫩》,這兩篇文章實際上是代發刊詞,表明了文藝副刊的辦刊宗旨,它們從不同的角度表達了一個共同目標:一是要打破北方文壇的沉寂,喚醒“五四”文學的生機和活力;二是要保持文學的獨立姿態,使文學寫作既不受商人的影響也不被政治左右,而是以“形形色色的人物、悲劇喜劇般的人生作題”(林徽因《惟其是脆嫩》)。
青年作家蕭乾就是在《大公報》發表了他的小說處女作《蠶》,受到林徽因的關注,她給主編沈從文寫信表達了自己的欣喜之情,而后,沈從文和林徽因一直關注著蕭乾的創作,得到鞭策的蕭乾在創作上大為長進,連續在《大公報》上發表了多篇小說。1935年,蕭乾在燕京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后,沈從文馬上把他介紹進天津《大公報》館作文學編輯。蕭乾回憶說:“在我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期間,徽因一直是我的啦啦隊。我每次由天津到北平舉行約稿懇談茶會,她總是不落空,而且席間必有一番宏論。她熱烈支持我搞的《大公報·文藝副刊》獎金,還從已刊的作品中選編出一本《大公報小說選》。”1935年7月4日,蕭乾又接編《大公報》最有影響的一個通俗消閑副刊《小公園》,在沈從文、林徽因等京派作家的幫助之下,蕭乾對《小公園》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造。
在《小公園》的改造中,林徽因起了重要的作用。蕭乾捧出了《小公園》的改造藍圖之后,她和梁思成一起為它設計了新的刊頭。他們冒著酷暑趕制出了一幅“壯麗典雅”的刊頭畫,林徽因為此專門給蕭乾寫信說明創作過程和圖案的寓意:“現在圖案是畫好了,十之七八是思成的手筆,在選材及布局上,我們輪流草稿討論。說來慚愧,小小一張東西我們竟然作了三天才算成功。好在趣味還好,并且是漢刻純粹中國創造藝術的最高造詣,用來對創作前途有點吉利。”他們的好友、《大公報·藝術周刊》的主編、著名畫家司徒喬也放下了正在進行的巨幅油畫創作,特為《小公園》設計了另外一個湖光塔影的刊頭畫,清新素雅,表達了畫家對這個小刊物“特別的寵愛”。
蕭乾為此特致讀者:“在這里,我們得向兩位藝術友人道謝,因為大熱的天,他們曾費許多心思為這小刊物計劃‘報頭,使它能有一塊漂亮的犄角。……吉利不吉利可全在大家的努力了。讓我們在這精彩的‘犄角下面鋪起精彩的文章,切莫使這些寵愛變成為錯愛。”由此可見,大藝術家畫“小刊頭”,不止是出于對這個小小副刊的關愛,而是表明了他們對文學新生力量的期待。
此后,《小公園》輪流用這兩幅圖案作為報頭,內容也大為改觀,告別了“消閑”和“散淡”的時代,走上了純文學之路。新的《小公園》誕生后,新文學作家也陸續登場,如沈從文、知堂、曹葆華、孫毓棠、劉西渭、陳夢家、何其芳、李廣田、靳以、南星、蘆焚、祖春、道靜、楊剛、林庚、常風、麗尼、方敬、畢奐午等人,而后它又并入《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成為“京派”文學最重要的陣地,展示了京派作家群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學活動,反映了他們的文學觀念和創作風格,也培養了大批青年作家,擴大了“京派”文學的影響。
《學文》
1934年5月1日,《學文》雜志創刊于清華大學,主編是時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葉公超。后來葉公超到國外休假,自第四期起由他的同事聞一多、余上沅和吳世昌共同編輯。《學文》是徐志摩去世三年、“新月派”成員已經流散、《新月》也停刊之后,北平文壇上的作家和知識分子為自己營造的一方文學天地。《學文》自籌資金,葉公超晚年回憶說:“當初一起辦《新月》的一伙朋友,如胡適、徐志摩、饒夢侃、聞一多等人,由于《新月》雜志和新月書店因種種的原因已告停辦,彼此都覺得非常可惜;1933年底,大伙在胡適家聚會聊天,談到在《新月》時期合作無間的朋友,為什么不能繼續同心協力創辦一份新雜志的問題……討論到最后,達成一個協議,由大家湊錢,視將來湊到的錢多少做決定。能出多少期就出多少期。當時一起辦《新月》的一群朋友,都還很年輕,寫作和辦雜志,談不上有任何政治作用;但是,《學文》的創刊,可以說是繼《新月》之后,代表了我們對文藝的主張和希望。”(葉公超《我與〈學文〉》)。由此可見,《學文》的創刊與《新月》已逝的催生,但是畢竟時光流轉,《學文》的面貌與《新月》又大有不同,成為“京派”文人崛起于文壇并走向鼎盛時期的見證。
《學文》的封面由林徽因設計,素雅清新,刊名下方的裝飾圖取自漢代碑刻圖案。人物、鳥獸、魚和植物古樸排列,線條簡潔明朗,給人留下無限的審美空間,既有濃郁的民族特征又有清新的現代精神。
季羨林當時還是清華大學外文系的學生,他有幸在《學文》創刊號上發表了散文《年》,刊物出版之后,葉公超專門送給他三本《學文》,捧讀還在油墨飄香的雜志,他第一眼就被這個與眾不同的封面吸引住了,并在他的《清華園日記》中留存了清晰的記憶:“《學文》封面清素,里面的印刷和文章也清素淡雅,總起來是一個清素的印象,我非常滿意,在這種大吵大鬧的國內的刊物,《學文》仿佛雞群之鶴,有一種清高的氣概。”卞之琳是“京派”作家的重要成員,《學文》創刊號上也有他應主編葉公超之約,翻譯詩人艾略特的論文《傳統與個人才能》。直到晚年,卞之琳憶起林徽因,還不忘她所設計的這個封面:“我在一九三四年親見過她(林徽音)為刊物所作的封面設計,繪制的裝飾圖案就富有建筑美,不離她的專業營造學(建筑學)本色。”endprint
《學文》雜志的確不同凡響。詩歌、小說、散文、文學理論都為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壇貢獻了不可多得的藝術精品,展現出“京派”作家文化理想中素樸雅潔的古典氣質與藝術創作上不斷探索的現代精神。林徽因本人的文學成就也在《學文》雜志中展現的淋漓盡致。她發表在創刊號上的詩歌《你是人間四月天》和小說《九十九度中》就大放異彩,引起了文壇的強烈關注。《你是人間四月天》與她之前的詩歌相比,突破了旋律之美,變換了詩節與韻式,更趨向于自由詩體,展現了新詩更豐富的美感,呈現出現代主義詩風。小說《九十九度中》發表后更是沖擊了當時的文壇,有大學教授竟然宣稱讀不明白。這篇小說借鑒現代派的表現技巧,以橫截面的手法,選擇北京炎熱的夏天,將看似互不往來的不同社會階層、不同的生活場景連綴在一起,“在我們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熱情奔放的時代,”作家以平靜的敘述控制住了“熱情”,用最快利的明凈的鏡頭,攝來人生的一個斷片,展現出三十年代北京城的都市生活的多個層面。“京派”文學最重要的批評家李健吾當時就指出:“在我們過去短篇小說的制作中,盡有氣質更偉大的,材料更事實的,然而卻只有這樣一篇,最富有現代性。”據說朱自清在小說發表之前,看過手稿之后就曾斷言:“確系佳作,其法新也。”當時的清華學生季羨林記錄他的閱讀體驗時,也用了詩一般的語言感嘆:“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寫得不壞,另有一種風格,文字像春天的落花。”(季羨林《清華園日記》)
《文學雜志》
1937年5月1日,“京派”又一個刊物《文學雜志》創刊,朱光潛主編,編輯部設在朱光潛的寓所——北平后門內慈慧殿三號,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林徽因是編委之一,其余還有胡適、楊振聲、沈從文、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馮至、凌叔華、常風九人,都是北平文壇的重要作家。《文學雜志》也成為“京派”文學的重鎮。
林徽因也為《文學雜志》設計了封面。《文學雜志》與《學文》的封面異曲同工,保留了一貫素潔雅致風格。沒有過多裝飾,“文學雜志”四字橫排位于封面上方,其余是大面積留白,畫面中心位置醒目地落有“雙魚抱筆”的裝飾圖案,整個封面由邊框圍起,雙魚一藍一紅,每期邊框顏色也藍紅交替變換,色彩和諧,圖案典雅。
“雙魚”在東西方都是吉祥的符號。據說在藏傳佛教中,雙魚有多種寓意,有說代表佛的雙目,象征佛眼慈視眾生,有智慧之意;又說魚行水中,暢通無阻,佛以其暗示超脫世間,自由豁達的修行者;又有說象征著復蘇、永生、再生等意。林徽因以“雙魚抱筆”作為《文學雜志》的裝飾圖案也會寄托了她對這份雜志的祝愿與期許。
朱光潛在《文學雜志》的發刊詞《我對于本刊的希望》表明了編者心目中“理想的文學刊物”:“一種寬大自由而嚴肅的文藝刊物對于現代中國新文藝運動應該負什么樣的使命呢?它應該認清時代的弊病和需要,盡一部分糾正和向導的責任;它應該集合全國作家作分途探險的工作,使人人在自由發展個性之中,仍意識到彼此都望著開發新文藝一個公同目標;它應該時常回顧到已占有的領域,給以冷靜嚴正的估價,看成功何在,失敗何在,作前進努力的借鑒;同時,它應該是新風氣的傳播者,在讀者群眾中養成愛好純正文藝的趣味與熱誠。它不僅是一種選本,不僅是回顧的而同時向前望的,應該維持長久生命,與時代同生展;它也不僅是一種“文藝情報”,應該在陳腐枯燥的經院習氣與油滑膚淺的新聞習氣之中,開一個清新而嚴肅的境界,替經院派與新聞派作一種康健的調劑。”所以希望這個刊物“不妨讓許多不同的學派思想同時在醞釀、騷動、生發、甚至沖突斗爭”及“對于文化思想運動的基本態度用八個字概括起來,就是:自由生發,自由討論”,由此引來文壇盛景。
作為“京派”的靈魂與《文學雜志》的編委,林徽因的“雙魚抱筆”應該是為這種“自由生發,自由討論”的編輯理想所作的形象解說。
林徽因在《文學雜志》發表了她一生唯一的劇作《梅真和他們》。朱光潛在《編輯后記》中熱情地稱贊這部劇作的價值:“現在話劇中仍留有不少的‘文明戲的惡趣,……林徽因女士的輕描淡寫是悶熱天氣中的一劑清涼散”。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她是在“水一般的流動中”展開戲劇人生,演繹悲歡離合,讓時間之水波光鱗紋,“在兩點鐘時間內能把人的興趣引到一個Make一believe的世界里去愛憎喜怒一些人物”。《梅真同他們》與《文學雜志》一樣,被日本人的侵略炮火中斷了。1937年8月l日《文學雜志》出版第一卷第四期后,因北平淪陷而被迫停刊。林徽因的四幕劇《梅真同他們》也就只發表了三幕,成為永遠的未完成之作。
1946年冬,抗戰勝利之后,朱光潛回到北京大學,經過半年的籌備,1947年6月1日《文學雜志》復刊,朱光潛發表《復刊卷頭語》,表明重振“京派”文學的信心。復刊后的《文學雜志》仍然沿用林徽因設計的封面,并且在抗戰后的北平文壇重新引起了很大反響,朱光潛回憶當時每期行銷都在兩萬份以上。但是1948年11月,《文學雜志》還是在出版第三卷第六期后徹底停刊,這份雜志在抗戰前后兩個時期共出版了三卷二十二期。
林徽因用勤奮的一生展示了一個藝術家多方面的才華。她的摯友、美國人費慰梅曾經回憶說:“在她身上有著藝術家的全部氣質,她能夠以其精細的洞察力為任何一門藝術留下自己的痕跡。”(費慰梅在《回憶林徽因》)的確,她把作家的才情和敏銳灌注到建筑師生涯中,展示了卓然獨立的成就;她也把建筑師、美術家的眼睛用在捕捉文學的靈感之中,建立了一個開闊、清新的文學世界。1955年,林徽因去世后,北京香山的墓地上寫著“建筑師林徽因之墓”。她是中國第一代建筑學家,清華大學建筑系一級教授;她會演戲,曾與泰戈爾同臺,又是著名的舞臺美術設計師、工藝美術家。上世紀三十年代就曾經為曹禺劇作的演出設計過舞臺布景。建國之后,為景泰藍改造投入大量心血。她認為傳統的色彩和紋樣過于呆板,暗淡和繁瑣,應該使景泰藍設計保持鮮明的民族風格同時應當更具現代化,又更流暢的線條,豐滿、和諧的色彩。天安門紀念碑前,那鐫刻在花崗石碑座上的裝飾花紋和碑心正下方的花圈浮雕也出自她的慧心,而她最輝煌的成就是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她又是作家,在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文學批評、翻譯等領域皆成就斐然。為“京派”刊物設計刊頭和封面,只是林徽因藝術生涯中的一朵浪花,但是卻鮮活地展示了這位才女不平凡的文學旅程。“京派”文學已成歷史,它留下來的文學成績仍然熠熠閃光。這三份“京派”雜志已經成為歷史的坐標,留存下這份永恒的業績。林徽因和她的這些刊頭與封面設計,也就成為了一份讓后人無限追懷的文化檔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