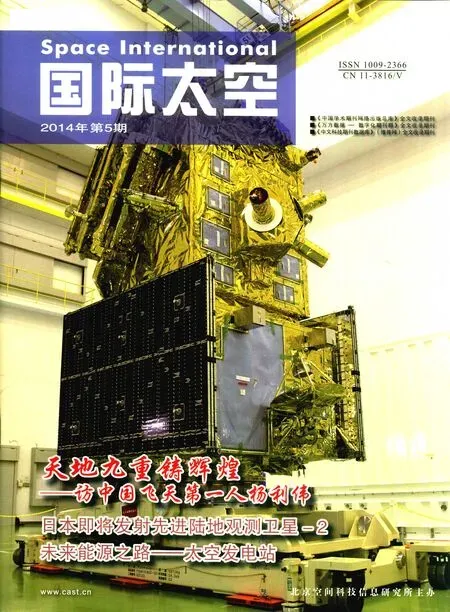新航天基本法—日本產業振興的源動力
新航天基本法—日本產業振興的源動力

王存恩:研究員,教授,日本航天政策、產業化、技術與應用等領域的資深研究專家。
2014年,恰逢日本航天60年。在這60年里,日本航天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莫過于頒布新航天基本法(以下簡稱新航天法)。接著,日本航天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開發體制做了重大調整,開發重點發生了轉移;提出了加速航天產業振興和驅動國家產業振興的總體目標。新航天法正成為驅動日本產業振興的源動力。
日本航天起步于1954年,當時正處于戰后恢復期,國家顧及不到航天,沒有資金投入,以糸川英夫為代表的具有遠見卓識的幾位科學家自籌資金,用極其簡陋的設備,研制并成功地發射了探空火箭,揭開了日本航天開發的序幕。
日本政府真正關心并領導航天開發可追溯到1969年。同年5月,日本政府頒布了名為“航天開發僅限于和平利用”的航天基本法,同時確定了科學技術廳和文部省分別負責應用技術和科學衛星及其運載工具的研發。
從1954年到2008年5月頒布新航天法,日本航天開發取得了顯著成績:搶先中國70天發射了首顆人造地球衛星“大隅”,使其成為繼蘇、美、法之后世界上第4個用本國火箭發射自己研制衛星的國家。日本憑借其雄厚的工業基礎,以及先進的機械制造、半導體加工、光學儀器生產,在推進機光電一體化進程中,不斷采用新技術、新方法、新理念、新工藝,不斷提高其設計和開發水平,使之成為擁有“領先于國際水平的各類高復雜度的航天硬件和組件的國家”。其研制的許多航天產品,如固體放大器、大型鏡面天線、合成孔徑雷達、微波輻射計、微波放電式離子發動機、64bit星載計算機等在國際航天市場上頗受青睞。國際權威調查機構—富創(Futron)公司的調查結果認為:“按人均航天能力計算,日本擁有世界上最能干、最優秀的航天勞動力”;“用較少的航天勞動力就能實現生產力最優化,具有較強的專業技術優勢”。美、歐,以及日美、日歐等聯合研制的航天器大都采用了日本開發的器件,或由日本提供核心有效載荷儀器。Futron公司還指出:“日本已成為為國際航天市場提供高復雜性的航天硬件和組件的主要國家之一。”
50多年來,日本完成了奠定基礎(1954-1970年)、培養獨立自主技術(1970-1980年)、確立基礎技術(1980-1999年)和奠定產業化基礎(1999-2010年)4個階段的任務,正步入“參與國際競爭”新階段。2009年,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的一份調研報告—《中國的科學技術能力》認為:日本的航天競爭力指數(SCI)在美、俄、歐洲之后,排在第4位。當時Futron公司的調查結果也與之基本相同。
但必須指出,在新航天法頒布前相當長時間內,日本不僅在政治上追隨于美國,在航天領域也過分地依賴美國。在美國“抵消貿易逆差必須訂購美國衛星”的強大壓力下,日本耗費大量外匯購買了美國30多顆通信衛星,這不僅嚴重影響了日本這一技術的發展,也推遲了其航天產業化進程。由于日本由兩個省廳長期分管航天,所以缺乏統一的領導和統籌規劃,以及片面強調研發,忽視應用,也影響了日本航天的全方位發展,推遲了產業化進程。日本右翼勢力在否認其侵略歷史的同時,以“朝鮮導彈威脅”等為借口,發展軍事航天。自民黨宇宙開發委員會委員長小野晉也甚至曾鼓吹“日本要與美國的航天開發戰略相呼應,不僅要擁有高性能的偵察衛星,還要有監視彈道導彈的早期預警衛星”,這道出了日本極右勢力處心積慮發展軍事航天和背棄航天開發“僅限于和平利用”承諾的內心世界。基于此,2008年5月,日本國會批準并頒布了新航天法,日本的航天開發政策開始發生以下重大變化:
1)成立以內閣總理大臣任宇宙開發戰略本部部長,進一步強化了內閣對航天的領導;
2)由“以研發為主導”轉變為“以應用需求為主導”,提出了“加快航天產業化”和通過振興航天產業帶動國家“產業振興”的口號;
3)從首部航天法中刪除了“航天開發僅限于和平利用”,即“非軍事”之承諾,目的是為航天軍事應用鋪平道路。
如Futron公司的調查報告中指出的那樣:“新航天法為日本航天活動帶來新生機”,“標志著日本航天計劃將發生重大的實質性變革,為持續提高其航天競爭力奠定了基礎,也成為日本產業振興的源動力”,“從此日本可以名正言順地將航天活動用于國防目的,標志著日本軍事航天政策的戰略轉變,也將對其競爭力產生重要影響”。
2009年6月,日本公布了新世紀的首部“航天基本計劃”并預言:“到21世紀中葉,航天將像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電子、汽車和計算機產業一樣,成為引領國際經濟和產業發展的新興產業”;提出要“通過執行航天基本計劃,提高航天開發能力和應用水平,增強航天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2009年剛從自民黨手中接管政權的民主黨也多次強調:“航天產業是確保日本獲得再生的‘前沿產業’”,要“通過執行航天基本計劃提高航天開發能力和應用水平,增強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重振國家經濟,并在亞太乃至整個世界范圍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不過,此間中國航天開發能力迅速提升,發射次數增多,執行任務能力增強。2010年起,中國航天競爭力指數超過日本。Futron公司2010年公布的調查排序也發生了變化:中國排到了第4位,日本則降至第5位。
不過,正如Futron公司在其調查報告中強調的那樣:日本是“近幾年唯一一個在各項競爭力指數都全面增加的國家”,日本“航天工業改革已經并將繼續滲透到政府和各工業領域”,“政府、人力資本和工業三大方面的競爭力都在提高”。的確,日本的航天開發與應用,以及產業化和拓展國際市場能力都取得了某些突破性的進展:2011年5月,三菱電機公司用DS-2000衛星平臺為新加坡和中國臺灣聯合研制的通信衛星中新-2(ST-2)交付并成功發射;與土耳其國營通信衛星公司簽訂了用DS-2000衛星平臺研制的2顆通信衛星—土耳其衛星-4A、4B[(Turksat-4A、4B),土耳其衛星-4A于2014年2月成功發射并交付];日本電氣公司與越南簽訂了用“具備新系統結構的先進觀測衛星”(ASNARO)衛星平臺研制2顆小型遙感衛星;三菱重工業公司已用H-2A火箭發射了韓國多用途衛星-3(KOMPSAT-3)。為保持這種良好勢頭,提升航天產業化和進入國際市場的能力,即便是在大地震、誘發海嘯、導致核泄漏以及民眾支持率降至最低點的危難時刻,民主黨野田內閣依然竭盡全力去完善航天政策,調整開發體制,其中包括:
1)修改了“內閣設置法”,進一步強化了內閣對航天的決策和指揮權;
2)修改了“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設置法”,刪除了“航天開發僅限于和平利用”,目的是使“和平利用”從日本的法典中徹底銷聲匿跡;
3)撤消了隸屬于文部科學省的宇宙開發委員會,成立了隸屬于內閣府的宇宙開發政策委員會;
4)成立隸屬于內閣府的國家航天戰略司令部—宇宙戰略室,既負責制定與航天有關的基本政策,也負責對與航天開發和應用有關事物的綜合調整等。
2012年,自民黨重掌政權,但仍繼續執行已頒布的新航天法,制定各項航天政策和確定開發體制。為標榜自民黨的功績,安倍甚至否定民眾和輿論界公認的應以“2011年為日本航天產業化元年”,而把2013年定為“日本航天產業化元年”,提出“提升航天開發能力和應用水平,盡快振興航天產業”,鼓勵企業“提高設計水平和產品開發能力,提高產品市場競爭力”和“提高企業知名度,提升日本的國際地位”。為推進這一目標的落實,2013年1月,安倍內閣又重新公布了新航天基本計劃,明確了以下幾點:
1)一個基本目標—“加速推進航天產業化”;
2)兩項基本方針—“擴大應用”和“確保自主性”;
3)三大重點項目—“安全保障和防災”、“振興產業”和“航天科學等新領域”;
4)四項基礎設施—“定位衛星”、“遙感衛星”、“通信廣播衛星”和“空間運輸系統”;
5)五項基本措施—①夯實產業基礎。“官民協力,面向國外推出一攬子服務式空間基礎設施”和“加快研發與推進應用”的新策略。②開展情報收集和調查分析。強化航天政策委員會和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的功能。③推進航天外交。“腳踏實地地推進多國間合作”、“強化雙邊合作”。④明確安全保障政策。靈活、有效地應用航天成果,實現“掌握情報”、“情報共享”和“統一指揮、管理”。⑤認真考慮環境問題。“開展國際對話”、“執行太空態勢感知體系”和“開發清除空間碎片技術”。
日本正從國家層面開始重視并全力支持航天開發,推進應用和產業化,以加快產業振興。自2013財年起,日本扭轉了開發經費連續4年遞減的局面,航天開發預算較2012財年增加了17.7%,而2014年又較2013財年初(尚不包括可能追加部分)增加了13.9%。
而在預算中,日本航天防衛經費增加比率最高:2013和2014財年分別較2012財年增加144.7%和110.23%。這尚不包括追加部分,以及與民營企業簽訂合同支持開發和完善X頻段專用國防通信衛星通信網絡系統、以內閣其他渠道支持早期預警衛星及其核心部件(雙頻段紅外遙感器)等的費用。
到2014年2月底,日本共發射航天器(含貨運飛船)194個。其中,國家投資研制120個,商業衛星40顆,民間機構開發的衛星34顆;為國外研制并交付衛星3顆,尚有3顆在研衛星的合同;為國外發射了1顆衛星,尚握有3顆衛星的發射合同(加拿大衛星通信公司1顆,越南2顆)。
日本航天開發政策還強調:在確保為國民提供通信廣播、氣象、地球觀測、環境變化、防災救災等航天產品的同時,積極落實、全力發展以科學技術發展、安全保障和振興產業為中心的最優先級、優先級計劃和長遠發展規劃。
1)最優先級(5年內):完成自主研發的“準天頂衛星”(QZS)系統(4星體制),滿足防衛、反恐用的快速響應小型偵察衛星系統,先進的“具備新系統結構的先進觀測衛星”系統,智能化、商業發射用的H-2A火箭和以“艾普斯龍”(Epsilon)為基礎發展的低成本、機動能力強的固體火箭。
2)優先級(6~10年):完善“準天頂衛星”系統(7星體制),構建自主防空網絡用的早期預警衛星,配備機械手,清除軌道碎片用的環保衛星,雙項多用途通信衛星,具有國際競爭力的H-3火箭,以及低成本的太空發射系統。
3)長遠發展規劃(10~50年):構建起太陽光發電衛星系統,研發平流層衛星、可重復使用的太空飛行系統和海上發射系統。
此外,日本還計劃加強通過發射民用器件性能驗證衛星等來推進先進的民用技術在航天領域的應用,把技術成熟的航天專利技術拓展到民用領域,縮短先進的民用技術在航天領域應用的時間,大幅度地提高航天產業的效益,推進/支持航天發展。
新航天法頒布近6年,日本航天發生了重大變化,日本航天產業化進程加快,加快了航天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的速度和提高了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成為日本產業振興的源動力。2012年,日本航天產業的銷售額突破7兆日元。日本的航天/防衛/安全保障專家、日本航空宇宙工業會前技術部長、東京財團研究員和國際宇航聯合會宇宙經濟技術委員會委員坂本規博預測:執行航天產業振興政策,到2020年日本航天產業的銷售額將翻番,達14兆~15兆日元。

日本“艾普斯龍”火箭飛行示意圖
不過要指出,日本在推進航天產業化和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進程中,依然存在一系列難以逾越的障礙:日本航天開發投入已超過“航天開發投入不得超過國民生產總值(GDP)0.05%”的底線,是否會得到國會(國民)認可?即便如此,其實際投入與計劃需求尚存在巨大差距,盡管三菱重工業、三菱電機、日本電氣等民營企業在不斷加大航天投入,短時間內仍很難解決兩者間的矛盾;雖然日本采取并將繼續支持民用器件在航天領域應用,但依然無法徹底解決因缺乏勞動力,從而導致勞動力成本過高,資源匱乏,絕大多數原材料要靠進口,致使航天產品,特別是火箭和整星產品價格高于國際同類產品市場報價,導致缺乏市場競爭力。
不過,新航天法的頒布,開發體制的調整,開發重點的轉移,已成為驅動日本產業振興的源動力,為日本航天活動帶來新生機。隨著政府支持衛星、火箭等航天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經濟產業省等正大幅度加大在技術方面占絕對優勢且利于產業化項目的投入,以促進“艾普斯龍”火箭、“具備新系統結構的先進觀測衛星”平臺進入國際市場,以及支持發射民用器件驗證衛星等推進民用器件在航天領域應用并進入國際市場、加大對超高分辨率合成孔徑雷達小型化研發的投資力度、支持太陽能發電等。這對推進日本航天產業化和解決上述困難,加快航天開發、應用和產業化,加速產業振興會產生一定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安倍內閣把發展低成本的“艾普斯龍”火箭、H-2A火箭的智能化和低成本,發展運載能力更強的H-3火箭作為最優先和優先級發展項目。這對振興其航天產業,增強航天產品市場競爭力不無好處。但與其否認侵略歷史,不斷與鄰國制造矛盾與沖突,以及完善以情報搜集衛星為核心的情報搜集系統、X頻段防衛通信衛星系統、加速早期預警衛星研發、擬盡快啟動防衛快速響應系統等聯系起來,不得不使人們懷疑其是否另有目的,需愛好和平的人們關注。
陸征/本文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