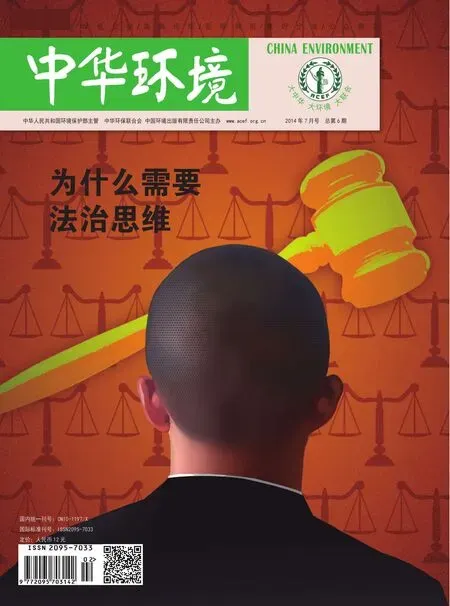環境群體性事件的法則
李蒙
環境群體性事件的法則
李蒙

甘肅徽縣的血鉛兒童。 CFP/供圖
近年來環境污染群體性事件呈多發態勢,分析發現,因環境污染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相較于其他群體性事件,人數眾多,聲勢浩大,政府的應對和控制能力薄弱,而且最終多是以當地政府迅速宣布停建項目,得以平息事態。之后類似的事件反復發生,已經形成了一種模式。
環境污染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有什么破解之道?與其等著矛盾醞釀到一定程度爆發,為什么不進行事先的紓解?政府的決策如何公開透明,讓公眾知曉?政府與公眾溝通對話的平臺在哪里?群體性事件中如何引導公眾的行為趨向合法、理性?
搭建談判溝通的平臺
我國已進入一個環境問題敏感時期:經濟發展快,環境污染嚴重;群眾的環境意識迅速提高,依法維護自身環境權益的愿望日益強烈;加上政府處理這類問題不論從制度上、認識上和應對實踐上,都準備不足,難以適應形勢需要,因此造成群體性事件的多發。
從認識上來說,有些地方政府長期以來重經濟、輕環保,為體現政績招商引資往往降低環保門檻,在環境問題上自覺不自覺的站在人民群眾的對立面,成為污染企業的代言人。很多污染問題直接影響群眾健康,突破了人民群眾的心理底線。而有的官員不能堅持以人為本,忽視民意,對群眾依法維護自身環境權益的強烈愿望,認識嚴重不足,一旦出現了群眾抗議,往往進退失據,應對乏力,事情鬧大,就一停了之。這既給人留下決策草率的印象,同時也變相證明群體性事件是扭轉政策的有效途徑,從而不排除可能形成非民主的“多數人的暴政”。
環境污染問題之所以容易積累官民矛盾,首先是對于此類問題,公眾參與的程度非常有限,而政府又在碎片化、散沙化的群眾意見表達中難以找到有代表性的意見,無法找到能為多數群眾接受的談判對手,雙方缺乏基本的溝通平臺。
事實上,環境訴訟是可以創造溝通平臺的出路。
在國外,民間往往有能夠代表各方各派利益的群眾組織,即NGO群體。而國內,目前這樣的組織非常缺乏。在僅有的環保NGO中,往往也因半官方或聽命于官方的色彩,使群眾難以信任。一旦群眾失信,環保NGO就難以實現與群眾的有效溝通,更做不了群眾的主。雖然現在國內已經有了像“自然之友”、“自然大學”這樣的環保NGO,但它們要想介入到某個環境污染事件中充當群眾的利益方代表,還有待時日。目前,多數環保NGO還處于既難以取得公眾完全信任,也難以得到官方應有承認的兩難境地。
沒有談判對手,政府怎么讓公眾充分參與到環境項目立項、環評、審批的全過程呢?而不滿的民意一旦積累,政府與群眾之間的溝通渠道又無法暢通,只能各說各話。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群體性事件。
新環保法提出有限環境公益訴訟,在法院的組織調解下,可以搭建起一個政府與公眾溝通的平臺。公眾聘請的訴訟代理人和參與者既是自身利益的代表,又是可以與政府談判的對手。這樣的談判對手,包括律師、某一環境領域的專家學者和環保NGO。
律師是群眾聘請的,群眾自然會信任;律師同時可以起到向群眾普及法律知識、客觀理性看待問題的作用,他們的話,群眾比較聽得進去。對于政府,律師是與群眾溝通的橋梁,律師懂法律,講規則,政府與律師的對話就可以在法律和政策的范圍內展開,理性對話,協商達成一致的可能性會大增。

由于規劃問題,湖北武漢鍋頂山垃圾焚燒廠如今基本位于漢陽區中心地帶。 李蒙/攝
在環境訴訟中,具有專業背景的專家學者也是重要的角色。在以往涉及環境影響的項目中,政府也請來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 但群眾往往覺得這些專家收了政府的好處,在替政府說話,很難信任他們。若是群眾自己聘請的專家學者,他們的學術觀點和立場,會更多地從公眾的角度出發,因而有更強的社會公信力。如果政府能夠熱情歡迎這批專家參與交流,既可以彌補項目原有的某些不足,又可以贏得更多的公眾信任,何樂而不為?
環保NGO,也可以通過環境訴訟,找到自己參與的方式、方法和位置,在政府和群眾之間起到很好的橋梁作用。
引導群眾理性客觀解決問題
除了搭建談判平臺,環境訴訟對引導群眾理性客觀地看待環境問題,積極遏止群體性事件,往往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如果群眾找不到可以“說理”的地方,又無法獲得正確的信息,他們走上街頭是必然的。一旦環境訴訟搭建起了官民溝通的平臺,群眾的基本訴求有了出口,就不需要走上街頭,“補償性發泄”了。
2010年,我到甘肅徽縣采訪當地的血鉛中毒事件,當時有800多村民起訴污染企業,代理律師是北京義派律師事務所的王振宇主任和李娟律師。在沒有立案之前,當地群眾多次上訪,到縣政府,到隴南市政府,到甘肅省政府,有時達到千人,引發了若干起較大的群體性事件。但是上訪4年,沒有拿到一分錢賠償。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決定走司法途徑試一試,到北京聘請了律師。通過兩位律師的艱辛努力,終于說服當地法院給受害村民立案,將這一環境污染事件納入法律程序。
之后,又經過三年,在法院的主持下,通過律師與政府、企業的艱苦談判,終于達成賠償協議,受害群眾拿到了上千萬元的賠償,問題得以圓滿解決。雖然賠償不算多,但相比于之前的上訪無果卻要好得多。而對于政府來說,自立案后,受害群眾再也沒有去上訪,一下子穩定住了當地社會秩序。
2014年5月底,我到湖北武漢采訪鍋頂山醫療垃圾焚燒事件,當地群眾也準備起訴污染企業,而聘請的律師還是王振宇、李娟。我不僅看到了群眾對律師的信任,對將污染事件納入法治軌道的歡欣鼓舞,也看到了當地政府的誠意。漢陽區的黨政領導與群眾代表和律師坐在一起交流,歡迎當地群眾在律師的幫助下通過法制軌道解決問題。
可以想見,環境群體事件立案之后,當地之前發生的群眾堵路堵門現象將不再發生。
司法機關不要葉公好龍
作為一名記者,筆者曾多次采訪環境污染事件,看到的是各地司法機關對待環境訴訟往往持比較消極的態度,經常不予立案。2013年全年,全國沒有一起環境公益訴訟得以立案。一個“零”的記錄,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至于環境私益訴訟,雖然也能達到公益訴訟的社會效果,但在立案環節更是難上加難。
在黨中央大力提倡“依法治國”的今天,司法機關應該轉變觀念,體會到環境訴訟在防治群體性事件上的良好社會效果,敞開大門立案。也許司法機關擔心會出現濫訴,浪費司法資源。其實大可不必,在全國不少地方的環保法庭,往往一年都沒有一個案子,環境訴訟在訴訟主體、舉證成本、辯護難度、訴訟費用等方面還存在著許多問題,真正能夠進入司法程序中的并不多。
因此,希望司法機關能在訴訟費方面對環境訴訟實行更多的優惠,對于收入不高的一般群眾,可以讓他們免交、緩交訴訟費,使更多的群眾走進法庭,而不是走上街頭,造成社會的不安定。
■ 名詞解釋
補償性發泄
當下中國在社會和心理的層面,產生出了某些失意者,表現為經濟上的低收入性、政治上的低影響力、生活上的貧困性、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等特征。且這類人群是以原子化的個體形式存在,面對強有力的秩序以及強勢群體,他們總是感覺到渺小和無力的。他們解決自己心理問題的辦法,是在社會的心理食物鏈上,去吃比自己更弱小的人,用心理分析的術語說就叫“補償性發泄”。
什么時候這些弱者不再以“補償性發泄”作為主要發泄方式,這種惡性事件就會少多了。社會更加穩定,需要全社會尋找改善其生存狀態,調適其心情及心態的辦法,同時彌合社會裂痕,并暢通階層流動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