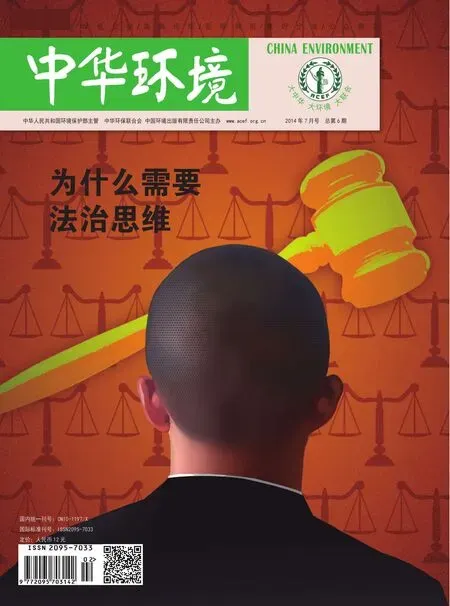環境基本法:環境法治建設的必需品
徐祥民 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劉 宏 中國海洋大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環境基本法:環境法治建設的必需品
徐祥民 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劉 宏 中國海洋大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自2011年《環境保護法》(以下簡稱《環境法》)修訂被列入十一屆全國人大立法計劃以來,業界專家以及公眾對其的爭論就不絕于耳。而人們在審視現行《環境法》之后,往往更關注于具體的法條是否全面,立法目的是否恰當,以及現行環境管理體制是否合適,卻忽略了修訂后的《環境法》在整個環境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問題。但后者恰恰是重點。
在當前的環境法律體系中,法條重疊甚至相互沖突的例子不勝枚舉。而明確樹立《環境法》的基本法地位,正是解決該問題的關鍵舉措。
現行《環境法》沒有基本法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盡管名稱讀起來好像是環境法體系中的基本法,也有不少研究者把它稱為環境基本法,并作為我國環境法體系的組成部分來評判,但是我們還是會得出這樣一個評判結論:現行《環境法》并沒有取得環境基本法地位。
首先,《環境法》并沒有從其前身《環境保護法(試行)》(以下簡稱《環境法(試行)》)那里繼承來環境基本法的地位。《環境法(試行)》是在“撥亂反正”的時代條件下倉促出臺的,不僅沒有為擔當環境法體系的統帥做好準備,而且“試行法”身份也使其無法在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的各種環境單行法中取得領導地位。
《環境法(試行)》對于比其頒布時間更早的相關法律,并不具有“后來居上”的地位。就拿《森林法(試行)》來說,在起草之初,它并沒有準備好要接受未來將會出臺的法律的“節制”;而《環境法(試行)》出臺時,也沒有明確提出要讓它服從“節制”。
事實上,像《森林法(試行)》這樣,早于《環境法(試行)》出臺的法律,與《環境法(試行)》都是獨立的法律個體,它們相互之間并不存在哪一個應當處于領導地位的關系。
其次,《環境法(試行)》對在其之后頒布的環境法律也沒有取得基本法的地位。1982年的《海洋環境保護法》(以下簡稱《海環法》)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頒布的法律。僅“正式頒布”這一點就足以將《環境法(試行)》的所有基本法品質抵消為零。
1984年的《水污染防治法》、《森林法》,1985年的《草原法》,1986年的《漁業法》、《礦產資源法》、《土地管理法》,1987年的《大氣污染防治法》,1988年的《水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既沒有把《環境法(試行)》當成它們的根據,也沒有在創設新制度時向《環境法(試行)》求“源”,或在做出與《環境法(試行)》不一致的規定時遵守“不破不立”的立法規律,就有關的不一致做嚴肅的立法說明。看起來,這些法律在中國環境法治建設歷史上的“來頭”似乎都比《環境法(試行)》要大。
1989年環境法正式頒布,這次雖然摘掉了“試行法”的帽子,但同樣沒有幫助它在事實上取得環境基本法的地位。
與《環境法(試行)》一樣,《環境法》沒有提出讓早已自成體系的《森林法》、《草原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服從它的“節制”的要求。同時,它也沒有對在其頒布之后將要制定或修改的環境保護單行法提出必須服從它的“節制”的要求。這部正式頒布的環境法既沒有對已經進入環境法調整范圍之內的環境保護事務做“全覆蓋”的規定,從而爭得比其他各種環境保護單行法更“基本”的地位,也沒有取得確立其基本法地位的授權,比如要求已經存在的和可能制定的其他環境法律法規接受它的指導等。
《環境法》與被我們列入《環境法》的《污染防治法》、《資源養護法》等法律、法規,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各走各的道。比如,1991年《水土保持法》的頒布“無視”環境法的存在,就像其前身《水土保持工作條例》(1982年6月30日國務院發布)的出臺也是“獨往獨來”一樣。再如,1995年的《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盡管其基本執行主體與《環境法》一樣,都是“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但它絲毫沒有做“源出于”《環境法》的表示。

僅“正式頒布”這一點,《海環法》就足以將《環境法(試行)》的所有基本法品質抵消為零。CFP/供圖
環境法治建設需要基本法
確立一部環境基本法,是我國環境法治建設的必需品,也是完善我國環境立法體系的必需品。
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中要求:“美國之各項政策、法律及公法之解釋與執行均應與本法之規定相一致”。以上規定,既反映了國家對環境基本法的需要,也說明為環境法體系制定環境基本法的必要性。
然而,我國《環境法》在30多年的歷程中發生了階段性的變化,產生出大批形成于不同時期的環境法律文件。而這,又造成不同時期累積的環境法律文件之間存在不一致。
張梓太先生曾指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按照環境要素陸續制定的單行法之間出現了“不夠協調甚至沖突”,包括“立法的指導思想、基本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全一致”。
也就是說,這些不同時期形成的環境法律法規無法構成一個內容協調統一的環境法律體系。
污染防治法時期,《環境法》接受污染之不可避免的假定,這就如同人工制造的劇毒化學藥物盡管劇毒也不能不使用一樣。所以在這一認識基礎上形成的環境法只能是以污染防治為中心,并且具有“末端治理”特點。
而清潔生產法時期,《環境法》相信人類可以通過預防性努力減輕甚至局部消除自身活動帶給人類和人類環境的消極影響。
再到循環性社會法時期,《環境法》“注意到人類是自然的組成部分,以生態文明為基本理念,以環境友好為基本態度,以與自然和諧相處為價值取向”,這一時期的《環境法》便要求人們的思想從自然的統治者、主宰者降低為自然的一部分,回歸到自然之中來。
每個時期中,《環境法》的基本指導思想、環保理念、環境保護路徑等方面都存在著難以彌合的巨大差異。
《環境法》的發展歷程說明,要使《環境法》真正成為一個內部協調一致的法律體系,必須對現有環境法律、法規做“大手術”。
手術方案就是建立環境基本法,賦予它“節制”所有環境法律法規的權威,包括《美國環境政策法》所說的對全國“各項政策、法律及公法之解釋與執行”權威。
如今我國《環境法》已經形成一個由兩大方陣十余支隊伍構成的龐大的法律體系。然而,這個體系卻沒有被人們發現。即便在個別的檢閱者中,其觀點也不盡相同。
蔡守秋先生把“環境資源法體系”分為“污染防治法”、“自然資源利用與管理法”、“以城市、鄉村和西部區域開發整治為主要內容的國土開發整治法”、“以防治自然災害為主要內容的災害防治法”、“以保護野生動植物及其棲息環境為主要內容的自然保護法”、“以防治生態破壞和建設生態環境為主要內容的生態環境建設法”和“以能源開發、利用、節約及其管理為主要內容的能源法”7個“子體系”。
而王燦發先生則認為,我國環境法體系在橫向結構上由“污染和其他公害防治法”、“自然保護法”、“自然資源保護法”、“特別方面環境管理法”、“環境標準法”、“環境責任和程序法”等分支構成。
曹明德教授的看法又有不同。他認為在“環境資源法體系”的“統一整體”中,最重要的分支有兩個,一個是環境污染防治法,一個是自然資源保護法。而自然資源保護法又有“實質”與“形式”之分。
這些不同劃分的存在至少說明了兩點:第一,我國環境法尚未形成法定的明確體系;第二,按照不同劃分標準劃分出來的不同分支之間存在著已經暴露的和潛在的不協調。
本文不想具體討論已經存在的或潛在的不協調,但從以上論述可以見得,我國已經創造了一個龐大的環境法隊伍,而這支隊伍卻“群龍無首”。雖然學者們勉強地把相關的法律法規“劃撥”給這個或那個分支,但它們實際上還沒有真正構成一個嚴整的法律體系。
所以,要化解我國環境法體系化危機的辦法是借《環境法》修改之機為“群龍”立“首”,把《環境法》改造成環境基本法。
以基本法定位拓展立法空間
在現行《環境法》全部47條的規定中有32條針對污染防治,可以說除對環境下定義,規定環境管理機關的權、責的條款和該法的“附則”等之外,幾乎全部條款都是污染防治或包含污染防治。
很明顯,這些內容與我國《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現行法律法規的內容是重疊的。
即使不考慮單行法的內容更具體、科學依據更堅實、可操作性更強等情況,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些單行法實際上已經占用了《環境法》那32條的幾乎全部立法空間。如果不能轉變為環境基本法,《環境法》再規定污染防治就將成為對立法資源的浪費。
此外,《環境法》對污染防治之外的環境保護事務的規定也沒有充分展開的空間。例如,《環境法》設有“保護和改善環境”一章,其內容涉及資源開發、防治水土流失、城市建設規劃等。沒有人相信該法的有關規定會比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城市規劃法等更科學,更值得執法者遵循。
再如,《環境法》就“加強對海洋環境的保護”所做的規定(第二十一條),比之于《海環法》,它合理存在的理由只能是:環境法是“綱”,而《海環法》不過是“綱”下之“目”。但這個理由只有在把《環境法》改造成環境基本法時才能成立。
在參與《環境法》修訂的過程中,筆者曾提出過調整《環境法》的立法目的的建議。但是,如果《環境法》對《污染防治法》、《生態保護法》等單行法不享有統帥地位,那么這一調整的作用將變得微乎其微。
所以,只有在把《環境法》改變為環境基本法時,多數的建議才有意義。
【本文是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建設(培育)項目“中國環境法治建設發展報告”的階段性成果】
■補充材料
單行法
單行法是指針對特定環境要素和自然資源保護而頒布的專門環境立法。在單行法模式下,各單行法適用范圍各異,但效力相同。除各類單行法,沒有規定多個環境要素或自然資源保護的綜合性環境立法,也沒有協調各單行法之間關系的專項法律存在。從環境法的歷史發展來看,在環境立法初期,各國均采用單行法模式。但是,隨著環境法的發展,許多國家轉采其他立法模式,但仍有一些英美法系國家,如美國、新加坡等采用單行法模式。
基本法
環境基本法,是指在一國環境立法體系內,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對環境法基本原則、基本制度、基本體制以及體系內的協調等內容作總括性規定的法律文件。基本法的作用在于“明示環境保護制度、政策之相關基本方針,揭示環境保護個別法制、措施之基本方向與共通性質,導引具體制度、政策與環境保護相關法令之制(訂)定,以落實實施達成環境保護之總目標”。世界上有很多國家環境立法采用基本法模式,如日本、俄羅斯、韓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