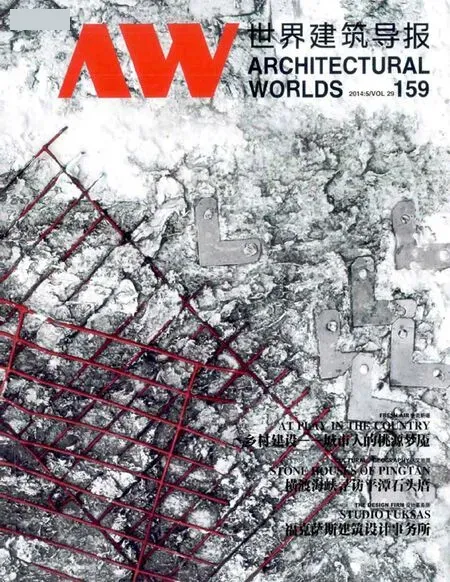AW訪談:安德魯?扎戈
(譯)徐云濤 (圖)Andrew Zago

AW:大家很感興趣人們是如何走進設計行業、如何開展設計工作的,同時也想知道跨界是如何實現的。而我本人則對你的作品與藝術的結合比較感興趣。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深圳現在對藝術領域投入了大量資金,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這將會帶動更多的創意產業的發展。
AZ(安德魯·扎戈):這沒壞處啊(笑)。
AW:沒壞處!全民供養藝術家啊。藝術究竟該如何來幫助我們重新思考建筑呢?
AZ:與藝術的關系,這個課題我思考了很久也不斷提及。我的學科背景是藝術,而且我堅信建筑就是一種藝術形式。它是一種非常特別的藝術形式,和繪畫不同,它有其特有的社會責任和學科構成,但是在我看來,就門類而言,建筑與藝術并無差異。
另一方面,當建筑走向學科自律或者更準確的說是準自律(quasi-autonomous)的時候,我常常會對建筑技術與媒介有所感觸,我非常著迷于這些心得體會。因為那些圖紙在我眼里已不再只是技術性的平面圖,我不會只考慮面積或者墻體之類的問題,我還會將它們看作一張張畫作。我覺得這兩者之間的關系由來已久。只是近來人們才意識到這一問題,才開始在建筑領域里探討這一問題。不過這一直是我所做項目的中心課題。
我一直嘗試著從更綜合的層面來探討技術問題,因為現階段,我們不再只停留于紙筆作圖的階段,我們會制作一些模型,有時候也會制作一些奇怪的結構或者各種參數模型。無論我們制作的是什么,如果要付諸實踐,這些圖紙或者模型將不再只是簡單意義上的物體,因為我們要借此演示建筑的結構。我可以很明確地說這就是這一學科的準自律。我可以給你舉個例子,我們一開始可能會用盒子和膠片制作各種奇形怪狀的模型。當我們著手做項目的時候,在某個階段,這些模型就開始變成建筑實體,但我絕對不會將這些模型看作是我的“藝術作品”,我只是在建造立面的時候會參考它。
我認為在我們這個領域,藝術性與建筑性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有了藝術性,我們創造的這些東西才有可能實現它們的自律。而且,這些模型也許還預示著未來建筑的形態,雖然這種預示還難下定論。如果現在出現了某種奇特的模型,或許以后就會聳立起類似的建筑。我記得有次在紐約MoMA的墻上看到一張西格拉姆大廈(Seagram Building)的設計圖,是大廈的立面圖而且還裝裱了起來。這看上去就像是件藝術品。這張設計圖不是為MoMA的展覽專門而作,而是為了更準確的建造大廈而作的。但是即便這只是一張建筑設計圖,卻恰如其分地懸掛在美術館的展墻上。
AW:跟你提到的西格拉姆大廈例子類似,我們也會讓藝術家們去描繪這些圖景,借此來訓練他們。我可以想象得到,接下來你會讓你的學生去描繪西格拉姆大廈。
AZ:沒錯,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課題。我們的主要工作是實現各種建筑項目。但是有時候我們的實現方式會各不相同。我們曾在底特律拍過很多照片,這也許可以解釋這種觀點。照片中的街道都是現有的,沒有一條是我設計的。我只是自創了一種影像處理技術,從而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底特律的街道。這和描繪西格拉姆大廈有著異曲同工之效。不過問題就在于:你打算怎么畫?莫奈(Monet)筆下的教堂和建筑師所描繪的是不一樣的吧?從某種意義上說,觀看和描繪都有很多方式,觀看方式的不同,描繪的方式也會不一樣。你首先確定視點,然后確定再現這座舊城的方式,最后按照你的視點描繪出來。最終你就可以設計一座新城了,這就像是你在城市的主廣場中選好一個視點,來觀看這座城市。
AW:如果和中國的園林設計結合來談,這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在中國園林中,無論你身處何處,映入眼簾的景觀都是不一樣的。一個成功的園林設計可以將園林以外的景象以不同的方式包容進來。這么來講的話,不同的景觀則是移動和設計共同的產物。
AZ:去年我曾經在京都待了一段時間,期間參觀了好幾座日本庭院。事實上,說到再現或者說城市景觀再現,我曾經長時間研習朝鮮王朝的皇宮畫作。出于某些原因我非常喜歡這些畫作。我記得在參觀京都的一座著名庭院的時候,我也見到了跟你剛剛所說的類似的景致,由于對庭院特意的安排,某些本不是庭院的景物也成為了庭院的一個部分。我總覺得這樣別致的風景是因為日本人知道怎么巧妙地將自然之物融入人工之中,因為庭院并非以自然之景為主。我們所看到的其實并不是真實的山石,而是一件人為的藝術品。但是即便是假山也很棒!我們可以從中領略到日本人對藝術恰到好處的熱愛。在他們看來,自然就是人工的一個部分。而且我很喜歡他們的這種觀點。我曾經也覺得我們跟自然是有某種關系的,還的確有。而且這種關系是真實的,因為它可以為你所用。
AW:而且這種關系還會帶來一些觸及不到的美感,這又再次回到那個問題,就是藝術和你經常要處理的形象的問題,或者說是在既定形象前再度創造形象的問題。
AZ:這個話題很有意思,技術層面中繪畫的功能是什么?或者說“這些元素是如何融合到一起的”。比如說博羅米尼(Borromini)筆下的教堂,他以獨到的線條排布表現各種建筑,這就是他融合這些元素的方式。這些畫作并不是用來向人們解釋建筑結構的,事實上,遺留在紙上的是設計師工作過程的痕跡。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這么理解,設計師本人或者其他人可以拿著這張畫跟別人說,“付錢吧,您將會得到一座一模一樣的建筑。”
這里的畫作和技術有重合的成分,而且兩者在其中是相輔相成的,但是它們還是有不一樣的方面。我在說第一個種類,也就是我說的藝術的時候,我指的是繪畫。我開始意識到無論是朝鮮王朝還是模擬都市之中,人們都會用到繪畫。我開始關注人們是如何就項目來交流的,這也成為探索新的美學領域的契機。
AW:我想到了你的文章中關于形象的觀點,你說形象是一種運動,是對世界的描繪,而不是對建筑的描繪,因為藝術就是對世界以及世界起源的形象再現。
AZ:這兩者之間的關系非常奇特。我們非常有必要了解它們為什么是一樣的,與此同時,也非常有必要了解它們又為什么不一樣。和繪畫一樣,建筑也是關于建構這個世界的,而且它更多地是從精神層面來實現這一功能。在探討這一學科的時候,我可能有些沙文主義的傾向,因為我覺得建筑是藝術之母。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一段話就是很好的證明,“我們建造了房屋,隨后它們也塑造了我們。”這并非一句宣傳國家機器的政治口號,但是如果從賦予城市某種特征或者說干預人們介入世界的層面而言,這倒挺像一句政治口號的。
AW:我可不可以就你剛剛的這個話題問一下,誰是藝術之父?
AZ:法國啟蒙運動時期,有一位建筑師叫尼古拉斯·勒杜(Nicolas Ledoux)。他寫了一本法文書,我記得好像是《建筑與藝術、道德和立法的關系》(Architecture in Relation to Art, Morals, and Legislation)。在我看來,藝術、倫理和政治,這三者就是建筑領域中的三大關系。
AW:是不是可以這么理解,藝術之母是一個,父親有三個?不過話說回來,這個倒是指出了建筑師們所面臨的來自各方的批判。比如說如果建筑師太過藝術,他將會因忽視社會和政治而受到批評。相反的,如果太過政治,又會被批評沒有藝術造詣。
AZ:我的態度倒有些不同。我覺得對有創造力的建筑師而言——我是指那些致力于創造的建筑師——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們要清楚建筑的創造性是建構在社會性與政治性之中的。你會發現有很多建筑師,他們幾乎不考慮創造性的,他們只是用他們那少得可憐的、東拼西湊的社會政治元素去粉飾他們的設計。
我經常和同事們討論建筑作為一種職業和作為一門學科的差異。總的來說,作為一種職業,從業者只要完成工作就可以了;但是作為一門學科,你就要自覺地去思考、提升藝術形式。
AW:你從誰那里獲取提升藝術形式的經驗呢?
AZ:可以從同行那里。我出版我的作品集,其實就是想跟同行們交流。我覺得其他領域應該也是這樣的吧。一門學科少不了從事相同工作的人來支撐。比如說醫學領域中,有人出版了自己的研究論文,同行之間就會相互交流評論。還比如公共衛生領域,這個領域應該受眾會比較多。有時候你有了新的進展,就會想跟其他人分享。不過我估計大部分建筑師都不會太注意這一方面。
AW:關于職業的交流不是有很多嗎?
AZ:是啊。學科與職業之間的關系其實很有意思。有一家名為Hetterson Fox的大型公司,他們在全球各地都有項目。比如說在韓國首爾的仁川機場附近,他們幾乎打造了一座城市。有好些年,他們一直被當作是后現代的建筑師。前段時間,我參觀了他們為洛杉磯設計的一家汽車博物館。它看上去就像是出自我的一個朋友或者同事之手,感覺好像是在藝穗節上經常看到的作品那樣,不是那種中規中矩的作品。這就是關鍵所在,他們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是建立在這門學科的創造性之上的。他們的工作就像是大家所理解的那樣,是一種后現代的實驗。他們的變化不大,但是他們的團隊人數不多,這樣團隊運行起來就很靈活,因為成員們相互之間都比較獨立,而且也獨具想法。正是這樣的團隊才能營造更好的城市生態。
AW:這個有些叛逆的想法倒是挺有意思的。現在整個中國都忙于將創意產業融入城市發展之中,尤其是深圳。所以也就出現了這么一個問題:對于這一精英行業的支持,我們應該做到什么程度?
AZ:我覺得“精英”這個詞可能不太適合。有些從事這類工作的人,我并不太喜歡他們的作品,而且我覺得有些甚至是敗筆。不過這些倒也不重要,畢竟他們或多或少都為這門學科做了些貢獻。
AW:他們加入到交流之中了。
AZ:沒錯,他們加入到交流之中了。從這個層面而言,這是一門開放的學科。這么來看,這門學科的確是有必要得到支持。如果不是只依靠解放思想的話,我們該怎么支持,這似乎還難下定論。
跟你說個故事,我和妹妹小的時候看到后院有只小鳥,當時我在籬笆上用草做了個鳥巢,期待著這只鳥會用得上。這就像是到處都有各種以科技命名的城市,但是人們并不知道為什么這么叫,但是他們就是要起名叫硅谷之類的。他們大概是想,如果把房子都建到一起,是不是這名字就名副其實了?
支持創意產業就像是煉金一樣。我覺得在藝術家身上投資是一種很好的方式。幾年前一家名為“美國藝術家”的機構做了一項研究,他們發現大部分美國人都認為藝術很重要,但是沒幾個人覺得藝術家很重要。這家機構非常直白的告訴社會——沒有藝術家就沒有藝術。他們成立了一個慈善基金,每年支持50個藝術家,每人可獲得5萬美元的資助,這其中也包括建筑和設計。我就獲得了一筆贊助。所以他們支持藝術的方式不是投資藝術機構,而是直接把錢給藝術家,這就相當于直接支持了這門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