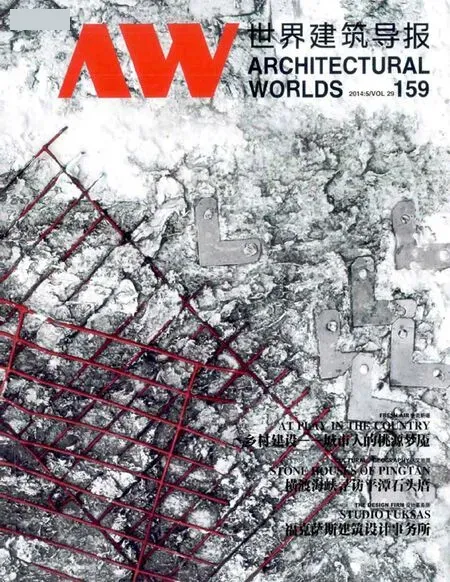怪象
(文)Andrew Zago (譯)徐云濤

怪象
傳統觀念中,關于技藝的核心評判標準是合適與否。歷史上,建筑行業的技術準則為建筑師們提供了各種工作方法,但與此同時也限制了我們的工作,因為它要求一切都是建立在合理的推算之上的。如今,我們也許不再奉其為圭臬,但是在處理比例、樣式、布局、裝飾、材料的表現、結構等問題時,還是擺脫不了長久以來形成的慣性,這是前賢留下的衣缽,后人們或可接納或可擯棄。這么一來,傳統理念中的評價標準依然影響著我們,即便在工作中我們不再以此為參照。“后諷刺”(post-ironic)時期,我們可以借用并不合適的手法來改變評價標準。為了追求完美,傳統工藝經營已久的那套標準,現在正讓位給更為獨特的變相手法。
怪象與正統之間的關系尤其特別。它既不與正統相茍同,也不會批判正統,而是在遵循更為普世的文化體系的同時,建構一套其特有的邏輯系統,自成一體。它的這套體系既不與傳統相沖突,也不會一味迎合。
怪象手法既不是顛覆性的也不是惡意歪曲的。采用這種手法的建筑師有必要背離他們的常態,放棄形成已久的技術經驗,從而為鮮活的想法做好準備。不過奇形怪狀的創作有可能看上去頗顯笨拙,甚至還有可能被誤解成為譏諷之作。作品可能毫無藝術性可言,它既不感興趣推翻傳統的權力架構,也無意于批判這一架構。它完全走出正統的窠臼,建立一套特有的審美機制。時而肯定時而否定的意涵,給怪象文藝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通過以下三個案例,我們可以了解到怪象文藝與其他風格的不同之處。這三個案例位于巴黎,是對城市棲居空間的不同表現形式。第一個案例是古斯塔夫·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于1877年創作的《雨中的歐洲廣場》(La Place de l’Europe,temps de pluie),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伸向遠方的豪斯曼大街。行人們一邊欣賞著街景一邊悠閑地散著步,此時此刻他們完全融入了整個巴黎,閑適的步履映照出這個城市的結構形態。如今罕見的文化樣式似乎在這些行人身上和街景中依稀還能看到些影子,街道的布局方式似乎束縛住了人們的行動。
第二個案例中,一名跑酷訓練者正跳躍于巴黎的房屋之間。這是一項令人嘆為觀止的運動,不僅僅是因為其靈活多變,還在于它改變了建筑的常規功能。跑酷是一項解構主義的運動,社會帶給城市的壓力在每一個不尋常的躍動中盡顯無疑,與此同時人們也開始質疑城市是不是奪去了什么。事實上,跑酷愛好者和行人的行動都離不開城市現有的環境,他們都受制于城市,卻又想改變它。
第三個案例發生在國家圖書館前,法國雜技演員皮埃爾-安東尼·杜索勒茲(Pierre-Antoine Dussouillez)正在以一種不同尋常的動作登上圖書館的樓梯。雖然和跑酷愛好者一樣動作靈巧,但是其用意卻截然不同。他的這一舉動既看不出行人們的優雅,也看不出跑酷愛好者輕巧如燕的身姿。杜索勒茲或許做錯了,他那畸形的肢體令人費解,究竟是抵制現有的城市形式還是另有所思。不過有意思的是,此舉一出,他似乎完全不用擔心這座城市會影響到他的一舉一動,他完全不用考慮改變自己來適應城市,反倒是這座城市來適應他。

怪象與現實
一方面,怪象只是一種手法而不是一條準則,用來打通文化中的某些禁區,這樣建筑設計才能適得其所。另外一方面,伴隨著新的感知方式,這種手法可以借助其特有的邏輯體系重新介入這個世界。看上去,似乎怪象手法不經意間創造出了一種新的方式,就個體而言,這只是一次創新,總而論之,它卻開辟了一片新天地。這種新手法不斷推出各種莫名其妙的創作,這些看似偶然的個體最終為新的文化樣式奠定了基礎。
作為一種文化實踐,建筑與物質世界的關系是共生的。正因為這樣,建筑作為一種人類的技藝,它應該對自己對這一角色負責,另外一方面在某一程度上它也應該忠實于現實世界。怪象手法通過技術層面的介入(例如改變建筑材料里的技術參數),改變技藝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對于傳統技藝的批判,有一點是值得我們借鑒的,那就是傳統技藝追求對手法、材料與效果的整體把握。在現代建筑中,這已經遙不可及了,比如“偶然性”這個問題。怪象手法會允許一定限度的技術介入(例如“由上至下”的傳統技術),同時也會開創其他的方式來制造不確定性。它這么做并不僅僅是在復雜的現實之中放棄個體的決定權,而是讓創造力和偶然性成為采取決定的主導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