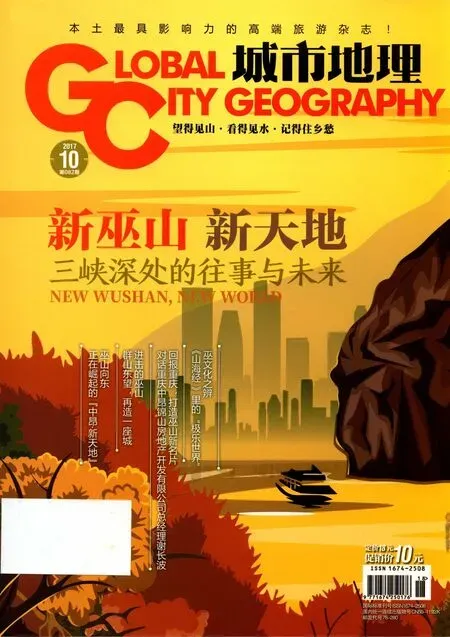烏江號(hào)子百里畫廊上的驚濤往事
文+文梓光 圖+文梓光 盧進(jìn) 簡文相
烏江號(hào)子百里畫廊上的驚濤往事
Boatmen and Their Labour Songs in Wujiang
文+文梓光 圖+文梓光 盧進(jìn) 簡文相

英文導(dǎo)讀: Boatmen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Wujiang River those years. They created Labour songs in many styles. We may find that their work songs are artistic.
一聲聲烏江號(hào)子,從赤裸身體、披肝瀝膽艱難前行的船工們口中沖出,那種高亢激越、撼山震水的旋律,那種撩人心尖、奪人心魄的力量,頓時(shí)將眼前的山山水水一下子震蕩得遠(yuǎn)了,徒留那起起伏伏、顫顫悠悠的號(hào)聲,回蕩在天空與大地之間。
關(guān)于川江號(hào)子,我們聽聞得太多,而烏江號(hào)子,我們則知曉得太少。它就像一段隱沒在烏江畫廊上的悠遠(yuǎn)往事,留下太多的迤邐遐想的傳說。
左右頁圖:百年時(shí)光過去,滄海已變桑田,江上的烏船依舊,但號(hào)子卻已漸漸消逝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巨龍的食道
烏江,源出貴州高原威寧縣境內(nèi)的烏蒙山麓,古稱延江或黔江、巴涪水,是長江水系最大支流之一。流經(jīng)川黔46個(gè)縣市,至四川涪陵注入長江,全長1036公里。流域面積80814平方公里。烏江奔騰于大婁、武陵山脈之間,氣勢磅礴,峽灘踵接。兩岸奇山對峙,江中礁石嶙峋,波濤洶涌,素有“天險(xiǎn)”之稱。
烏江水源充沛,流區(qū)物產(chǎn)富饒,自古以來為川東與黔東北的重妥運(yùn)輸紐帶。秦國大將司馬錯(cuò)曾率巴蜀將士十萬,自烏江溯舟,取黔中郡,這是烏江航運(yùn)最早的記載。隨后劉備稱帝于蜀,公元前140年,漢武帝置涪陵縣于今郁山鎮(zhèn),把涪陵縣上升為郡一級(jí)治所。晉控制蜀漢以后,準(zhǔn)備進(jìn)攻吳,又將烏江航運(yùn)繼續(xù)向上延伸。明、清以來到民國初年,烏江沿岸先后有商民捐資,鑿灘疏淺,以興鹽利。
如果說長江是一條蜿蜒的巨龍,那么烏江就是巨龍的食道。郁山的鹽丹,思南的桐油,石阡的生漆和德江的木材等,都順著這條食道涌入龍頭重慶。“裝不完的郁山,塞不滿的重慶”說的便是當(dāng)時(shí)的情形。
烏江作為抗戰(zhàn)生命線,那時(shí)也是航運(yùn)最鼎盛的時(shí)期,烏江上同時(shí)漂著百種以上的木船,“古藺船”、“金銀錠”、“墮籠子”、“黃瓜皮”、“麻雀船”……不一而足。其中有僅載重幾噸的“小蝦爬”, 也有能載二百多噸的“八大櫓”。有用楠竹做成,前頭溜尖,船脊翹得高高的,后面撒開像只孔雀,跑起來速度奇快的“楠船”。也有四四方方,專載重料,跑得像烏龜一般的“大料船”。
川、湘、貴號(hào)子的混血兒


船雖分大小,但船上的分工則大體相似。地位最高的是前后兩位駕長,前駕長一般是最有經(jīng)驗(yàn)的老船工,負(fù)責(zé)選擇航路。他們要有熟知風(fēng)向、辨別水位多大、何處是暗礁和石頭的本事。后駕長掌舵,一般由沉著穩(wěn)重“舵感”細(xì)膩的人擔(dān)任,關(guān)鍵時(shí)刻,他手上握著全船人的性命。槳工和櫓工的頭領(lǐng)叫做橈頭,也是個(gè)重要人物,發(fā)現(xiàn)有人不使力氣,他就破口大罵。除此之外,船上還有一個(gè)極重要又江上特色的工種:號(hào)工。
號(hào)工,又名“開口”,職責(zé)便是領(lǐng)喊號(hào)子。烏江上的號(hào)子來源沒有詳盡的歷史記載,只有一些民間傳說。說是魯班發(fā)明了船,最開始是用手劃水帶動(dòng)船前進(jìn),可是船行灘多浪急的烏江時(shí)手劃遠(yuǎn)遠(yuǎn)不夠,魯班撿到一節(jié)樹枝,以枝代手,才發(fā)明了搖漿。他看到江岸牧童牽牛的情景,又叫他的弟子趙巧上岸,仿照牧童拉牛的姿勢去拉船,弟子很不高興,邊拉纖邊哭訴著自己的不幸,這勞動(dòng)中的哭聲,相傳便是最早的烏江號(hào)子。
根據(jù)這些傳說,我們可以推想烏江號(hào)子的誕生歷程:最早烏江上的先祖?zhèn)兂嗌砺泱w,艱難地?fù)u著木船或是背負(fù)著沉重的纖繩,終年累月地爬伏在烏江的狹窄古道上拉纖。他們頭頂懸崖絕壁,面朝驚濤駭浪,為了調(diào)劑勞動(dòng)的呼吸和動(dòng)作而開始發(fā)出有節(jié)奏的呼聲,后來才逐漸有了簡明的詞句。先祖?zhèn)儼l(fā)現(xiàn)這種呼喊能使寂寞的環(huán)境變得氣氛熱烈,繁重的勞動(dòng)成了輕快的活兒,且能通過這些詞句的呼喊,指揮生產(chǎn),鼓舞勞動(dòng)情緒,提高勞動(dòng)效率。于是這種呼喊便代代相傳下去,不斷豐富,逐漸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內(nèi)容和形式,烏江號(hào)子由此誕生。
由于地處三省交界處,這些號(hào)子具有濃郁的川、湘、貴三地生活氣息和藝術(shù)特色。既有川江號(hào)子雄壯的氣魄,又有湘江玩水號(hào)子娓婉清麗的韻律,更有云貴高原粗獷野樸的山味。
左右頁圖:現(xiàn)代人只知道烏江畫廊艷極一方,卻不知道這里當(dāng)時(shí)也是吞噬江船險(xiǎn)灘密布之地。

平水號(hào)子:龍門峽中的“龍門陣”
烏江號(hào)子分平水、沖灘兩大類,風(fēng)格也是大不相同,不同的河段,號(hào)工們會(huì)選擇不同的號(hào)子鼓舞船隊(duì)。
在彭水自治縣鹿角鄉(xiāng)境內(nèi)的烏江河段,水勢和緩,風(fēng)景清幽,是百里烏江畫廊中最精華的河段之一。河的東岸,有一個(gè)石灰?guī)r大溶洞,宛如一道大圓門,自古稱之為“龍門”。龍門高約二十來米,龍門頭頂數(shù)十株古榕樹,通體披著綠色的藤蔓,景致瑰奇獨(dú)特,有著“龍門勝境”和“青城天下幽,龍門勝青城”的顯赫名頭。由于龍門的名氣很大,人們也就把“龍門”所在的一段烏江峽谷,稱為“龍門峽”。
在這種風(fēng)平浪靜的河段,號(hào)工會(huì)唱起平水號(hào)子。這些號(hào)子的曲調(diào)比較舒緩、悠揚(yáng),聲音明朗、輕快,富有歌唱性。當(dāng)然,這也是最考驗(yàn)號(hào)工肚里墨水濃度的時(shí)候。每到水流平緩的地方或下水船甩灣截角的時(shí)候,船工們便要號(hào)工“拿書來背”,于是號(hào)工全神貫注,或唱戲文,或唱順口溜。不管是苗鄉(xiāng)土諺還是志怪小說的方言新編都是信手拈來。在龍門峽,號(hào)工們最愛唱的,是一段“撞破龍門”的故事。
范堅(jiān)強(qiáng)從身上掏出一塊玉佩,反復(fù)打量,像打量一位久別的朋友。過了半晌,他把玉佩遞給一杭,說:“這個(gè)你認(rèn)得吧?”一杭從身上掏出母親臨死前交給他的玉佩,一模一樣。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期待地看著范堅(jiān)強(qiáng)。
說是很久以前,在鹿角鄉(xiāng)的大山中藏著一條巨蟒。這條巨蟒,后來修煉成仙了,變成了一條龍。在天庭領(lǐng)了個(gè)給鹿角鄉(xiāng)降雨的差事,倒也把這一方土地打理得風(fēng)調(diào)雨順。可惜工作久了,心生厭倦,想著去旅游。有天晚上,龍就給大山上一個(gè)要好的老漢托夢,說:“老哥哥,我要離開鹿角,通過烏江到大海里去看看。請你給周圍的人說一聲,明天天快亮?xí)r,務(wù)必將自家的公雞照好。不讓它叫喚我,免得被神仙發(fā)現(xiàn)。”
不料這話被土地公公聽到了,土地公公想,這還了得,龍一走,沒了雨水,鹿角山區(qū)老百姓都要遭殃,我一定得想法去制止。
天快亮?xí)r,天上突然狂風(fēng)暴雨大作,土地公公知道這是龍想遮掩自己溜號(hào)的行跡。果然,巨龍很快躲在山洪里沖出來,準(zhǔn)備溜到烏江去。土地公公看到龍來了,就伸起頸子學(xué)雞叫喚。它這一叫四面八方的公雞就一齊爭先恐后,咕咕地叫起來了。

龍聽到到處都有雞在叫喚,以為天真的亮了,心頭就發(fā)慌,忙說:“遭了,遭了!這盤還是起來晚了。”既然下不了海,為了不被天上的神仙發(fā)現(xiàn),龍就想鉆到山里躲起來。它把尾巴一甩,甩在一壁懸?guī)r上,把石壁打穿一個(gè)像龍門的大圓孔。又用腦殼朝前一拱,把前面靠烏江的那匹大山拱了一個(gè)又大又深的洞,龍就藏在山下的洞內(nèi)去了。這個(gè)洞子便是今天的龍門。
這么一段故事悠悠地唱完,龍門峽也悠悠地從身邊飄過,枯燥繁重的船上生活,也便顯得不那么難捱了。


左右頁圖:烏江隨著河段不同,水勢也完全不同,有的地點(diǎn)地方滿是驚濤駭浪,有的地方卻平靜如畫。
沖灘號(hào)子:無限壯烈在險(xiǎn)灘
當(dāng)船行離開龍門峽,來到土坨子峽、龔灘峽一線時(shí),真正的考驗(yàn)便開始了。此時(shí)灘大水急,峽與灘交響,水與石撞擊,在架長小心控制船行方向的同時(shí),號(hào)工會(huì)唱起變化多端,毫不停歇的沖灘號(hào)子。此時(shí)所有船工的勞動(dòng)工序和強(qiáng)度都靠號(hào)子頭唱腔唱詞的變化來指揮,駕長與號(hào)工就如方向盤與油門,二者的合奏必須完美而精確才能讓小小的木船在危機(jī)重重的大江上踏出一條坦途。駕長、號(hào)工指揮全局,橈工則背對船頭,循著號(hào)子的節(jié)奏瘋狂推動(dòng)橈板,只要?jiǎng)蓬^稍懈,在逆流巨大的沖力之下,輕則傷筋斷骨,重則船毀人亡。搶灘是把腦袋別在褲腰上的活兒,因此所有的人需要步調(diào)一致,齊心協(xié)力。
過這些“灘連灘,十船九打爛”的地段時(shí),通常是十余條船成群出發(fā)。每遇大灘,除了船工在水上賣力,還需集中人力下到岸邊共同拉纖。纖工們巨大的號(hào)子聲扎實(shí)鏗鏘,高亢激昂,能壓過咆哮的江水聲,遠(yuǎn)傳數(shù)十里外。這種雄壯的拉纖聲被稱為“奪奪號(hào)”,它沒有弱拍,沒有領(lǐng)唱,也沒有歌詞,只是不斷地吶喊和呼號(hào),聲音明亮而強(qiáng)烈。進(jìn)入高潮時(shí),節(jié)奏陡然加快一倍,氣氛更加熱烈。船過灘一瞬間號(hào)工一聲大吼,灘頭頓時(shí)一片歡騰。
這時(shí)船工們知道,自己又從鬼門關(guān)里沖出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