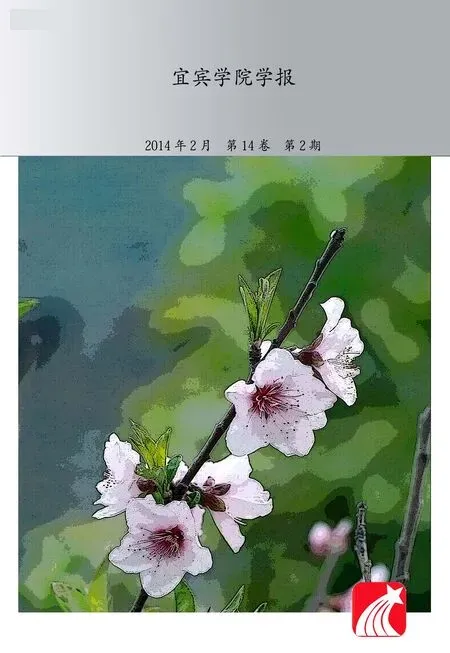馬克思早期關于人的本質論斷嬗變的深層邏輯
王 穎
(南京大學 政府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46)
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后文簡稱《44年手稿》)和《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后文簡稱《提綱》)的理論地位不容忽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1]56。
而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對這一問題的闡釋轉變為:“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135。厘清二者發生嬗變的內容、原因和支撐這種嬗變的深層邏輯有利于理解這種嬗變之于馬克思整個哲學思想的意義。
一 馬克思早期關于人的本質論斷的嬗變
(一)著眼點:從“類”到“社會”
1843年,費爾巴哈發表了《未來哲學原理》和《信仰的本質》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對于青年馬克思的影響十分深刻,同時,馬克思也給予這兩篇文章高度評價,認為它們的意義要“超過目前德國的全部著作”。在這種崇拜情緒之下,馬克思寫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時便以費爾巴哈哲學為主要出發點。此時的馬克思在論述人的本質的問題時,自然也就借用了費爾巴哈的術語“類”,將著眼點放置于“類生活”之中,提出人的“類本質”的觀點。
“類”的概念是費爾巴哈哲學中十分重要的概念,費爾巴哈認為,人與動物最大的不同在于動物沒有類意識而人有類意識,而人作為一種類存在物,其共同性可歸納為人的理性、意志和情感,同時,他還指出維系人的“類生活”的是“愛”。
馬克思首先肯定了費爾巴哈關于“人是類存在物”的觀點,認為:“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于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1]56但是,他并未止于費爾巴哈關于“類”的概念的理解,而是更進一步將人的勞動引入到“類”的概念之中,提出人的類本質在于自由自覺的活動。也就是說,馬克思認為人作為一個“類”的共同性應該在于勞動,而這種勞動是有一定限定的,即自由自覺的勞動。這樣,馬克思就在“類”的概念中加入了新的含義:一方面,“類”的共同性在于個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這里“自由自覺”指的是相比較動物而言的“普遍性”。即“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1]57具體表現在:第一,從生產目的來說,動物只能根據自己的生存需要生產,而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其它(如精神)需要等進行生產;第二,從生產的對象來說,“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在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于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1]57;第三,從生產手段來說,“動物只能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1]57另一方面,在人的自由自覺的勞動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亦形成了一種相互補充、互相依賴的關系,這種關系也是馬克思的關于“類”的重要內涵。“活動和享受,無論就其內容或就其存在方式來說,都是社會的,是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2]82-83在這里,馬克思雖然運用了“社會”一詞,但實際表達的是“類”的意思:“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絕不僅僅存在于直接共同的活動和直接共同的享受這種形式中,雖然共同的活動和共同的享受,即直接通過同別人的實際交往表現出來和得到確證的那種活動和享受,在社會性的上述直接表現以這種活動的內容的本質為根據并且符合其本性的地方都會出現。”[3]301當人所進行的活動是符合自由自覺的本性之時,它就是社會—類的活動,而隨之產生的是實際交往中體現出的相互補充、相互依賴的關系。
在《提綱》中,馬克思拋棄了費爾巴哈關于“類”的概念,并批判費爾巴哈“撇開歷史的進程,孤立地觀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種抽象的——鼓勵的——人類個體。他只把人的本質理解為“類”,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純粹自然聯系起來的共同性。”[1]135因此,馬克思轉而將著眼點放置于真正的“社會”,認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與之前關于“類”的概念相對應,這里的“社會”也包含了兩層意思:第一,處于人類歷史特定階段上的社會。這種社會是具體的,因為相比較于之前的“類”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存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1]135實踐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而生產實踐是決定其它一切實踐的最基本的活動。生產實踐是怎樣的,就決定了其所在的社會是怎樣的。處于不同的歷史階段上,生產實踐的內容各不相同,就決定了處于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有其不同的內容。這種社會也是歷史的,因為社會不僅是特定歷史階段中一定的物質結果和一定數量的生產力總和,也是歷史維度上世世代代生產力發展的積累。綜上而言,某一階段的社會亦是作為歷史發展的結果而存在的。因而,這種社會是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統一。同時,人在這樣的社會里生活,從事著生產實踐活動,必然會由此生發出一定的社會關系,這里就出現了第二層含義——社會關系。這里的社會關系與《44年手稿》中的類—社會的關系不同,它所強調的不僅是抽象的、純粹由個人所生發出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性,還是在特定歷史階段的人從事物質實踐活動時自發形成的各種社會關系。這一系列的關系群的總和,共同構成了人的本質的內容,這種社會關系一旦形成固定后,又會反過來制約人的實踐活動。由于社會是具體的、歷史的,因而這種社會關系亦包含了橫縱兩個維度。從橫向來說,是指在其所生活的特定歷史階段上以生產關系為基礎而產生的一系列關系群,包括社會關系、政治關系等,而從縱向上來說,是指繼承的前代積累起來的關系群。
如上所述,馬克思《44年手稿》時期著眼于“類”,所言“類生活”以及由此產生的相互之間的關系都是一種平面化、抽象的關系;而相比于“類”,后期馬克思所說的社會是具體的,同時也具有歷史感。
(二)出發點:從人自身到實踐
在《44年手稿》中,人的類本質論斷的出發點是人自身。即是說,類本質的論斷是直接通過對人的本質的直觀——哲學的思辨——而得來的抽象概念,是“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自然地聯系起來的普遍性”[1]135。此時的馬克思并沒有看到人的特性是人的活動的結果,而是將人的特性理解為人的活動本身,同時,這種活動是一種抽象意義上的活動,是自由自覺的,是不受當時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制約的活動,是真實歷史中所未出現過的活動。
在歸納出人的類本質后,馬克思又以此為出發點,作為衡量資本主義現實的尺度,他發現,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人類勞動的景觀又是另一副模樣:工人的勞動事實上是一種異化的勞動,這種異化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人同自己創造出來的勞動產品之間的異化。資本主義貨幣制度之下,勞動產品不再直接為勞動者所占有,而貨幣媒介的介入,驅走了人的本質,勞動產品成為人的本質淪喪的證明。第二,人的勞動活動本身的異化。“外在的勞動,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勞動,是一種自我犧牲、自我折磨的勞動”。[1]54第三,人同其類本質的異化。人的本質在于自由自覺的勞動,然而,異化了的勞動產品和勞動活動本身從根本上剝奪了人的類生活。第四,人同人相異化。人同自己生產的勞動產品之間、勞動活動本身以及人同其類本質之間產生了異化,直接導致了人同人相異化。“不生產的人”(資本家)通過貨幣關系占有了工人生產出的勞動產品,造成二者的對立異化,同時,對于“不生產的人”(資本家)而言,他占有的也僅僅是物,因而也是異化的。
從人出發,馬克思在許多個人之中抽象出了他們的普遍性,并以此為標尺,衡量出了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而這也正是《44年手稿》中馬克思批判的張力所在,而要消除理想與現實的距離,馬克思又將這一動力歸于人自身,認為只有人重新占有人的類本質,達到人性的復歸,才有可能實現所謂的真正的“社會主義”。
而在《提綱》中,馬克思對人的本質有了新的認識,出發點也由原先的人自身轉變為實踐。此時的馬克思才真正了解了人的特性是人的活動的結果。“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中社會關系的產生依賴于一定歷史時期人們所從事的特定實踐活動,人們正是在一定的歷史的實踐中產生了自己的一系列的社會關系。因此,馬克思是從實踐出發去探索人的現實本質的。
在《提綱》的第一條,馬克思就批判了舊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在于“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們當做人的感性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1]133;這樣,人在面對外部世界時是無能為力的,人是一種生物意義上的類的存在,而相反,唯心主義則“發展了能動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是不知道真正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1]133按此理解,人類的活動就僅僅局限于思維領域而不存在現實的基礎,這二者皆是片面的。馬克思重新認識了實踐的含義,他認為:實踐應當是“人類主體通過客觀物質創造表現出來的能動的社會歷史活動”。從這種意義上說,實踐表征了人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并非隨意的能動,而是受到自然條件以及一定時期社會歷史因素所制約的能動性,從實踐出發去理解人的本質,人的本質也應當是具體的、歷史的,同時與其所處的環境也表現出相互的制約性。故而馬克思在《提綱》第三條就批判了庸俗的唯物主義學說“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駕于社會之上”[1]134,并指出“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1]134實踐只有結合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才能真正地把握其實質性的內容,那么人的本質也一樣,人的本質從來就不是人的腦海中思辨的產物,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只有結合了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承認人與其所處環境的相互制約性,才能真正認識人的本質。
實踐的出發點是與社會現實生活基礎相親近的,且又保持了人類主體的創造性功能的全新哲學出發點。這無疑將人的本質重新納入到現實之中。實踐著的人是在現成的和他們自己所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中活動和表現他們自己的,同時,通過這種實踐活動,他們又改變著現存制度,推動歷史的進一步發展。如果要對人進行研究,就必須要對人所生活的現實的物質生活條件進行研究,并歸納總結出其中的規律,這樣才能對現實的人的本質給予回答。
二 馬克思早期關于人的本質論斷嬗變背后的深層邏輯轉換
(一)《44年手稿》中的理論困境
縱觀《44年手稿》,馬克思尋求人類解放的致思理路事實上走的是與費爾巴哈相似的路徑,是一種人本主義的異化史觀邏輯下的人類解放道路。這樣的邏輯思路的主要缺陷表現在:
一方面,“類本質”的設定僅是一種價值懸設。“類本質”的規定中“自由自覺的勞動”是一種本真意義上的勞動,是一般意義上的勞動,它是脫離于現實基礎的;同時,由此生發出來的維系“類”的類-社會關系,也是一種未異化的、本真意義上的關系,是一種理想中的狀態。綜合說來,馬克思這時所說的人的“類本質”并不是一種現實存在,而僅是一種價值懸設。
另一方面,“類本質”的回歸僅是一種倫理呼喚。馬克思將人的類本質的歷時性自我矛盾的運轉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馬克思以抽象的人為邏輯起點,去看待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他發現,在這種“人之應有”的理想尺度下,人的本質在現實的“是”中喪失了,而現實的“是”必須要在揚棄私有制的前提下才會與理想的“應該”相互一致。業已轉向無產階級政治立場上的馬克思開始尋求推翻資本主義的根據和途徑。于是,馬克思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共產主義,他認為,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方式在于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4]279這種共產主義也并非科學意義上的共產主義,而僅是一種倫理意義上的口號,《44年手稿》中,馬克思最終沒有能夠找出一條走向理想目標的現實的必然的途徑。
在這樣的邏輯引領之下,馬克思能做的只是如同以往哲學家一般“解釋世界”。然而,馬克思的目標在于“改變社會”,是要尋找出一條能夠達到人類自由全面發展的必然之路。要做到這一點,馬克思就必須有一全新的邏輯思路,這種邏輯思路包含主觀和客觀兩個維度:在客觀維度上,要能夠從社會現實出發,并要以現實的社會物質條件為基礎;在主觀維度上,要能夠充分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即是說在現實的社會面前,人類必須要有一定的主動性。只有做到這樣兩方面,才可能真正地喚起無產階級的使命感,才真正可能達致改變世界的目的。
(二)《44年手稿》之后邏輯思路的轉換
之后,隨著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日益深入的研究,他愈來愈發現之前那種基于“費爾巴哈式”的邏輯思路的缺陷,并愈來愈接近對現實的考察,尋找著哲學的新思路。最終在《提綱》中,重新找到了哲學新起點:歷史唯物主義。
從《44年手稿》到《提綱》,時隔不到一年,馬克思從人本主義異化史觀的邏輯框架轉向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框架,但是這種轉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正如恩格斯所說:“要從費爾巴哈的抽象的人轉到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須要把這些人當作在歷史中行動的人去研究……但是費爾巴哈所沒有走的一步,終究是有人要走的,對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費爾巴哈的新宗教核心,必須由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來代替,這個超出費爾巴哈而進一步發展費爾巴哈觀點的工作,是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開始的。”[5]334
寫于1844年下半年的《神圣家族》中,馬克思指出:“人的生存資料的喪失也就是人本身的喪失,即人的本質的喪失。因此,消滅人對自己的實物本質的實際異化關系,就意味著真正改變自己的現實存在,改變自己生存的現實條件,恢復對生存資料的占有。”[6]52此時,馬克思又提到了一個新的名詞“實物本質”——表達人對生存資料的需要與占有。“實物本質”的提出顯示了馬克思由費爾巴哈的人的自然需要轉向了人對勞動產物、生存資料的需要,這是一種社會的需要。從自然界轉向社會,決定了馬克思必然要從對人的自然本質的探討轉向對社會本質的探討,并從對費爾巴哈抽象人的崇拜轉向對現實人的歷史考察,這是馬克思后來邏輯發生變革的重要因素。
此外,馬克思還指出了消滅人對自己的實物本質的實際異化關系的途徑:“真正改變自己的現實存在,改變自己生存的現實條件,恢復對生存資料的占有。”[6]52此時,馬克思已經開始將現實的人與他的社會是生存條件直接相聯系了,認為要改變這種異化關系,需要對現實的生存條件進行真實的改變,而不是空談重新占用自己的本質了。
這種轉變在1845年3月的《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手稿(后文簡稱《手稿》)中被進一步發展了。在《手稿》中,他對勞動作了重新定義:“按其本質來說,是非自由的、非社會的、被私有財產所決定的并且創造私有財產的活動。”[4]254相比于《44年手稿》時的勞動一般的概念,此處的勞動是富含歷史意義的概念,是浸染有資本主義歷史特征的勞動,是具體的。更重要的是,馬克思對于走向共產主義道路的指認已經開始走向現實了,認為在工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人類之力量本身“將炸毀資產者用以把它們同人分開并因此把它們從一種真正的社會聯系變為社會桎梏的那種鎖鏈”[4]259。
到了《提綱》時期,馬克思的邏輯框架開始有了質的突破,從現實的人及其社會關系出發,揭示出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徹底拋棄了人本主義的思維方式,從客觀和主觀兩個維度揭示了人類歷史運動的規律以及人類走向真正解放的現實路徑。
在客觀性上,馬克思指出,人的物質存在決定了人的意識,生產力決定了生產關系,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歷史的驅動力。而在主觀能動性上,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和主人,生產力的發展有賴于人的主體實踐,在實踐的邏輯基點上,實現了客觀與能動的統一。在《提綱》的最后一條,馬克思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社會,問題在于改變社會”[1]136。而這種改變應該是從實踐的基點出發,對現實社會的真實改變。第一,主導馬克思思想的已經不再是“否定之否定”的邏輯框架,而是社會歷史實踐自身的內在矛盾運動及其解決的邏輯體系,取消了“應有”的懸設。第二,重塑現實之“能有”。現實之“能有”在于“社會化了的人類”。“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1]136,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社會化了的人類”有較為明確的解釋:個人和集體的有機統一,個人自由和社會發展的有機統一。這是根本上有別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倫理價值意義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化了的人類”是在現實私有制狀況下從事非自由活動的過程中,不斷累積著廢除私有財產的力量和可能的結果,是社會歷史現實發展的必然結果。第三,指出達到現實之“能有”的道路。馬克思真正認識到解決現實的問題,讓人走向自由的道路不在于人類從意志上擺脫異化的狀態達到自由自覺本質的復歸,而在于“改變世界”。因為現實的市民社會之所以呈現出了“自我分裂”的特性,其根源不在于人的觀念的異化,而在于現實的私有制度及其被這一制度所決定的社會物質活動之中。人類背負著社會關系的枷鎖,無論在觀念上如何理解自由、向往自由,若不能學會如何打開枷鎖是無法真正自由的。不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社會關系,僅僅通過啟發人們沉思何為自由、如何從觀念意志上趨向自由,是難以讓處于這種社會關系中的人走向解放的。因此,馬克思從人的本質的異化和復歸的人本主義走向了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這也導致了馬克思對于人的本質理解的根本變化。
總之,馬克思的思維邏輯的轉換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出發點上從對抽象的人的觀照逐步轉為對現實的人的考察,解決途徑上,從激情洋溢的倫理評價與呼喚逐步轉為客觀冷靜的歷史必然道路的指認,是一種將人的主觀能動性與歷史的客觀必然性相結合的科學、歷史的思路。
三 馬克思早期關于人的本質論斷的邏輯嬗變意義
(一)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
1845年之后,馬克思開始清算自己“從前的哲學信仰”,與一切舊哲學決裂,將自己哲學的出發點由對人的類本質的探討開始轉向對實踐和物質生產的探討。“馬克思的哲學邏輯框架發生了重大的格式塔轉換:那條從“人”的先驗主體本質出發的邏輯在總體上被揚棄了,馬克思找到了一個新的邏輯基點,這就是歷史的、具體的、現實的社會實踐。”[7]這使得馬克思主義哲學走上了與以往一切舊哲學不同的道路,將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自己的新的世界觀。
在《44年手稿》時期,馬克思是無法真正回答人的本質問題的,他對人的本質問題的探討雖然較費爾巴哈有了一定發展,能夠從自由自覺的活動的角度去看待人的本質,但由于這種勞動依然是一種本真意義上的勞動,是沒有歷史感與現實感的勞動,是一種抽象的勞動,所以,其所歸納出的人的本質也是抽象的,沒有歷史意義的人的本質,人為地將人與其生活的世界相互割裂了。從根本上說,馬克思仍然是將抽象的人的某種屬性代替了現實的人的真實存在。只有在改變其基本的世界觀立場之后,走上了歷史唯物主義之時,他才真正開始了對現實的人的考察,只有將人與其生活的世界看作一個基于實踐而整合起來的有機整體,才能真正認識在一定階級和歷史條件之下的人,而人的本質正是在其生產實踐所形成的社會關系中體現出來的,這才真正地回答了人的本質之問。
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全新的世界觀。歷史唯物主義要求以實踐為基本出發點看待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從而擺脫了舊哲學對于現實世界僅是“感性的直觀”之窠臼,使得馬克思主義哲學可以真實地解釋世界,也為馬克思哲學之“改變世界”提供了可能性。
(二)走上了“改變世界”的道路
馬克思自始至終都在為尋求人類解放之道而努力。在《44年手稿》時期,他發現了理想的人的類本質與現實中勞動異化之間的差距,激發了馬克思的批判力。在人本主義異化史觀的邏輯下,他指出了只有揚棄私有制,達到人的本質的復歸,才有可能真正地實現共產主義。此時的他將歷史前進的動力寄希望于人自身。這樣的道路顯然是一條虛幻的道路,因為他脫離了具體的歷史,將人懸置于沒有歷史和社會的真空之中,這只是一種美好的愿景,這種共產主義只是倫理口號。然而,當馬克思轉向了唯物史觀的邏輯框架后,他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便轉向了對現實道路的指認,他了解到生存于現實社會之中的都是一個個“現實的人”,是具有一定歷史制約性的,并非歷史前進的動力,而歷史發展的最終動力應該是生產力的發展。故而馬克思將研究的對象轉向了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揭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隨著生產力發展會被新的生產關系所替代的歷史必然性,而在這種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運動中,人類社會必然走向共產主義。這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從此走上了一條與以往一切舊哲學相區別的道路。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馬克思.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單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 張一兵.關于馬克思哲學邏輯轉換中的三個難題的深層解決[J].江蘇社會科學,19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