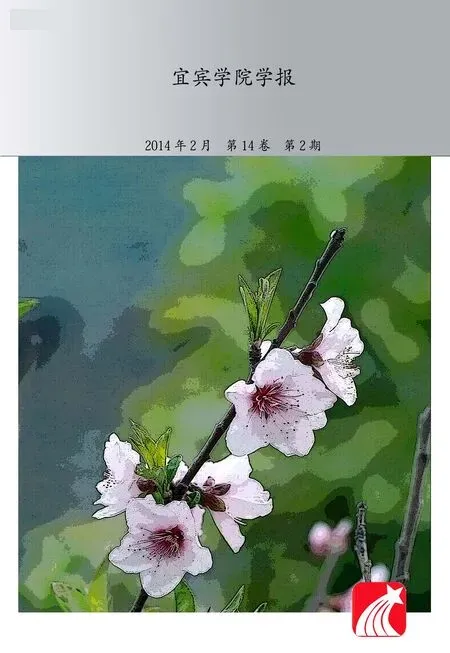裴斯泰洛齊的社會工作理論及其啟示
黃依依
(四川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5)
一 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與對西方社會工作理論的借鑒
在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代背景下,社會轉型和現代化進程為中國社會工作發展提供了歷史性機遇,并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趨勢。改革開放初期,面對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改革所帶來的新問題、新矛盾,中國社會工作的探索始于對西方社會工作理論和實踐的引進和吸收,尤其關注以美國為中心的社會工作實務理論體系,將社會工作置于社會學的框架下來研究,并致力于社會工作實務的學習、傳承和研究。我國社會工作的開展,多以“問題的產生”作為出發點,力求以“解決問題”作為核心任務和工作目標。毋庸置疑,這種“問題解決式”的社會工作理論對于當時正處于社會工作萌芽時期的中國內地來說是一劑良藥,它正好能應對那個特定的改革時代里社會問題數量較少、性質較為單一的社會狀況。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整個社會大環境日趨復雜多變,社會矛盾、沖突不斷涌現,使這種帶有嚴重的滯后性的社會工作理論,難以應對當前社會的發展需要,這就對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阻礙。在這樣新的社會背景下,就迫切需要一種新的理論來填補我國現有社會工作理論體系的空白,現在,我國學者找到的是盛行于歐洲尤其是德語國家,但卻被我們長期忽視的以“預防”為核心價值理念的社會工作理論。
歐洲學者認為,社會工作本身也是教育學,是一個“人影響人”的過程,因而,他們將社會工作歸入社會教育學,作為它的一個分支。而這種預防性的理論也是在教育學的脈絡下成長和發展起來的[1],主要探討如何采取各種措施以預防和減少社會問題的出現。預防性社會工作分為三級:初級預防是創造良好的環境、避免可能出現的沖突;二級預防是在可能產生社會問題的環境中防患于未然;三級預防是在危機發生之后的介入,以避免次生危機的出現。其代表人物之一為德國社會教育學和社會工作學家約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齊,本文立足于分析裴斯泰洛齊的社會工作理論并探討其對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的啟示,從而為中國社會工作理論的發展提供新的視角,推動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進程。
裴斯泰洛齊的主要研究對象和研究興趣集中在兩方面:一方面,他關注哲學問題,試圖探索人及人類社會的本質,從而為其后教育學思想框架描繪出了一個理想目標,即在現有社會背景下,要把人培養成何種狀態的人,同時在此過程中,不斷改變現有社會環境和條件以更有效地方式達成其教育目標,最終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狀態。另一方面,又致力于政治學和教育學問題的研究,他把現有的政治學和教育學問題歸結為人的教育的問題,其試圖深入探討和研究如何建立一種有效及科學的社會政治體制以推動教學領域的發展,同時,教育的發展反過來又能促進政治學及其領域的改革和科學化。另外,由于早年的孤兒教育實踐,他尤其關注貧民教育問題,再加上后來創辦了帶有教師培訓的教育機構,因而其一直在潛心研究和實踐:如何進行貧民教育?如何通過建立簡單的機構來實現貧民教育?裴斯泰洛齊在后來其系統的理論介紹和闡述中,一一體現了他這兩方面的關注興趣。他的社會工作理論研究分為人類學、教育學和政治學等,本文主要立足于探究這一理論在教育學觀點方面的借鑒意義。
二 教育學觀點對家庭和學校社會工作的借鑒意義
(一)教育的出發點
裴斯泰洛齊認為所有教育的出發點都為孩子“未腐朽”的自然天性,以“教育應適應自然”為原則,確立了教育的目的在于發展人的天性和形成完善的人,使人的天賦、能力能得到全面的、和諧的發展,使之長成為有智慧、有德行、身體強壯、能勞動并有一定勞動技能的人[2]。在《天鵝之歌》中,裴氏這樣寫著:“依照自然法則,發展兒童道德、智慧和身體各方面的能力,而這些能力的發展,又必顧到它們的完全平衡”[3]。裴斯泰洛齊認為“好的教育方法只有一種——這就是那種完全建立在自然的永恒法則基礎上的教育方法。”[4]當前中國家庭社會工作,從廣義上講它是涉及衣食住行、心理建設、健康醫療、法律援助等方面的龐雜體系,而對應的服務提供者有政府機構、群眾性團體與非政府組織,如民政、勞動和社會保障、醫療部門、各級婦聯、民間組織等,他們各自帶著本行業的工作價值觀與工作方法參與到家庭社會工作中,使家庭服務呈現出不同的特點[5]。專業家庭社會工作也在近年來逐步運用專業社會工作理念和方法加入到家庭服務的行列,但由于中國整體社會福利狀況較低,在中國內地大多數地區所進行的家庭社會工作大都是一些應急或修補性的,關注于對家庭問題的及時解決,卻忽視了在這個過程中對家庭中孩子的天性的尊重,常常為了盡快解決家庭矛盾,而讓家庭成員各自妥協讓步,難以周全考慮孩子在成長期所應接受的“自然養成”。這種忽視在一些對特殊家庭的社會工作中體現得更明顯,如單親家庭、留守家庭等,這類家庭更迫切需要解決一些應急困難,而難以關注孩子天性問題。
而中國當前的學校社會工作常常與“思想政治教育”或“學生管理”等聯系在一起,其特點主要體現“在思想政治教育與管理相結合,以班級為單位,在教育上注重灌輸;在管理上強調規范,以班主任、輔導員為主,強化班級建設,采取抓兩頭促中間的措施,解決學生的問題。”[6]這一貼有強烈政治標簽的工作模式,泯滅了學生的天性,使其能力和天賦難以在成長中得到盡可能全面平衡的發展。
這種中國式家庭與學校社會工作的缺失,就需要裴氏理論來填補。首先,在介入之前,我們應將孩子的天性列入對整個工作背景的考察中,在制定介入方案時,注重對孩子天性的保護和開發;其次,在介入過程中,切實維護孩子天性,并有意識挖掘可以激發孩子自然個性的介入措施,鼓勵其自我有效發展;再次,在介入基本完成后,對孩子天性在整個介入中受到的影響進行認真評估,及時發現介入中的問題,總結經驗,為下一步工作的開展做好鋪墊。最后,在整個工作完成后,對孩子天性的發展進行后期跟蹤,檢驗介入效果,及時改進不良影響。
(二)教育的方式
在裴斯泰洛齊看來,所謂教育,就是通過使用恰當的方式方法,以充分發揮人類自然和天性中所固有的力量和潛能。可見,教育的宗旨就是去發現和激發一個孩子的自我發展力量和潛能,提倡“幫助我,自己做”,這與蒙特梭利在其改革教育學中的觀點不謀而合。從另一個角度我們也可以理解,教育也是一種助人自助的方法,而這一精神也是社會工作的本質核心。這一觀點同樣可以融入當前中國的家庭和學校社會工作中。
在當前中國社會教育中,我們對孩子都有一系列硬性的指標和要求,力圖將孩子培養為一個符合社會大眾標準的“好孩子”,而這一觀念本身就忽視了孩子的獨特性,抹滅了其成長發展的天性,遏制了個性的發展。因而,借鑒裴氏理論,中國的家庭和學校社會工作就應該將“注重每個孩子的獨特性,最大可能激發其自我發展力量和潛能”作為工作目標,打破現有的社會成見,與教學領域聯手推動整個社會教育觀念的改革。另外,在發掘和培養孩子潛能的過程中,注重培養其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即家長和學校為孩子的成長提供大體框架上的幫助,而非去直接解決孩子的問題,讓其在此過程中獲得自我成長的能力,真正有效完成其社會化。
(三)教育的核心
裴斯泰洛齊提出教育的出發點源于孩子本身,愛和信仰,“愛”的教育是其道德教育的本質核心,道德教育的本質任務在于喚醒和促進兒童“愛”的種子的發展,培養他們對人們的愛,最初愛自己的父母,進而愛兄弟姐妹,然后擴展到愛上帝、愛人類。
在當前的中國家庭和學校社會工作中,我們將重心放在了對問題的介入和解決上,致力于從問題的成因上找到開展工作的突破口,在工作開展過程中剛性較強,而忽略了對家庭和學校工作的情感建設。針對這一問題,我們可以考慮將“愛”的觀念引入家庭和學校社會工作,在家庭和學校生活的各個方面,讓“愛”貫穿始終,讓孩子看到愛的相互性,即注重強調對家長和老師教育方式的改良,讓其以身作則,用其在日常生活中體恤和愛他人的示范行為,使孩子在潛移默化中產生一定的道德情感,然后利用這種情感教會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觀察他人的痛苦與憂愁,并給他人以關心和幫助。于是愛和信任的感覺也就通過自身的實踐擴大到家庭和學校生活的全部領域,營造出了一種“愛”的氛圍,從而也就避免了很多家庭和學校生活問題的出現,或者使問題更容易解決。
(四)教育的目的
裴斯泰洛齊強調要將勞動與學習相結合,將教育的目的歸結于培養孩子的工作能力、傳授和學習知識以及接受道德教育,從而使孩子能在這三個方面得到有效地完善和發展。
在當前中國教育中,受各類門檻考試的影響,教育以應試作為其首要目的,以高分作為衡量學生能力的標尺,卻未能注重對學生實踐動手能力的培養。而社會工作在介入中國家庭和學校生活中,也礙于當前考試體制的限制,而較少涉獵將知識傳授與實踐參與相結合的內容。但近年來,隨著社會對“高分低能”現象的重視,人們開始嘗試以實踐教育來彌補應試教育的缺失,如國家正大力倡導的職業教育等;同時,社會逐漸提升了對學生實踐能力的考察。在這一大背景下,社會工作應將這一內容納入實際家庭和學校工作中,如切實結合中國國情,參與到課堂教學和課下輔導工作中,與教師和家長一道輔助孩子更好地吸收科學知識,同時加入對應的技能訓練。既使孩子能通過實踐操作加深對書本知識的領悟,同時也使孩子的動手能力得以充分的提升。具體操作方法可以為一對一的個案輔導、多人參與的興趣小組或是形式多樣的社區活動。從而以充實和豐富中國社會工作的內容,促進其長遠發展。
三 教育學觀點對反貧困社會工作的借鑒意義
針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教育,裴斯泰洛齊認為,雖然貧民接受并得到了收容慈善機構的幫助,在機構里生活改變了其原有的生活境遇,使其獲得了良好的生存環境和發展可能,但其終究得回歸到社會中,于這些貧民來說,就是又返回到其接受幫助前所生活的貧困環境中,因而其已經得到的改變瞬間消失,從根本上說他們并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的幫助。面對這種情況,裴斯泰洛齊認為慈善機構應該去教會貧民如何面對貧困,雖然無法改變其作為貧民和窮人的這一社會分層事實,但窮人應被教育為窮人,應學會怎樣以窮人的身份在社會中生存和發展。可見,裴斯泰洛齊的理論中關注到了慈善機構在對貧民等弱勢群體幫助上局限性,即其幫助只在其機構環境內具有即時的改善效應,而缺乏對長期持續發展的影響和推動。
而在當前,中國的慈善福利機構等對弱勢群體的幫扶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由于體制機制以及執行力度上的困難,中國的扶貧扶弱存在僅著眼于表面功夫和政績業績上的問題,而忽視了對弱勢群體長期發展上的考慮。因而,需要社會工作對這一方面進行介入,一方面,在機構內教會弱勢群體自我成長發展的知識和技能,幫助其樹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觀念,有信心參與到社會生活和社會競爭中。另一方面,在機構外,為其提供社會支持網絡,尤其是注重推動社會政策的改革,將各項惠民利民措施用社會工作專業知識的予以包裝,從而增強其推動實施的執行力。
結語
在中國內地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面對急劇變化的社會,中國引進專業社會工作是必要的和必然的。對當今中國來說,首先要梳理和認清社會工作理論發展的脈絡,從其根源入手有效地理解其各類理論的內涵和高度。因此,我們就不應僅僅局限于吸收以美國為代表的社會學分支下的社會工作理論和方法,更要開拓視野、兼容并蓄,多方面吸收有利于我國社會發展的社會工作理論,以裴斯泰洛齊為代表的歐洲社工理論便可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借鑒,希望國內學界對此多予關注和研究。
參考文獻:
[1] 張威. 社會工作基礎理論探究——一個學科構建的新視角[J]. 中國社會工作研究(第9輯),2012(9):99-135.
[2] 吳值敬. 裴斯泰洛齊教育思想述評[D].揚州: 揚州大學, 2009.
[3] 張煥庭. 西方資產階級教育論著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4] 裴斯泰洛齊.裴斯泰洛齊教育論著選[M]. 夏之蓮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2001.
[5] 韓麗麗. 家庭問題和家庭社會工作的介入[J].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2):98-102.
[6] 胡凌霞. 我國學校社會工作的本土化研究[D].蘇州: 蘇州大學, 2008.
[7] 黃耀明. 落地生根: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與基礎理論建構[J]. 社會工作, 2013(5):7-12.
[8] 李素菊. 從國情出發,走中國式社會工作發展道路[J].社會工作與社區研究,2010(1):51-62.
[9] 李曉光. 試析德國的社會教育學[J]. 成人高教學刊,2000(5):61-63.
[10]裴斯泰洛齊. 林哈德和葛篤德:上卷[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11]王思斌. 試論我國社會工作的本土化[J].浙江學刊,2001(2): 56-61.
[12]楊漢麟,陳崢,楊佳. 論裴斯泰洛齊愛的教育及其現實意義[J]. 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3): 61-65.
[13]De Guimps R, Pestalozzi. His Life and Works[M]. New York: Pelton & Company, 1890.
[14]Gabriel C. Pestalozzi and Elementary Education[M].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07.
[15]Kate S, Pestalozzi. The Man and His Work[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