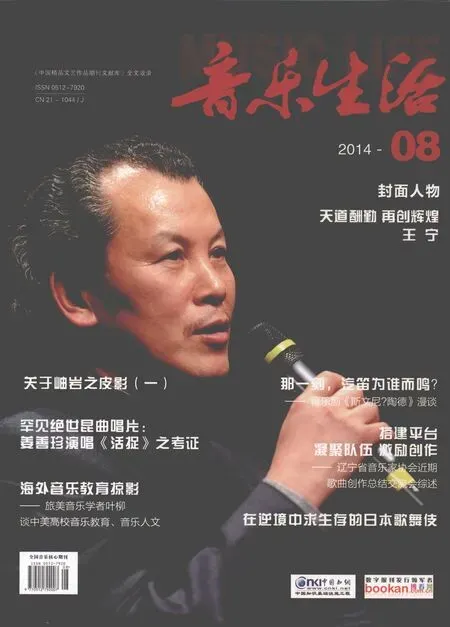重復與變化
——如何在重復的樂段中保持演奏的動力性
文/楊小影 樊禾心
重復與變化
——如何在重復的樂段中保持演奏的動力性
文/楊小影 樊禾心
音樂是一種用來表達人類內心情感的藝術形式,缺乏動力性的音樂是無法打動人們并引起共鳴的。演奏者能否使音樂充滿動力性,是衡量其演奏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標志。 本文從鋼琴演奏的角度,比較了不同的演奏版本,歸納了二種在重復樂段中保持音樂動力性的方法,即彈性節拍Rubato的設計和增強戲劇化對比,以期能使學生在鋼琴學習中逐漸提高音樂處理及作品分析的能力。
演奏重復 樂段 動力性 戲劇化 副旋律
1.何謂動力性,其地位及重要意義
“動力性”一詞常常出現在作品分析與音樂創作中,它是一種能使音樂具有凝聚力并推動音樂不斷向前發展的力量,是音樂性格中最富活力的基本特征之一。演奏者在賦予樂譜生命(即二度創作)的過程中,能否使音樂充滿動力性是衡量其演奏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浩瀚的鋼琴音樂文獻中,不乏優美的、能叩擊人心靈的樂章,一個個如珍珠般精致璀璨的樂句在音樂的海洋中熠熠生輝。但當一個相同的樂句連續重復四遍以后怎樣保持其動力性呢?這就是本文將要探討的問題。大多數演奏者靠自身的音樂本能或樂感來解決這一問題,但每個人由于情感體驗、審美標準、個性氣質、文化底蘊的不同,其音樂本能是有差異的。因此我們不能憑本能來處理音樂,還需要有所綜合、布局,通過理性的分析、設計來補充和完善我們的演奏。本文將從鋼琴演奏這一角度入手,對彈性節拍Rubato的設計、增強戲劇化對比進行分析,比較不同的演奏版本來討論如何在重復的樂段中保持音樂的動力性,以期能使學生在鋼琴學習中逐漸提高音樂處理及作品分析的能力。
2. Rubato的設計
Rubato常被翻譯為“彈性節拍”或“自由速度”,字面意義為“被劫持”,指有控制的靈活速度,有些音符的長度因速度略為減慢或略微加快而有所增減。在浪漫主義時期它被大量運用于表現音樂中速度的彈性伸縮,通常分為以下兩種情況,“第一種是獨奏聲部使用彈性速度,其他聲部(伴奏聲部)照正常的速度演奏。第二種是全部聲部同時用彈性速度演奏。現在一般通常指第二種而言”。速度上的延遲或收緊等細微的變化,打破了節奏中時值組織的規律性,這種不規律的出現能給聽眾造成對規律性的期待,從而產生強烈的推動力,使音樂充滿了動力性。
Rubato是音樂表演藝術中的重要處理手法之一,源于人們抒發內心情感的需要。我們不能將Rubato簡單等同于拖拍子煽情,拖拍子將破壞音樂的動力性。下面以肖邦的#c小調幻想即興曲op.66中的B樂段為例,這個樂段的主題旋律帶有夢幻般的情調,充滿對未來的憧憬和希望,一共連續重復了四遍,下面通過對霍洛維茲、阿什肯納齊、博列特等人演奏的版本進行比較,讓我們學習一下他們是怎樣巧妙地在演奏中運用Rubato來保持音樂的動力性的。
Rubato往往出現在樂句的結束處、新樂句出現之前,如第49-50小節,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在此處漸慢并伴隨漸弱,但漸慢的程度和范圍有所不同。阿什肯納齊在第49小節的第三拍裝飾音處開始漸慢并持續到第51小節第一拍出現之前;博列特的漸慢出現得更早些,在第47小節最后兩拍8分音符漸強并伴隨漸快的推動下,這個樂句走向頂點,隨后于第48小節開始逐漸放慢速度直到這個樂句結束。 到第51小節時,B段的主題旋律第二次出現,李云迪演奏的版本給予了這個小節充分的Rubato。在左手伴奏聲部平穩的進行下,右手第一拍A音延遲出現,第三拍8分音符顫音時值延長,接下來的第四拍做stretto.處理,并輔以漸強到第52小節這個樂句的最高音A音,展現出一唱三嘆的語氣。阿什肯納齊在第52小節這個A音上作了細微的延長,隨后第53小節回到原速,并在裝飾音處再次拉寬,給予樂句充分的呼吸。
第59-62小節是一個補充樂句,在強(forte)力度背景下出現。
突強sf出現之前,阿什肯納齊在力度、速度及語氣上均作了提示,預示著補充樂句的出現。第60小節C音是這個樂句的最高點,經過一個華彩性的片段,樂句逐漸引出主題樂句的第三次重復。阿什肯納齊在演奏這個華彩性片段時,在力度上如譜所示用了強奏,但在速度上并沒有像七連音應有的速度那么快,這種力度、速度一直保持到句末pianissimo(pp)記號出現。他在此時(第62小節)變換了音色,并在最后八分音符三連音處稍微放慢速度,使得隨后出現的主題樂句(第三次出現)與前兩次形成鮮明對比,色彩更朦朧。博列特的處理與之完全不同,他一開始就果斷地進入補充樂句,沒有絲毫的猶豫,卻出人意料地選擇在第60小節華彩性片段處采用pianissimo的力度,并放慢速度,一直到B段的主題旋律第三次出現。 B段的主題旋律從第63小節開始第三次出現,此時大家似乎都覺得如果再沒有變化,音樂就太枯燥乏味了,因而都各顯神通地使音樂更顯趣味性:除了音色有變化外,在裝飾音的處理方面,阿什肯納齊、齊夫拉和博列特的演奏都著重突出裝飾音的旋律性,使之更具歌唱(cantabile)性。到第72小節七連音的華彩性片段再次出現時,齊夫拉和博列特的版本在此處都有即興發揮,使這個片段更加華麗,將Rubato的即興性質表現得淋漓盡致。霍洛維茲的演奏總是出其不意的,他將這個華彩性片段彈得更像不占時值的裝飾音,幾乎是蜻蜓點水般一帶而過。但他并不摒棄給旋律加花的手法,在第77小節(B段的主題旋律第四次出現),他將右手的四分音符作了裝飾性處理。隨后,B樂段緩緩走向尾聲,為了突出A樂段再現時的主題形象,第80-82小節作為承上啟下的部分,大家在這里做了漸慢和漸弱的處理。 他們在掌握時值的彈性時都遵循著一個重要的原則,那就是“在一定范圍內整體上保持樂譜基本速度的前提下其中各個單位的拍速可稍有不同的變化”,而他們對這些變化的不同處理,則形成了不同的演奏風格。
3.增強戲劇化對比
無論是跌宕起伏的力度還是斑斕奇幻的色彩 ,都是音樂動力性的重要表現形式。因此,鋼琴演奏的動力性還體現在演奏者對速度和力度的安排、踏板的運用以及觸鍵方式的變化上。在音色與力度等方面做出戲劇化對比是鋼琴演奏中常見的處理方式。下面我們以肖邦的#c小調圓舞曲op.64 no.2為例,看看鋼琴大師們是怎樣在重復的樂段中保持音樂的動力性的。
霍洛維茲帶給音樂界的震撼是空前絕后的,小澤征爾曾說:“音樂最微妙的地方是能牽動人內心各種不同的感覺。霍洛維茲彈出的音樂,就是如此微妙、讓人心動。”音樂在他那富有魔力的指尖下充滿了生命力。當這首圓舞曲進入第33小節時,B樂段(c+c1)第一次呈示(B樂段的兩個樂句c+c1在樂曲中共原樣重復了六遍),霍洛維茲首先從音色上同前面樂段形成了對比,色彩變得朦朧、夢幻,仿佛以倒敘的方式講述著娓娓動人的故事,到第49小節(c+c1第二次出現)時,音色才逐漸明朗起來。大多數鋼琴家如基辛、普列特涅夫演奏的版本在這個樂句上有相反的處理,他們在樂句呈示時的觸鍵清晰利落,而把音色的變化安排在樂句后面的重復或再現時:基辛在這兩個樂句第一次反復時(第49-64小節)采用了弱音踏板,使c+c1樂句的兩次出現形成明顯的音量及音色的戲劇化對比;普列特涅夫把音色上的處理放在了樂段后面的再現處(第113小節和第177小節),形成一種轉折語氣。
踏板的應用簡潔是霍洛維茲演奏版本的另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他在c+c1樂句第二次出現時幾乎沒有使用踏板,使這兩段相同的音樂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音響效果。
霍洛維茲對樂曲最后再現段落的處理顯得戲劇性十足,他在最后B樂段再現部分(c+c1樂句第六次原樣重復)采用了明顯更快、更頑皮的速度來結束全曲,讓人印象深刻。基辛在進入B樂段再現部分的頭兩小節(161-162小節)時沿用了前面A樂段結束時漸慢以后的速度,之后再逐漸漸快至原速,并伴有適當的Rubato彈性節奏。王羽佳演奏的版本有類似的處理,只是她處理得更夸張些,在A樂段再現部分結束后進入B樂段再現部分時,她沒有立即回到原速上,而是經過了整整8小節的逐漸加速,直到c1樂句出現時才回到原速上,悠然自得的速度使樂句得到充分的呼吸,聽起來別有一番風味。普列特涅夫演奏的版本在速度的處理方面相對穩健些,沒有使用過多的彈性節奏。
鋼琴大師們雖然在音樂處理手法上各有千秋,但他們在展現其獨特的音樂性的同時都緊緊掌握著音樂的邏輯關系,使音樂像小說般首尾呼應,樂句結構清晰明朗,沒有絲毫過分夸張的煽情,一切恰到好處,形成了獨具魅力的個人風格。
[1]汪啟璋等編.《外國音樂辭典》[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1988年
[2]林勝儀編.《新編音樂辭典樂語》[M].臺灣:美樂出版社2008年
[3]施詠.《基本樂理的文化視野》[M].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
楊小影(1980—)女,四川音樂學院講師。 樊禾心( 1964--)女,中國音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