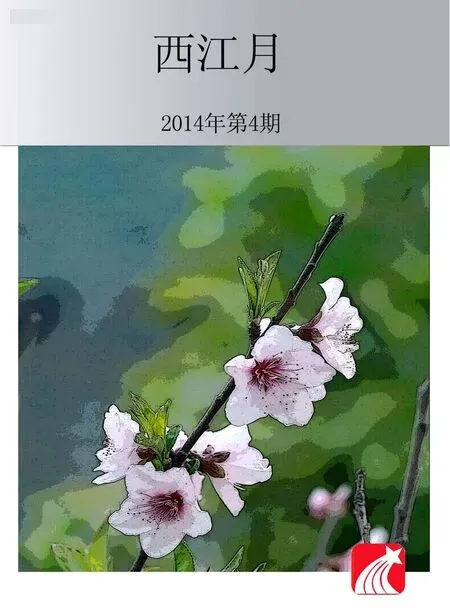許雪萍:寫詩是為了內心的幸福
鐘世華
文學意味
許雪萍:寫詩是為了內心的幸福
鐘世華

許雪萍近照
許雪萍,女,1976年生,廣西西林人。其以詩歌及散文創作為主,筆觸貼近自然及生活,作品散見于《詩刊》、《民族文學》、《廣西文學》等雜志,著有詩集《河水倒流的聲音》、《廣西當代作家叢書?許雪萍卷》,2008年獲得第三屆廣西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花山獎”。
“希望通過寫詩獲得豐富的內心經歷”
鐘世華(以下簡稱鐘):你寫詩已經有多少個年頭了?
許雪萍(以下簡稱許):寫詩應該是從1994年開始吧,那時候我還在讀書。之后斷斷續續地寫,有時兩三年一首詩也沒寫,很松散的狀態。
鐘:你詩歌的啟蒙老師是誰?
許:最早的啟蒙老師,應該算我初中時的語文老師,他常常把我的作文當范本讀。后來,我遇到蔣菁蕖老師,他是廣西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著名的詩人之一。當時他在學校當老師,并負責校園文學社,他自己開詩歌課,邀請廣西作家來學校講文學課。我想他給我的影響最大。我開始在《右江日報》上發表詩歌、散文,后來又成為學校文學社的負責人之一。我父親也算一個吧,他當過中學老師,教政治和數學,但是他很喜歡文學,我最早接觸的文學書籍,都是他年輕的時候買的。
鐘:參加文學社,對你的創作影響大嗎?
許:對那個時候的我,影響很大。學校當時在澄碧湖附近,離城區比較遠,每次城里的大學有文學講座,文學社都組織我們去參加,十幾個人,騎著自行車去,浩浩蕩蕩的。現在,我偶爾想起當時的情景,眼前馬上會浮現這樣的畫面,一群稚氣未脫的人,在月光中邊騎著自行車,邊高聲地談論、唱歌,風呼呼地掠過耳邊。青春時代因為有對文學的愛好、憧憬,有對文學單純的夢想和癡迷,回想起來真好。
鐘:請談談你在魯迅文學院學習的感受。
許:魯迅文學院去過兩次。一次是1998年,偶然的一個巧合。給我留下最深刻的感受是,我第一次讀到了外國詩歌,是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博爾赫斯詩集,藍灰色的封面。我記得當時讀到他寫的《雨》,內心有一個聲音在應和:“啊,是這樣的啊,原來是這樣的。”詩歌的魅力,超越時間和空間,打開了一扇視野的窗口。另外一次是2009年,去參加魯迅文學院高級研討班。印象最深的是院長的開班詞:如果你來這里學習,有一位老師的某一句話擦亮了你思想的火花,那一切就值得了。
鐘:那之前你主要讀的是哪些作家的作品?
許:在縣城,主要去縣文化館閱覽室閱讀。《詩刊》、《人民文學》是常見的刊物。我喜歡過大解、娜夜、白連春、沙戈的詩。
鐘:詩人是善于發現常人所不能見的,對你來說,生活是否時時充滿驚奇?你容易對生活中的哪些細節感動?
許:是的,我愿意對生活保持驚奇感。也許我們周圍的事物看起來都恒常不變,但是其實一切都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不劇烈,需要用心去感受。現實生活需要規矩和次序才能繼續,但是內心生活不需要。內心生活可以活躍、自由和跳躍。我容易對那些掙扎并從容成長的事物感到震顫和贊賞,覺得他們的力量超乎想象。
鐘:西川曾說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人要是不寫詩,可能就有病了;到了九十年代,如果有人在寫詩,那真的是有病。對于在九十年代寫詩的你,理想和現實存在著怎樣的差距呢?
許:那種大語境,對我沒有影響。也許是因為我在一個遙遠的地方、閉塞的地方。寫詩,除了寫和詩,沒有其他雜音。現實和理想的差距也沒有。我寫詩的初衷,并不是憧憬詩歌將會給我帶來什么,而是有一天,我偶然推開了詩歌這扇門,我走進了一個像夢境一樣的世界,這個世界看起來有邊界,其實并沒有邊界,因為你越有知,邊界越在擴展;你越有知,越明白自己的無知。我希望這種無知延續,讓自己獲得豐富的內心經歷,直到生命的盡頭。
鐘: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新詩發展出現了重大的變化,詩歌的生存語境和生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新詩也面臨著從未有過的尷尬與困境。你是那個年代的經歷者,請談談當時廣西的詩歌環境。
許:也許我在體驗語境這方面,始終是一個感覺遲鈍的人。當然,不能說我完全沒有感受到詩歌在時代中的遭遇。但我更愿意用感受尷尬和困境的能量,去感悟生活、感悟詩歌。在廣西,我知道有很多詩人還在默默寫詩,默默寫著就會讓那種氣息一直存在。
“寫詩讓我發現生活表層下豐富的美”
鐘:一個詩人的精神成長往往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你的童年是在那勞村度過的,也寫過一首《那勞村》,請談談你在那勞村的童年生活。
許:從出生到五歲多,我一直在那勞村生活。那是一個近百戶人家的大村子。村里的房子這家的前院和那家的后院是連在一起的。人與人之間關系和睦、親密。我家院子里有一棵特別高大的石榴樹,晚上人們就聚在那里聊天。他們大多不識字,但都是天生的完美的講述者。我的童年伴隨著鬼和神的故事,伴隨著一種隱秘、神秘的氛圍。
我家旁邊的一個老宅子,是廣西乃至西南地區都有影響的土司建筑群岑氏莊園。童年的記憶隨著時間的推移,有點模糊了。但像石榴樹、院子、雨、星星,這些詞語還會繼續給我非常美好的感覺,應該和童年有很大的關系。
鐘:你說過:“一朵花開在自己的香氣里,一個人活在自己的苦難里,寫詩是為了內心的幸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創作對你而言是否具有一種療傷的作用?
許:這首詩大約是2003年寫的。當時沒有經歷很多事情,特別是對生死、苦難理解得不深。反而是現在,經歷了更多的事情后,你今天提起,我重新讀,感覺到這句話傳遞給我的信息是一種豁達的幸福。寫詩讓我發現生活表層下豐富的美。這種美,是豐富體驗的美,是生、離、死、別,匯聚起來的生命層次感。
鐘:你在西林這個小鎮生活了三十年,西林對于你是地理概念嗎?在你的詩中有大量地方特色的地名,比如“足別”和“八務”、“魯渭村”、“那霧村”等。
許:西林對我不是地理概念,是生活。“足別”和“八務”、“魯渭村”、“那霧村”這些都是我周圍的村莊、湖泊、小鎮的名字。把它們寫進詩里不是為了紀念我到過那里,是因為漢字的組合會對我的思想產生一種奇異的魔力,魔力的結果就是成為詩。這種魔力來自我的潛意識。人的腦子是一臺神秘的機器,它會幫你選擇讓你心動的詞語。我會長久地記住一個女人的名字:穩在,或是一個超市收銀員的胸牌:那西。這些讓我一怔的詞語,會延伸我的想象力。
鐘:地域性的文化傳統對一個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西林地處桂、滇、黔三省(區)結合部,多種文化的滲透,對你的詩歌寫作有哪些影響?
許:我在那個小鎮生活三十年,那里是三省的交界處,交通不算發達的時候,更顯得遼遠。我更多地感受到當地人性格中淳樸、憨厚的那一面。密林、群山、草木安靜,我們在偌大的松林里奔跑,揀松果,摘剛開的野菊花,它們自然都滲透到我的詩歌里。
“用心的眼睛與周圍的事物交流”
鐘:我讀你早期的詩集《河水倒流的聲音》,總覺得不夠充分,有更深、更重的東西被埋藏了,沒有顯現出來。
許:寫作和思考都有一個過程吧。但是如果不寫詩,生命中的很多細節,可能都被忽略掉了。
鐘:在你的作品中,回憶是個非常突出的主題。正如你所說的“很多細節都被時間淡漠了。選擇留在記憶里的,會穿越時間的束縛,成為某種信念”。那某種信念具體所指向的是什么?
許:指向是明亮,像光一樣溫暖的,可以引領自己繼續有勇氣生活的東西。生命由昨天組成,明天永遠在想象中,往事是你擁有的一切。詩歌和生活無法截然分開,生命的完善指向心靈向上的成長,精神也必然選擇明亮的指引。對我,詩歌起到這個作用。
鐘:在你的詩中清晰讀到兩個字:孤獨。孤獨的來源是不是和你常常下村蹲點有關?
許:孤獨?怎么說才好呢,喧嘩應該不能被選擇作為詩歌的外衣吧。不僅是詩歌,還有散文、小說都應該喜歡把孤獨作為底色吧。因為寫作需要安靜,無法靜止下來怎能聽到內心的聲音呢。
其實我在心里喜歡自己和自己說話,別人問我話,我在心里回答了,但是他沒有聽見,那是他的事。孤獨衍變成一種內心的對話,我感到很自由。工作后,經常下鄉,有時一整天在青岡林里走,或者穿過一片片密密匝匝的玉米地。只聽到腳步聲,兩三個人的呼吸聲,深山里的那種靜謐,是完全把你網起來,兜起來的感覺。那時,我會用心的眼睛和周圍的事物交流。
“我終于承認,死亡是真的”
鐘:你第一次觸及“死亡”的是你外婆?
許:是的。活著,看見過葬禮,知道是有死亡的。但是如果你沒有經歷過身邊最親近的人死亡,你永遠也不明白死亡;如果你不去深入地思考死亡,你就算明白了死亡,也不肯相信自己每一刻都活在無常中。
鐘:在你2011年的詩歌中,大量出現“死亡”這個意象,并且和父親是緊密相連的,是你父親的死亡帶來的陰影嗎?“死亡”系列傳遞給讀者的是什么?
許:父親的去世,給我帶來很深的刺痛。父親和我先是朋友、兄長般的關系,其次才是父女關系。那種刺痛不僅僅是失去親人的刺痛,還是一個親密的朋友以他的死亡來提醒我思考:你為什么而活著,你要怎么生活。寫下《時間已經遲暮,燈光恰好熄滅》這組詩,是為了紀念失去父親的難過,也是為了記錄自己對生命終極問題的感悟。每一首都提到死亡,是因為,三年多來,自己走進了生命的荒野,而在深入內心的幽暗叢林中,惟有詩歌,詩歌的光才能引領自己走出黑暗。
鐘:談談你對于死亡的理解或看法。為什么說“我終于承認,死亡是真的”?
許:每個人都會遇見死亡。十多年前,中午我們還和父親一起吃午飯,一個小時后他因為車禍,永遠地走了。很長的時間,我不相信他走了,他的笑容、話語還縈繞在家里的每一個角落,我想他是去了一個很遠的地方,所以每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我都會無意識地在人群中去尋找他。父親在我們的生命中扮演一把大傘,我們一直躲在他的庇護之下生活。忽然之間,庇護所倒塌了,生活遭遇了廢墟,你怎么辦?于是用漫長的時間來思考,想死亡除了告訴你悲傷還要告訴你什么。直到想明白,能真正領悟到被悲傷厚厚包裹起來的禮物,是珍惜和豁達。我說我終于承認死亡是真的,其實也是說,經過刺痛我才明白,活著就是奇跡是真的。
鐘:這些關于“生與死”永恒主題的詩,我覺得是你詩歌中最見功力和感染力的。
許:父親從生病到去世,這中間有一年多的時間。那時,我已經離開小鎮。但是每到周五,我都會坐傍晚的最后一趟車,深夜回到小鎮陪著他兩天。這期間,他活得非常痛苦、辛苦,我們會整夜坐著,說話。
鐘:主要聊什么呢?
許:最后一次聊死亡。我在詩里寫道:“我們談到了植物和土地/談到了感恩/當說到生命的結束/如同一次新旅程的開始時/我轉過身/含淚遙望黑暗”就是談話的真實記錄,我的詩歌,有時候是生活的旁白。
那時,父親看起來已知天命,比較平靜。因為沒有藥物可以治愈,只能敷些草藥汁液來稍微減輕他的疼痛。他問我,以后有什么打算。我沒有回答他這個問題,我說:以后我會特別感謝植物,因為這些植物的作用,讓我們還能在一起好好說話。忽然,他非常堅定地對我說:我會在那里一直看著你,活著要有信心!我們都流淚了。他的祝福,在我心里就是詩歌的光芒。
鐘:你的詩歌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是將抽象的東西具體化,這些具體化的形象多以群山、草木等為中心意象。如詩句“我們去往的是一條通向永生的路/像一只塔形的松果輕輕落下/死亡來臨的瞬間”。
許:這些都是我周圍的事物。松樹林是我常去散步的地方。山楂林、迷迭香都是父親種下的,大概有幾百畝。我說,迷迭香就是回憶的味道,因為我和父親曾經在漫山遍野的迷迭香中一起行走無數次。
鐘:在你詩歌中也有不少“雪”的意象。
許:是的。雪在南方是很新奇的。而且那年的大雪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難忘的還有一個叫梅的姐姐,是我們的鄰居,長得很美。那年她剛好參軍回來,和我們一起玩打雪仗。很多年后,她出車禍走了。所以這些串起來,是一種感傷和幸福交織的記憶。可能我的記憶會自動儲存這些細節。也許在無意識中,我一直在思考死亡。
鐘:你的詩中常常出現“曠野”“蒼鷺”這兩個意象,你想賦予它們哪些意味?
許:曠野代表的是空曠、遼闊。蒼鷺是堅韌、堅強。它們在我心里都是美的事物。空是美的,靜也是美的,動也是美的,生命是豐富的載體。
責任編輯:傅燕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