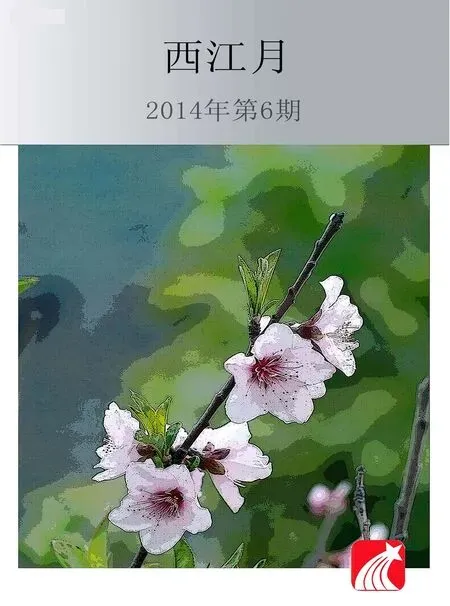那么臺灣
伍愛春 文/攝
風情風物
那么臺灣
伍愛春 文/攝

天然的藝術沙盤
如果沒有去過臺灣,它于我而言,只是一個還未回歸的海島,那么遙遠,那么陌生。余光中詩句的美麗憂傷,讀得懂,卻觸不到。
如果不了解臺灣,在聽到《綠島小夜曲》時,我心頭也不會涌起淡淡的憂傷。它那么老式,那么沉緩,一首有點過時的情歌而已。
如果沒去過臺灣,又怎么體會得到它無法言說的風情?
那么狂野,那么溫柔
有誰可以留住海的腳步,有誰可以記錄風的足跡?在臺灣海岸線,處處有海的腳步、風的足跡。
依著狹長的版圖,臺灣的海岸線分為東海岸線和西海岸線。東臨太平洋,西近福建省。
東海岸以雄壯峻峭見長。在太平洋的凌厲海風年復一年的拍打下,臺灣東海岸山脈只剩下嶙峋的巖石,倔強地傲立著。山上茂密的叢林冠頂,都被海風修剪得整整齊齊。懸崖下,幽深的山脈直插海底。海底山脈深度的變化,直接影響到海水的顏色。幾十米的海面內,海水已經由淺藍色漸變成了深黑色。
在臺灣東邊,有中國最美麗的海岸線——野柳。野柳的著名,是因為海蝕和風蝕的共同作用,造就了這里奇特的自然風光。整個野柳仿佛是一個巨大的沙盤,盛放著那些由上帝之手雕刻而成的藝術作品。那些像蘑菇、像蜂窩、像人物、像豆腐塊的巖石,呈現金黃色或者深褐色,任人遐想。

潘安邦故居
那著名的“女王頭像”,頸部修長,肩部豐滿,發髻高盤,海風吹起了發尾。她雙目微垂,仿佛陷入了沉思;那巨大的“魚尾”,倒立在海岸上,一定是它在某個午后歡快過頭,隨海浪一躍而起,卻一頭扎在沙堆里;還有那些被海浪侵蝕成燭臺狀的巖石,圓潤的“燭身”,搖曳的“燭火”,大浪撲過來,“燭淚”傾泄而下……形狀各異的巖石,造型簡潔生動。海的腳步,風的足跡,在這里清晰而又深刻。
不僅僅是野柳,整個臺灣東海岸,都被這種大自然的力量包裹。一邊是綠色的高山,一邊是蔚藍的深海。處處都是巖石和海浪搏斗的場景,高山與海風對峙的畫面。這個季節,是萬物復蘇的季節,沿路偶爾有幾塊農田掠過,秧苗在農田鋪滿了縱橫交錯的綠色線條。生命如此珍貴,又如此渺小。
車子在臺灣最南部的墾丁拐個彎,我們進入了臺灣西海岸。
相對于東海岸的萬馬奔騰、氣勢磅礴,西海岸顯得格外嫻靜嫵媚。如果說臺灣的東海岸是大刀闊斧的,那么,西海岸則是精雕細琢的。
它有著名的玄武巖,像一根根經過打磨的石柱,將島嶼一層層圍起來,被風和海浪剝去一層,里面又露出一層;它有令人神往的吉貝嶼,潔白的沙灘如一片羽毛飄落在海中;它有帶給人們浪漫遐想的星沙,每一粒潔白的沙子,都呈現不規則的星形;它有神奇的雙心石滬,這些漁人們堆砌的捕魚陷阱,那心心相印的造型在數百年的海水浸潤下,已經成為了永恒愛情的象征……所有這一切,與晶瑩的海水融為一體,讓人仿佛置身夢境。
風清沙細的西海岸,以其無限柔情,滋養了許多著名的藝術家,誕生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歌曲。著名歌手潘安邦和張雨生,不僅都生活在臺灣西海岸的澎湖灣,兩家居然還是鄰居。兩家都顯得非常簡陋,院墻用粗糙黝黑的巖石砌成,外面糊一層水泥灰。然而,對于少年潘安邦和張雨生來說,有大海、有家人就足夠了。《外婆的澎湖灣》、《大海》……這些膾炙人口的歌曲,就是在這樣簡陋又美麗的地方唱響,紅遍了全球華人區,讓多少人跟隨他們的歌聲,遙想過澎湖灣的美麗,感受過大海的深情。
那么喧囂,那么虔誠
在臺灣期間,也親歷了一些讓我們感嘆的“小事”。
當時我們在臺灣花蓮縣開展桂臺文化聯誼活動,鄉長以及縣里的議員都到齊了,可桂、臺雙方的主要與會領導代表,卻因其他活動拖延了時間,臨近中午還沒有趕到聯誼活動現場。兩名議員面露難色,最終不等領導到來便離開了。其實,他們離開的原因,是因為鄉里有位鄉民擺喜酒邀請了兩位議員。為了一個鄉民的喜宴而缺席重大政治活動,對于我們來說,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臺灣是全世界廟宇密度最大的地方,而且其數量還在迅速增加,據臺灣《中國時報》報道,2011年臺灣已有廟宇15211座!10 年間增加了2678座。每一座廟宇都修建得繁復細致精美,與周邊的現代建筑形成鮮明的反差。這些廟宇里,既有供奉道教、佛教、基督教神明的,也有供奉歷史人物、英勇先烈的。
臺灣廟宇文化的興起,本就源于悲凄的歷史。據說臺灣不少人都是近三四百年間由大陸移居過來的。他們大都是落弟秀才、無業游民,部分是失意官員、逃犯,他們光著膀子、穿著褲衩,乘一葉扁舟,渡過寬達一百多公里的“黑水溝”(由于水極深而呈墨色)——臺灣海峽。他們船上的竹籃里通常放著兩樣貴重的東西:一是祖先牌位,二是家鄉、家里所參拜的神明。懷著對故鄉不堪回首又日夜思念的復雜心情,面對“蠻荒瘴癘之地”的惡劣環境,他們帶著家鄉的神明,祈禱在外一切平安。
歲月的流逝,經濟的騰飛,并沒有沖淡臺灣居民們對家鄉的深深眷戀、對中華神明文化的崇拜、對自信安寧生活的無限向往。一座座廟宇,寄托著他們對故鄉的思念、對幸福的期盼。

在臺灣隨處可見這樣造型繁復的廟宇
那么可愛,那么嗲
同伴說,她來臺灣,目的之一是要沾染些臺灣腔的嗲聲嗲氣,像林志玲一樣“嗲嗲的”。我們沒有遇見林志玲,也沒有遇見那種嗲到像林志玲一樣的臺灣女孩。但在臺灣的第一餐飯,我們就見識了臺灣腔的與眾不同。
那是一家類似大排檔的小飯店,由于靠近景區,人滿為患。店里也沒有正規的服務員,都是阿媽阿爸、阿姐阿嫂在忙碌著。然而,他們并未因此而少了禮節,每一次上菜,每一次撤碟子,每一次添飯,開口閉口必言“謝謝”。一餐飯下來,我們收獲了20多次“謝謝”,點頭回禮點到脖子都發酸。
在此后的整個行程中,“謝謝”成了我們的口頭禪。
臺灣腔是什么呢?去年以來,隨著《爸爸去哪兒》流行,臺灣小萌娃KIMI讓無數人為他那奶聲奶氣的臺灣腔著迷,他的招牌語言“爸比”和“我要喝奶奶”已經響遍大江南北,連大人們都禁不住模仿一兩句。
事實上,臺灣腔不是嗲,而是一種透著平和、謙讓的語氣。他們的口頭禪“我和你說哦”總是透著一種親近的、有商有量的態度。即使不認可,也會說“不要醬子(這樣子)啦”,囫圇的“醬子”和長長的語氣詞“啦”,瞬間消磨了許多對立情緒。當地一位當老師的朋友介紹,在外來人口相對較少的澎湖,警察是最閑的,一年到頭都沒幾個案子可辦。我想,這是否與他們這種溫言軟語的性格有關呢?
不知道是語言軟化了性格,還是性格決定了溫柔的語言。我們在臺灣遇到的人,都那么溫和親切。導游阿郎是個三十來歲的高雄人,語調和名字都帶著濃郁的臺灣味。除了笑瞇瞇,他與大陸導游的最大不同是對拍照有澎湃的激情。他把相機別在腰上,隨時準備為我們抓拍。在一些大型活動場合,他甚至比專業的記者還敬業,永遠第一個沖上去,最后一個撤下來。我們并沒有要求他拍照,對他那過分的攝影熱情開始還有些不理解:一個導游那么愛照相,仿佛去到哪都是第一次去似的,不會是新入行的吧?
離開臺灣的時候,阿郎說,他會把給我們照的相片刻成光盤寄給我們,大家來一次臺灣不容易,他雖然照相技術不好,拍的都是些很生活化的鏡頭,卻會給我們留下最真實的記憶。那一刻,我們覺得他那別扭的高雄腔真的很親切很好聽,都在不知不覺中,學他把野柳說成了“矮簍”。
一天晚上,慕名來到臺北士林夜市。路邊有許多賣新鮮水果的攤檔,熱情的攤主們用竹簽戳著切好的水果給我們嘗,在美味的誘惑下我們都買了不少。即使拎著大袋小袋,攤主們也會把水果遞過來邀我們品嘗。臺灣水果并不便宜,動輒幾十元一斤,小小一塊也得好幾塊錢。我們不好意思地舉起袋子,意思是已經買了。她們并沒有因為生意做不成而立刻變臉,而是繼續大方地請我們吃一塊,很驕傲地說:“臺灣水果很甜哦,買啦就對了啦。”
那溫和甜潤的臺北腔調,讓我無比懷念臺灣水果。
就這樣吃吃走走,說說笑笑,在某個早上,我突然間發覺,我們說話的聲音小了,語調不那么張揚了,那嗲嗲的臺灣腔已經脫口而出了。
那么親切,那么傷感
從來沒有哪次旅程會像這樣,有些緊張,又有些期盼。像探望已經離家多年的親人。60多年了,跨過了人生大半世,雖是血脈相連的親人,巨大的時間和空間又會讓我們有多少不同呢?
與臺灣民眾最直接、最大型的一次接觸,是在臺灣花蓮縣的一次贈書活動上。花蓮縣原住民占全縣人口的四分之一,是臺灣原住民聚居區高度密集的地方,包括阿美族、太魯閣族在內的六大族群。
走進捐贈會場,我們便被那熱鬧的場景震撼了。會場是兩座山谷間的一片寬闊平整的草地。為了迎接我們,花蓮縣政府工作人員、普通民眾,以及六大族群的族長們率領的原住居民,早早來到了會場。他們穿著節日的盛裝,繞著會場跳著歡快的舞蹈,偌大的草坪上到處是歡快舞動的身影。沒有刻意的濃妝和精心的編排。陽光灼熱地打在臉上,歡快的笑容映著藍天白云,那么真誠。
看慣了泛濫于各地的民族表演,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真不敢相信,這里真的還有這么原生態的居民。他們快樂、知足。還記得中午我們沿途路過一些村落,路邊綠樹叢中的一戶庭院里,隱約傳出了節奏強勁的樂曲聲,走近才發現,這戶人家剛擺了喜酒,鍋碗瓢盆還沒來得及清理,客人們已經伴著節奏跳起舞來了,熱熱鬧鬧地擠滿了院子。
我想,該有多么熱愛生活的人,才會這么簡單快活啊。花蓮人對生活、對家鄉的熱愛,體現在他們的一言一行中。
我們和花蓮縣民眾聯誼的那天,大約聚集了1000多人,大部分人的午餐都是在活動現場吃的。近千份飯盒、無數的礦泉水瓶,以及各種塑料袋、紙巾、剩菜剩飯……按我們以往的經驗,曲終人散時,會場會狼藉一片。然而,令我們驚訝的是,他們沒有一個人亂丟垃圾,一些阿姨們見到地上哪怕只是一點紙屑,也馬上撿起丟進垃圾桶。待我們上車離開時,清運垃圾的車也幾乎同時離開了。山谷里,依舊碧草藍天。
然而,在臺灣不是所有的回憶都是歡快的。特殊的歷史畢竟造成了我們在時空上的分離,造成了一些無法回避的傷痛。這些疤痕深深地刻在太魯閣險峻的巖石隧道里。途經太魯閣地質公園的中橫公路,是一條長約300多公里、完全由人工開掘的穿山公路,是一條用200多條性命搭建起來的血肉之路。
開掘這條山路的,據說是當年的志愿軍戰俘,被美軍押送到臺灣。臺灣當局在他們身上刻字,然后命令他們用血肉之軀,在深谷險峻的巖壁上,硬生生鑿出臺灣第一條橫貫東西的公路。現在人們都驚嘆于這段公路的險峻,還有誰能銘記那些葬身這亂石之下的英靈們?如今時過境遷,相信他們的英魂已魂歸故里了吧。


橫貫太魯閣國家地質公園的黃貫公路有著辛酸的開掘史
在夕陽西下的路上,我們唱起那首《綠島小夜曲》。那時,臺灣東海岸正春暖花開,一片片的小野花如花毯似的掠過。海浪一波波涌來,躍起又落下,送來一陣陣潮濕的風。太平洋上空,一朵朵白云如蓮花般靜靜開在夕陽里。歡快中夾著淡淡的憂傷,隨著歌聲彌漫在車廂里。
在花蓮,我們還在海邊的一家餐廳里,認識了一個姓chen的老板。整個餐廳不如說是一個小小的藝術展覽館。各種木雕、書畫、對聯,占據了餐廳大部分空間,臨海長廊,一溜擺了各種造型奇特的桌子、椅子,是用木頭和圓形的鵝卵石做成的,樣子和材料都匪夷所思。
老板60來歲的樣子,言談之間以文化人自居。交流時我們問他怎么稱呼,他說姓“chen”。
再問:“是耳東陳嗎?”他驕傲地回答:“不是那個陳,我們那個chen,你們不知道的,我們先輩是正黃旗!”
出于禮貌, 我們也各自介紹了姓名和來自哪里。當小劉自我介紹說他來自四川時,老頭子眉毛動了一下,追問:“四川哪里?”得知是德陽的,他眼睛一亮,脫口而出:“那我們是老鄉啊!”突然神色又暗淡了下來,自言自語了一句:“我們那邊的人很少來臺灣呢。”聊了一陣,老頭子忙去了,過了一會,端來一大盆海鮮,說今晚高興,請大家的。過了一會,又把一盆菜送過來,還是請大家的。我們忙說“夠了,夠了”,請他坐下來一起喝酒。本來孤言寡語的老頭子話多了起來,談自己的子女,談自己的生意,滔滔不絕。在漆黑的海岸邊,飯店溫暖的燈光下,一桌子人把酒夜談,共話離殤。
那一晚,海灣沉靜,春風習習。
責任編輯:傅燕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