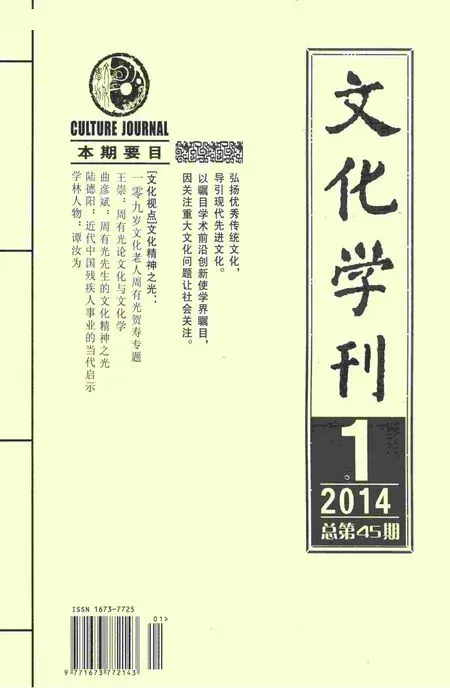兩股道上跑的車
王充閭
一席話
敘寫張學良的親朋故舊、社會交往,我覺得有一個人需要綴上一筆,那就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因為從他對于溥儀的關注,特別是為這位前朝廢帝所設計的人生道路中,可以洞見其人格、品性和卓越的識見。
溥儀,作為一個政治工具,一個典型的能走動、會呼吸的時代玩偶,就其道路抉擇、政治取向來看,誠然是可恥、可鄙的,然而,如果從人性的角度觀察,那么,他的人生處境、慘酷遭遇,又確是可悲、可憫的。登基、退位之類的話題,與本章主題無關,且不去管它,這里只講他被逐出紫禁城而日夜籌謀著還宮復辟之事。他的社交圈子很廣,親族之外,面對的主要是三種人:一是前清的遺老,帝師、老臣、忠仆、南書房行走;二是走馬燈般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軍閥政客;三是陰險狡詐、虎視眈眈、居心叵測的東鄰野心家。角色不同,心性各異,但他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千方百計要利用這個政治玩偶,達到其不可告人的個人目的。就中,只有一個人例外,他沒有政治野心,根本沒想在溥儀身上打什么主意,只是出于友朋之間的真誠愿望,甚至是年輕人熱心、好勝的習性,善意地提出了一些個人見解,他就是張學良。
張學良與溥儀相識于上世紀20年代中葉,那時他不過二十五六歲,溥儀也剛過二十歲。他們相會于天津日本租界地宮島街的張園,那里是溥儀的所謂“行在”辦事處;他們在其他場合也見過面,可以說,交往較多。有人統計,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及張學良,多達二十處。
1990年夏,張學良在同日本廣播協會 (NHK)電臺記者交談中,說到了早年他與溥儀會面時的一席話:
我在天津的一個飯館吃早飯,溥儀突然進來看見我。我勸他把袍子脫掉,把身邊那些老臣辭掉,你這些老臣圍著你就是在揩你的油,你能天天出來走走,我倒很佩服你。我勸他,你肯不肯到南開大學去讀書,好好讀書,你作一個平民,把你過去的東西都丟掉,你真正做個平民。如果南開你不愿意去,我勸你到外國去讀書,到英國或到哪兒去讀書。我說你原來有皇帝的身份,你雖然是平民,你比平民還是高,你要是真正好好做一個平民,將來選中國大總統中有你的份。你如果今天還是皇帝老爺這一套,將來有一天會把你的腦瓜子耍掉。
從敘談情景看,他們并非初識,而是相處已久、相知較深了。張學良言詞峻烈,但態度是真誠的,設身處地,置腹推心,完全出自對溥儀的關愛。正如溥儀研究專家王慶祥所說的:“張學良跟溥儀交往,從來沒想過利用‘宣統皇帝’這塊招牌,恰恰相反,而是勸溥儀脫袍子,辭老臣,‘真正做個平民’,然而,他們政見不同,交往中潛藏著對立和斗爭。張學良承繼著老一輩的交往,同時牢牢掌握著自己的原則。”
王君的解讀,片言居要,恰中肯綮。這里有三個關鍵詞:(1)“沒想過利用”他;(2)勸他“真正做個平民”;(3)二人“政見不同”“潛藏著對立和斗爭”。
與少帥恰成對照的,是他的父親老帥。從王慶祥《溥儀與張作霖》一文中得知,老帥曾經巴結過這位退位皇帝,叩過頭,送過兩棵高價的東北人參。當年拜見袁世凱大總統時,他也只是送上一棵,價值六千金;那么,兩棵呢?前此,溥儀選立“皇后”時,老帥曾主動要把女兒獻上,只是由于“滿漢不能通婚”的清宮祖制所限,才算作罷。俗話說:“禮下于人,必有所求。”這一代梟雄精明絕頂,外殼是“忠君”,而內核卻是利已——深知問鼎中原,還需利用“宣統”這塊招牌。特別是老帥早就把滿蒙地區看做自己的勢力范圍,而要提高在這一廣袤地區的影響力與號召力,清朝帝室與蒙古王公的特殊歷史背景是絕對不能忽視的。當然,以復辟為職志的末代皇帝,也看中了這個“東北王”的政治地位和強大的軍事實力,互為利用,這原本是他們之間的本質特征。
少帥奉勸溥儀脫去皇袍,辭掉老臣,真正做個平民,卻是完全出于至誠,而且是絕對的高明。對于溥儀,少帥可說是仁至義盡。直到“九一八”事變之后,張學良已經弄得焦頭爛額,自顧不暇之際,他還不忘拉扯已經泥足深陷的溥儀。據王慶祥文中披露,1931年11月2日,土肥原夜訪溥儀,并甜言蜜語地說,日軍在滿洲的行動,僅為反對張學良,而對滿洲毫無領土野心,并愿意幫助宣統皇帝在滿洲建立獨立國家。溥儀傾向于接受。張學良聞訊,于6日晚,往其駐地靜園送了一筐水果,其中潛藏兩枚炸彈,意在警告溥儀,讓他清醒。翌年7月,溥儀任偽滿執政四個月后,張學良又通過他的胞弟溥杰再一次進行規勸。溥杰后來有回憶文章,說:“暑假我從日本回國了一次,張少帥大概也得知了我回國的消息,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他的信,記得信的大意是:日本人歹毒異常,殘暴無比,我們父子同他們打交道的時間長,領教夠了。他們對中國人視同奴仆,隨意宰割。你要警惕他們,并要勸誡你哥哥,讓他同日本人脫掉干系,懸崖勒馬。可惜,我當時為了同溥儀一道恢復滿清王朝,對張少帥這些忠言根本聽不進去,真是一樁終生憾事。”
時光不會倒流,歷史不容假設。如果當日溥儀能夠聽進去這番話,篤信躬行,付諸實踐,那么,他就不會背上“漢奸”“戰犯”的惡名,遠離那根歷史的恥辱柱,余生將會現出嶄新的霞彩。
至于說到少帥與廢帝兩人“政見不同”“潛藏著對立與斗爭”,這是準確無誤的。他們確實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豈止不同而已!這在對待日本軍閥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次郎的態度上,暴露得至為充分。
三條路
張學良的忠告,對溥儀來說,有如秋風之過馬耳;或者說,逆耳之言,根本聽不進,這里有主觀與客觀雙重因素。從主觀方面說,溥儀復辟意志的頑強與堅定,應該說是占主導地位的。
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記載,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的國民軍把他逐出紫禁城,當帶兵進宮的北京警備司令鹿鐘麟問他“你今后是還打算做皇帝,還是要當個平民”時,他曾爽快地回答:“我愿意從今天起就當個平民。”對他來說,無疑這是最光明的前途,最理想的選擇。張學良的勸說,正與此恰合榫鉚。
后來的實踐表明,他的這種表態,純屬言不由衷,根本不是真心話。他的真實打算,卻是:“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實現我的理想——重新坐在失掉的寶座上。”其間,北府二十四天,日本大使館三個月,天津七年,以至后來潛往東北,可以說,無分晝夜,醒里夢里,時時刻刻,都在思謀著、策劃著怎樣還宮復辟。對此,少帥并非沒有察覺,只是出于真正的關心,作為朋友,還是披肝瀝膽地掬出至誠,為他做出具體的擘劃:到南開大學進修,或者去英國留學;最后,當頭棒喝,如果舍此不由,繼續走那條幻想復辟的老路,那就等著掉腦袋吧!
除了少帥,可以說,溥儀身邊的一切親朋故舊,再沒有人這樣地勸過他,包括他的父親載灃在內,那些遺老舊臣、皇親國戚,還有軍閥政客,用他后來的話說,身旁正有“一群蠅子”,整天嗡嗡營營地,吵得一塌糊涂。有些人,比如他的父親載灃,頭腦昏憒,未諳覆車之鑒,也就是見不及此,而更多的人,是從個人私利出發,把這個末代皇帝居為“奇貨”,當做實現種種目的的政治工具。
溥儀后來回憶說:
我面前擺著三條路:一條是新“條件”給我指出的,放棄帝王尊號,放棄原有的野心,做個仍然擁有大量財寶和田莊的“平民”;另一條,是爭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國民軍的新條件,全部恢復袁世凱時代的舊條件,或者“復號還宮”,讓我回到紫禁城,依然過著從前那樣的生活;還有一條,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過那時的紫禁城,必須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這條路當時的說法則是“借外力謀恢復”。
我站在這個三岔路口上,受著各種人的包圍,聽盡了他們的無窮無盡的爭吵。他們對于第一條路,都認為不屑一顧,而在其他兩條路線的選擇上,則又互不相讓。即使是同一條路線的擁護者,也各有不同的具體主張和詳細計劃。他們每個人都爭先恐后地給我出主意,搶著給我帶路。
表面上,這些人期待復辟的目標是共同的、一致的,實際上,每個人都是“各懷心腹事”,打著自己的小算盤。以羅振玉為首的“出洋派”,主張“立刻出洋”,日本也好,歐洲也好,他們想望拉著這個末代皇帝,投靠到洋主子的卵翼之下,通過壟斷居奇,收獲各自的好處。以帝師陳寶琛為首的“還宮派”,那些王公、舊臣、帝師、翰林們,則是惦記著這些名頭,這些高位,使已經喪失了的重新回到手中。這一點,溥儀后來也看清楚了,他說:
我認為,那些主張恢復原狀的,是因為只有這樣,才好保住他們的名銜。他們的衣食父母不是皇上,而是優待條件。有了優待條件,紹英就丟不了“總管內務府印鑰”,榮源就維持住樂在其中的抵押、變價生涯,醇王府就每年可以照支四萬二千四百八十兩的歲費。
就溥儀個人來說,復辟復位,是所至望,但他并不愿意重新回到紫禁城去,以免在那里遭限制、受約束,他的目標是“依他列強,復我皇位”。這樣,他從北府出來,一頭就扎進了日本使館,實際上,從此也就投入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懷抱,開始踏進罪惡與死亡的深淵,他卻醉生夢死,酣然不覺,竟說:
在那個時代,“使館區”和“租界”正是“好客”的地方。我在這里遇到的熱情是空前的,也許還是絕后的。……使館主人看我周圍有那么一大群人,三間屋子顯然住不開,特意騰出了一所樓房,專供我使用。于是,我那一班人馬——南書房行走和內務府大臣以及幾十名隨侍、太監、宮女、婦差、廚役等等又各得其所。在日本公使館里,“大清皇帝”的奏事處和值班房又全套恢復了。……這些表示骨氣的,請安的,送進奉的,密陳各種“中興大計”的,敢于氣勢洶洶質問執政府的遺老遺少們,出進日本使館的一天比一天多。到了舊歷的元旦,我的小客廳里陡然間滿眼都是辮子。我坐在坐北朝南、以西式椅子代替的寶座上,接受了朝賀。……
在使館的三個月里,我日日接觸的是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遺老們的忠誠信誓和來自社會的抗議。我的野心和仇恨,在這三種不同的影響下,日夜滋長著。
這種仇恨到了1928年7月2日,國民政府陸軍第十二軍軍長孫殿英東陵盜墓事件發生,達到了一個新的頂峰,末代皇帝發誓與國民政府不共戴天,可是,事實上,他根本不具備報仇雪恥的實力。怎么辦?除了投靠列強、借助外力,就是發展自己的武裝勢力。他從蔣介石與張氏父子的發跡史中得到一個重大啟發,“這就是若求成事,必須手握兵權,有了兵權實力,洋人自然會來幫助。像我這樣一個正統的大清皇帝,倘若有了軍隊,自然要比一個紅胡子或者流氓出身的將帥更會受到洋人的重視,因此,我決定派我身邊最親信的親族子弟去日本學陸軍。我覺得這比自己出洋更有必要”。
與此同時,溥儀正在一步步地向日本軍閥靠近。當時,日本侵略者把子承父業、執政東北、特別是宣布“易幟”、服膺中國統一大業的張學良看作是他們分裂中國、吞并滿蒙、建立“滿蒙帝國”的最大障礙,由過去的百般拉攏,而變為切齒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了。受其影響,溥儀對于張學良的態度也隨之而改變。他既不愿意張學良當“東北王”,更對南北統一持強烈反對態度,因為這不利于他實現復辟大計。
兩條路
張學良主政東北之初,擺在他面前的有兩條道路可供抉擇:一條道路,是繼續堅持奉系軍閥的路線,沿著他父親所闖開的老路亦步亦趨,戰伐不停,窮兵黷武,使國內仍舊處于南北分裂狀態——如果這樣做,則勢必仰承日本人的鼻息,尋求列強的支持,實行所謂“保境安民”“滿蒙獨立”;另一條道路,是改弦更張,同老帥所慘淡經營的什么“東北王” “滿蒙王”——也就是現代“李世民”的路線劃清界線,堅決走國家統一、民族獨立之路,接受國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他毅然選擇了后者,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國青天白日旗,有條件地接受國民政府的統一指揮。
奉系軍閥是北洋軍閥中的重要一支,又是北洋軍閥政府末代的統治者。東北“易幟”,標志著現代中國長期以來混亂局面的終結,起碼是在形式上實現了統一,這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就張學良個人來說,實現了由封建軍閥向愛國主義將領的政治轉變。
在他宣布東三省“易幟”,服從中央統一指揮之前,日本人曾經連番發出警告;后來見威脅恫嚇不成,便又甜言笑臉,百般利誘。那天,日本首相的特使登門拜訪,承諾要全力支持他出任滿洲“執政”,并表示:只要提出要求,都將一一照辦。張學良卻不緊不慢地說:“你想得挺周到啊,只是忘掉了一點。”特使忙問:“哪一點?”他說:“你忘了我是中國人。”幾句話,噎得日本人目瞪口呆,不得不刮目相看。他們原以為這個二十八歲的“愣小伙子”,不過是一只假張作霖“虎威”的狐貍崽兒,誰知竟是一頭無人駕馭得了的興風怒吼、咆哮山林的猛虎啊!
對于堅持走統一之路的果敢作為,少帥終生引以自豪。那一年,在臺南參謁延平郡王祠,他曾即興題寫了一首七絕,借助稱頌鄭成功戰勝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的英雄業績,抒寫自己當年以民族整體利益為依歸,堅決維護國家統一的的愛國情懷:
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義抗強胡。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臺灣入版圖。
據《張學良世紀傳奇》一書記載:在同美籍華人、著名史學家唐德剛交談時,張學良對此專門作過闡釋:
學生從題干出發,多從運輸距離和運輸重量來分析運費成本進行分析,而圖中沒有具體運輸重量,難以計算。最終根據運輸距離推斷,O點到原料M1、M2產地和市場距離距離相等,這說明M1、M2這兩種原料對工廠的影響相等,即原料指數相等。當M1、M2和產品的重量都為1個單位時,將工廠建在這三者的中間,使之到三地的距離相等,這時的運輸費用會最低,據此可推斷選項D正確。這樣講解學生對原料和產品重量沒有直觀的認識,理解存在一定困難。
“你看出我這首詩有什么意思沒有?我是在講自己呢。是講東北!假如不是這樣的話,東北不是就沒有了嗎?我與日本一合作,我就是東北的皇帝啊!日本人真請過我當皇帝,真請過我呀!而且向我申明了,當皇帝!”
“哦,這事是誰干的?”唐教授驚訝地問。
“就是土肥原干的,他搞王道論。”
“他真叫你做滿洲的皇帝?”唐教授重復問道。
“是啊,是做皇帝,做滿洲皇帝。”少帥接著說了一大篇:
已經把話說明了!為這個,我同土肥原談崩了,所以我就知道東北不能了 (當地口語,意為安定、平靜)啦!那時,他一直不讓我同中央合作。他說,你來當東北的皇帝,我日本捧你,我日本幫你。那個時候,日本在東北奉天負責任的是秦真次,那時他們叫特務長官。我把秦真次找來,我要他換顧問,把土肥原換掉。土肥原本來不是我的顧問,他是北京政府的顧問,跟著我父親回到奉天,接著就當上了東北的顧問。
我為此事跟他火了。本來,日本“二十一條”上訂的,奉天的軍人要有兩個顧問,一個上校,一個上尉,一定要請日本人。我就跟秦真次說,我要換人。他說,你沒有這個權。要不要顧問,這是日本政府的權啊。這可把我氣死了。我這個人啊,我這個怪人,事情都是這么引出來的。我說,好,我沒權,可他是我的顧問,我沒權換,那好,但我有權不跟他見面,這個權我總該有吧?我就告訴我的副官,我說,土肥原顧問隨便哪個時候來,我都不見。我說,我可以不見他,我不見土肥原的面!你是顧問,但我不跟你談話。……沒過多久,秦真次調回日本去了,土肥原又回來當上了特務長官。哎呀,這事情可糟了,我曉得這問題大了,他回來當特務長官,那就是升官了,這東北的特務都在他手里頭。我就知道要來事了。
下面,我們再聽聽溥儀的陳述:
他 (土肥原)那年是四十八歲,眼睛附近的肌肉已出現了松弛的跡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臉上自始至終帶著溫和恭順的笑意。這種笑意給人的唯一感覺,就是這個人說出來的話不會有一句是靠得住的。他向我問候了健康,就轉入正題,先解釋日軍行動 (指“九·一八”事變),只對付張學良一人,“因為他把滿洲三千萬人鬧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權益和生命財產也得不到任何保證,這樣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說,關東軍對滿洲絕無領土野心,只是“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希望我不要錯過這個時機,很快回到我的祖先發祥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日本將和這個國家訂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權領土將受到日本的全力保護;作為這國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誠懇的語調,恭順的笑容和他的名氣、身分,完全不容我再用對待羅振玉和上角利一的眼光來對待他。陳寶琛所擔心的——怕羅和上角不能代表關東軍,怕關東軍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兩個問題,我認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個關東軍的舉足輕重的人物,況且,他又斬釘截鐵地說: “天皇陛下是相信關東軍的!”
我心里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也得到了滿意的答復。我問道:“這個新國家是個什么樣的國家?”
“我已經說過,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
“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
“這些問題,到了沈陽都可以解決。”
“不,”我堅持地說,“如果是復辟,我就去,不然的話,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聲調不變地說:“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帝國,我就去!”
“那么,就請宣統帝早日動身,無論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達滿洲。”
溥儀就這樣登上了土肥原的賊船,從而一步步墜入了罪惡的深淵。
戰后,土肥原被定為日本甲級戰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指出,“土肥原是日本陸軍大佐,一九四一年升到將官階級,在“九·一八”事變前約十八年間居住中國,被視為陸軍部內的中國通。他對于在滿洲所進行的對華侵略戰爭的發動和進展以及嗣后受日本支配的偽滿洲國之設立,都具有密切關系,日本軍部派對中國其他地區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著政治的謀略、武力的威脅、武力的行使,在促使事態的進展上擔任了顯著的任務。”
同是面對這個日本軍國主義的特務頭子,少帥與溥儀,一個是以清醒的頭腦、犀利的目光、凜然不可侵犯的威嚴,從民族命運、全局利益出發,義正辭嚴地斷然加以排拒;一個卻是純然出于復辟稱帝的一已私利,奴顏婢膝,毫無氣節與廉恥地“為虎作倀”,充當日本侵略者的政治工具。他們由于所選擇的道路天差地別,最后的結局也判若云泥:一個成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受世人景仰;一個淪為罪惡的漢奸、賣國賊,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