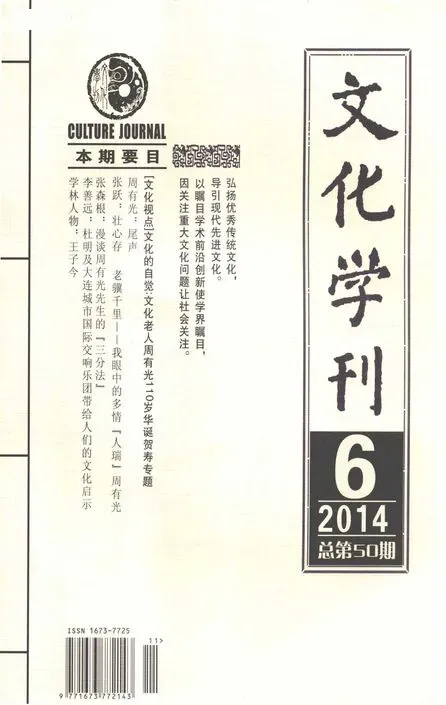任璧蓮小說中的通婚與種族身份建構
李紅燕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外國語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5)
當今美國是個移民大國,異族通婚日益增加,然而,從歷史上看,美國是一個種族主義觀念嚴重的國家,反對異族通婚幾乎從殖民地時期就已開始。反異族通婚法從法律上嚴格劃定了種族和社會界限,在形成種族認同和種族等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直至2000 年,美國才陸續廢除了各州的反異族通婚法。法律上允許通婚無疑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但是觀念上的種族階梯論并未消失,華裔在美國的地位一直在低位徘徊,于是被視為同化最后階段的跨族通婚具有了某種程度的向上流動、改變種族身份地位的功能。以亞裔為例,除日裔,基本上是學歷越高,跨族婚姻比例就越高,尤其是女性。另外,亞裔的聯姻對象基本上是白人。[1]
通婚是否真的可以幫助華裔改變種族身份地位?一些具有通婚經歷的作家從文學角度對此作了深入探討,華裔美國作家任璧蓮頗具代表性,她的作品通過表現通婚家庭成員關系來揭示種族身份地位問題和社會中的權力關系。下文將以小說《誰是愛爾蘭人》 (下文簡稱《誰》)和《妾》為例,借助身份理論來分析通婚重構種族身份的政治功能及其有限性,以及通婚所造成的社會性別身份錯位和基因傳承的不確定性等問題,表明通婚不能幫助華裔個體以改變自我角色身份的方式達成改變華裔群體的種族身份地位,任璧蓮的作品通過對通婚問題的呈現審視了華裔在當代美國的種族身份地位和政治訴求。
一、社會性別身份錯位
任璧蓮小說表明,美國華人移民個人身份與自我的角色身份和社會群體身份密切相關。角色位置可以定義和建構一個人的身份,而社會分類所形成的社會群體身份往往比角色身份更能彰顯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根據社會群體身份理論,將自我和他人進行分類從而形成“內群體”或“外群體”的方式決定了一個人的社會身份,個體的言行總趨于與群體內成員的特征相一致,以此來區分與群體外成員身份的不同。[2]自覺選擇哪個群體為“內群體”體現了社會認同。在美國,由基因所決定的膚色和血統標出了華裔的外群體身份,華裔遭受偏見和歧視,因此華裔想獲得白人主流社會的承認和尊重并成為白人內群體成員。就群體之間關系的變量而言,他們無疑相信群體邊界的可滲透性,因而采取社會流動策略,以白人的妻子或丈夫的角色身份進入白人家庭,以角色身份滲透群體身份,進而改變后代的遺傳基因,使后代逐漸白化,進入白人群體,獲得等同于白人的種族群體身份。然而,現實并非如此簡單,通婚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問題。
在《誰》和《妾》這兩部小說中,從夫妻關系層面看,通婚家庭中華裔一方的社會性別突破了常規的角色形象和功能作用,尤其是打破了中國傳統的男性和女性的家庭分工模式和話語權分配,在存在種族階梯的歷史背景下,傳統的社會性別身份產生了錯位,女性擔當男性化的角色,男性處于女性化的地位。從混血后代的基因層面看,或是華裔的基因被吞沒,混血兒身上的華人特征基本消失;或因為繼承較多的華人特征而將繼續邊緣化的待遇,遭受更多身份的困惑。
(一)女性的男性化角色
在傳統社會的家庭內部,男性具有話語權并處于支配地位。父權文化的性別體系為兩性規定了不同的性別角色,即“男主外女主內”。即使在當今社會,女性也還完全沒有擺脫對傳統社會性別的認同,一方面是基于生理差異,另一方面是對男性社會性別角色的認同。不過,性別身份與族裔/種族相關聯時情況卻可能發生變異。作為丈夫的白人男性即使經濟不能獨立,作為妻子的華裔女性仍愿意給他家庭主宰者的地位。
《誰》中的通婚家庭就存在這樣的性別身份錯位關系,但也不是“女主外男主內,”而是“女主外女主內。”故事的敘述者是一位68 歲的華人移民老太太,老伴已經過世。女兒娜塔莉與愛爾蘭裔男子約翰·希結婚,有個混血女兒叫索菲婭。孩子的保姆走后,老太太來到女兒家帶孩子,在她看來,這個家庭是個顛倒的世界。娜塔莉是一家銀行的副總裁,連婆婆都認為她“真是和白人一樣出色。”[3]雖然娜塔莉嫁的是白人,但是老太太否認高攀,這不僅因為美國的愛爾蘭人移民社會地位不高,還因為希家四個男人能力都很差,沒有一個工作的,且有各種諸如懶惰和酗酒等壞習慣。老太太完全有理由相信希家男人沒有男性氣質,沒有養家的責任感。依據中國傳統的社會性別意識,男主外女主內不僅成為男女之間的界限,也把男性作為以社會為主的人,女人則以家庭為主。當然,現代女性同樣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獲得較好的工作,但是男性也還是被認為需要工作,有時也要幫助照顧小孩或做點家務。娜塔莉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較高的職位和不菲的收入,這個家可以“女主外”,她對此沒有表示過不滿。然而,女婿既不能主外也不愿主內,“他既沒有工作,也不照顧索菲婭。因為他是個男人……”[4]娜塔莉必須獨自支撐這個家,因為她不想離婚。
華裔女性與白人通婚的結果是讓自己充當了傳統的男性化角色。娜塔莉卻沒有抱怨過丈夫,丈夫好不容易找到一份保險員的工作,她就恭維道:“很高興看到你又執政了。”[5]她在家里自我弱化,表現出對傳統女性性別身份的認同,同時也順應了種族身份地位的從屬性。不論是作為妻子還是作為華裔,她的自我角色和群體身份歸類都將自己置于弱勢地位。她對待婚姻的方式體現了以退為進、以守為攻的思想,有失必有得。她也因此獲得希家人的尊重,并維持了婚姻。從這個通婚家庭結構的表面上來看,華裔女性是拉近了自己與白人的“社會距離”。
(二)男性的女性化地位
任璧蓮小說顯示,在家庭中占支配地位的一方究竟是男性還是女性和種族身份密切相關,社會性別更像是一種權力系統,而不只是一套刻板化的模式或是一些男女之間可見的差異。在《妾》里華裔男性卡內基·黃與歐裔女性簡妮·貝利的通婚家庭中,話語權的分布狀況顯出種族身份的高低,性別身份錯位表現在華裔男性的女性化地位。
當初黃母對兒子要娶白人表示堅決反對,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擔心兒子婚后沒地位。但是卡內基堅持要娶簡妮,白人對他的誘惑力很大。黃母于是悄悄給了簡妮一百萬美元現金讓她不要嫁給卡內基。簡妮雖收下“賄賂”,卻照嫁不誤,于是黃母更加不喜歡這個白人。正如黃母所料,卡內基婚后的家庭地位確實低于簡妮。簡妮居于傳統家庭中的男性地位,并以此規定自己的言行。[6]當她的支配性地位受到挑戰時,她就立刻給自己打氣,“在這個家里,我只讓別人疑惑。”[7]盡管卡內基有接近白人社會的傾向,但是他的思想多數時候是樸實的,他的善良沒有被等級觀念所限制。例如,當初蘭蘭從中國來美國是以保姆的身份進入這個家,卡內基并沒有以主仆的姿態對待她,而是認為應該讓蘭蘭住樓下的獨立成套客房。然而簡妮借口說蘭蘭肯定想要私密性,讓蘭蘭住外面馬棚上面的小房間。卡內基覺得自己要表達點想法都“需要聚集自己微不足道的男人的勇氣…… 得先考慮自己的染色體”。[8]在這個家里,白人太太才是主人。后來,卡內基為了幫蘭蘭排遣工作之外的無聊,翻出舊電視和VCR 給蘭蘭用,還想讓蘭蘭上大學、拿學位,簡妮知道后感到很吃驚、很不舒服,因為卡內基產生這種想法居然沒有先和她商量。很明顯,在這部小說里,華裔男性在美國社會處于女性化、邊緣化的地位是以一個家庭內部的華裔男性被支配的性別身份展示出來,他處于傳統社會中女性的從屬地位,顯示出種族地位的邊緣性。
人的性別角色行為受到環境的強烈影響,不論是真實存在的還是人們想象的社會環境,都對性別身份及其發揮的功能產生很大作用。美國主流白人社會,或出于錯誤的認知,或為了保護利益集團的權力,對華裔男性的氣質做了歪曲的認定,否認他們應該擁有同等的社會地位。同時,白人男性或女性為自己構建了高于其他種族的氣質和品質,將自己置于支配性的地位。
二、基因傳承的不確定性
通婚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后代族性特征的不確定性。或許以跨族婚姻進入白人家庭并“制造”混血后代是當初華裔重構種族身份的一個目標,但是結果仍然出乎他們意料。《妾》中堅持通婚的卡內基明顯對混血兒子沒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他看到自己“新出廠的”兒子時非常吃驚:
他不是你最近你可以在周圍看見的那種褐色頭發、居于兩者之間的孩子。這個孩子——我的孩子——他是白膚金發的孩子……還有他的眼睛:圣母瑪利亞藍色。能親眼目睹孩子的接生真好。如果擱在50 年代,我很可能跌跌撞撞地跑去找律師,語音不清地告訴他,孩子出生時被掉包了![9]
與卡內基的不安相對比,簡妮對兒子的樣貌則比較滿意,“我對我的基因沒被卡內基的吞沒而感到高興……我的血統,我這一邊,我自己沒有被淹沒。”[10]血統是一個民族、家族或者說一個國家在文化上沉淀下來的血緣關系,通常用來指代某種優秀的品質,無疑,在簡妮心目中,她的血統代表更優秀的品質。小貝利像貝利家人使得簡妮非常高興,因為貝利家的基因顯出了壓倒性的強勢力量,但是卡內基對混合基因兒子的感受可謂五味雜陳:
多數人都沒注意到貝利是個雜燴湯。即使有人注意到,他們中的一些人也反應遲鈍。思考他意味著什么。然而是什么呢? 多數人會說,是未來,很可能——這是他們最善良的表達。只有我會說,是正在消逝的過去。[11]
多種族人可能被視為美國的未來,但是卡內基卻表現出對華裔作為一個族裔的顯著特征突然消失的震驚,表現出對生物同化的憂慮。在同化的過程中,少數派或其文化有可能消失在更大的或占更多支配地位的群體或文化中。
第一代移民往往反對通婚,也不喜歡混血后代,因為華人的基因被吞噬了,如在《誰》中,老太太對混血兒外孫女的不滿:“她跟我曾見到的其他中國姑娘可不一樣。我們去公園的時候,她是這么做的。她站在嬰兒車上,把衣服脫掉,然后扔到泉水里。索菲婭!我說,別扔!但她卻只是笑,像個瘋子。”[12]老太太認為中國女孩應該文雅端莊,她最不能忍受外孫女在公共場合光著身子亂跑,她天天教育索菲婭不要脫衣服,口頭教育不行,她就改為打屁股。在用體罰方式幫助外孫女不在公共場所脫衣服后,索菲婭的麻煩更多了,她學會了踢人,后來索性向老太太身上扔起沙子, “中國有成百上千萬的孩子,沒人這么做的……她跟所有的中國女孩兒都不一樣。”[13]究其原因,當然是由于華人的基因沒有得到良好的復制。她認為自己能幫索菲婭,“讓她用很中國的一面去跟她很野性的一面搏斗”。[14]
混血兒最不能讓華人接受的首先是外貌,其次是言談舉止、思維習慣等,很多混血兒完全不像中國人,華人一方的基因或文化基因得到的遺傳不多,像美國孩子一樣,他們全無中國人推崇的孝順概念,血緣和文化的紐帶在他們心中變得十分脆弱。不論華裔與白人的混血后代傳承哪一方的基因更明顯,都存在一個被社會接受的問題。混血兒遺傳白人基因多常被“理解”為白種人,遺傳華裔基因多就會被“理解”為亞裔美國人,他仍將遭遇華裔的種族身份問題。
結語
美國通婚的合法化本身反映了美國社會的進步,法律上種族隔離和歧視逐漸消除,但是社會觀念中的種族優劣區分依然存在,并對婚姻家庭關系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任璧蓮通過通婚家庭里的成員間關系揭示了美國存在的種族階梯,暴露了華裔美國人在美國社會里的弱勢地位,表達了對種族歧視的“理性的憤怒”,同時用選擇通婚表達了少數族裔個體對社會的自我調適和對于社會上種族觀念的妥協,既體現了向白人種族的靠攏,又表達了華人族裔希望分享平等權利的政治訴求。但是,華裔選擇與白人通婚并不能立刻改變種族階梯的秩序,從而幫助華裔和白人社會實現無縫對接或重構種族身份。在文化有中心和邊緣之分、種族群體有優劣之論的當下,華裔不可避免地遭遇身體、性別身份和基因的等級化,靠一代人的通婚不僅不能消除華裔個體的身份焦慮,更不能解決華裔整個族群的種族身份問題。
[1]Qian,Zhenchao,et al. Asian American Interracial and Interethnic Marriages: Differences by Education and Nativity[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35.2(2001) : 557-586.
[2]Goldberg,Caren B. Applicant Reactions to the Employment Interview: A Look at Demographic Similarit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56. 8( 2003) : 561-571.
[3][4][5][12][13][14]吉什·任. 誰是愛爾蘭人[J]. 郭英劍,譯. 外國文學,2002,( 4) :27.30.29.28.29.29.
[6][7][8][9][10][11]Jen,Gish. The Love Wife[M]. New York: Knopf,2004. 83. 247.22.184.15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