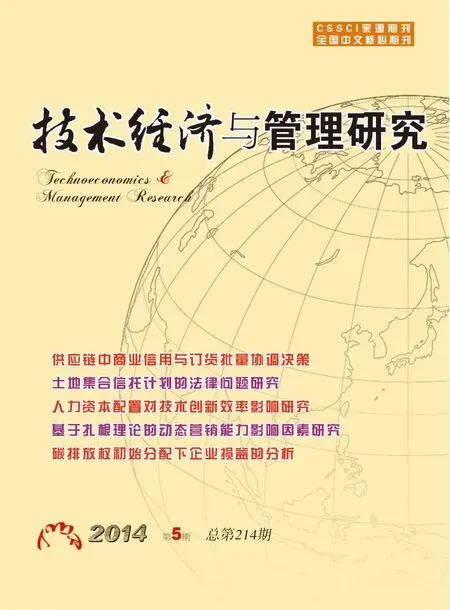西部地區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
——基于環境規制工具視角的分析
王小寧,周曉唯
(1.陜西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2; 2.青海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青海 西寧 810000)
西部地區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
——基于環境規制工具視角的分析
王小寧1,2,周曉唯1
(1.陜西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2; 2.青海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青海 西寧 810000)
西部地區在西部大開發過程中面臨的最大挑戰莫過于環境的破壞和惡化。文章立足于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的關系,利用1999-2012年我國西部地區1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數據,基于命令控制型、市場激勵型、隱性環境規制工具等視角實證分析了不同環境規制工具對西部地區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命令控制型、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對西部地區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顯著高于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隱性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有顯著的抑制作用,技術創新投入對技術創新產出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因此,未來西部地區要完善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政策;加快西部地區的市場化進程建設,為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的有效實施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提高西部地區公眾的環保意識,發揮隱性環境規制的作用;繼續加大技術創新投入,從而充分激發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誘發作用,推動西部地區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西部地區;環境規制;技術創新;區域經濟
一、引言
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隨著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西部地區的生態環境形勢日益嚴峻。以空氣污染為例,2013年12月西安霧霾位列全國污染嚴重城市排行榜第一。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提出,使地理位置處于經濟帶輻射片區的西部地區成為對外開放的前沿,可以更多地參與全球貿易,可以更方便地獲取資金與技術,為西部地區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西部地區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凹陷區的最重要部分,同時又是典型的資源型經濟地區,具有豐富的礦產資源、能源資源、土地資源、旅游資源等。因此西部地區如何抓住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帶來的發展機遇,利用突出的資源優勢在實現經濟增長、推動經濟發展躍上一個新臺階的同時,又能避免帶來空氣污染和良好生態環境的損失,就成為一個亟需面臨和解決的問題。適當的環境規制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環境規制是政府為了降低經濟活動中環境污染的外部性、改善環境質量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是實現環境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途徑。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內生增長理論都表明,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于技術進步與創新。因此有效的環境規制應當是在降低環境污染的同時,還能夠通過刺激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促進經濟的發展。文章立足于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的關系,從環境規制工具的視角實證分析西部地區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在實證分析結果的基礎上,對如何促進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誘發作用、推進西部開發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雙贏格局提出一些參考建議。
二、文獻綜述
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環境規制將通過影響企業的資源配置增加企業生產成本,減少對研發的投入,從而降低企業的創新能力。Porter(1991)[1]則認為環境規制不但不會增加企業成本,反而能夠誘發創新,產生創新補償效應,進而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即“波特假說”。此后國內外學者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設、研究樣本、分析方法和變量設計進行了豐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大致可分為三種:一是環境規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Denison(1981)。通過對美國1972-1975年生產率變化的實證分析,發現環境規制政策導致美國生產率下降了16%。江珂、盧現祥(2011)利用中國1997-2007年29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環境規制對中國三類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結果表明環境規制對我國技術創新沒有顯著的正影響。王鵬、郭永芹(2013)[2]運用1998-2009中部地區六省的面板數據實證研究發現環境規制水平抑制了該地區的技術創新能力。二是嚴格的環境規制可以顯著的促進技術創新。Berman and Bui(2001)[3]通過研究1982-1992年空氣質量規制對美國洛杉磯地區石油冶煉業生產率的影響發現,在樣本期間受規制企業的生產率上升幅度較大,同期未受規制企業的生產率則處于下降趨勢。趙紅(2007)[4]運用中國標準產業分類中18個兩位數產業1996-2004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有激勵作用。李強、聶銳(2009)[5]利用1999-2007年的中國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環境規制政策能夠顯著地促進技術創新。馬海良、黃德春、姚惠澤[6]利用1995-2008年長三角經濟區域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實證結果顯示環境規制通過技術創新產生的正向效應超過了成本增加引起的負向效應,且在即期和滯后期都能夠顯著促進技術創新和產業績效。三是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Jaffe&Palmer(1997)[7]對美國企業的整體研發活動情況進行實證研究,結論顯示環境規制政策對企業的整體研發支出有顯著的正效應,但專利數量與環境規制政策之間并不存在明確的聯系,因此環境規制政策所引致的企業研發活動并不具有明顯的效率。沈能、劉鳳朝(2011)[8]利用1992-2009年的面板數據和非線性門檻面板模型實證研究表明: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存在地區差異,“波特假說”在較發達的東部地區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而在較落后的中西部地區難以支持,原因是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之間呈現“U”型關系,只有環境規制強度跨越特定門檻值時,“波特假說”才能得到支持。
從環境規制工具分類視角對環境規制政策進行研究的相對較少。國外在這方面最早的研究是Weitzman (1974),他從理論上證明了當預期邊際減污成本曲線比預期邊際減污收益曲線陡峭時,采用稅收手段比單純采用命令與控制的手段更有利于企業。Magat (1978)、Milliman&Prince(1989)[9]經過研究發現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比如排污收費或可交易許可等,相較于命令控制型規制工具比規制者規定一個固定的排污量,更能刺激污染控制技術的發展。國內的相關研究起步較晚。馬富萍、郭曉川、茶娜(2011)[10]通過對201家資源型企業進行研究,發現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經濟績效和生態績效的正向影響都不顯著,激勵型環境規制和自愿性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經濟績效和生態績效都有顯著正向影響。王嶺(2012)[11]的研究表明環境信訪對工業三廢的影響是不顯著的。賈瑞躍、魏玖長、趙定濤等(2013)[12]運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方法,測算了2003-2012年中國各省份的生產技術進步指數,發現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對生產技術進步的作用并不顯著,市場激勵型的環境規制工具和以環境信息披露為代表的非正式環境規制對生產技術進步具有顯著地推動作用。原毅軍、劉柳(2013)[13]將環境規制分為費用型和投資型,通過對2004-2010年中國大陸30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費用型環境規制對經濟增長無顯著影響,而投資型環境規制顯著推進經濟增長。
綜上所述,目前對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的關系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幾點不足:一是大多研究是將環境規制視為一個整體,以一個綜合變量籠統地代表環境規制強度,而對環境規制類型進行區分并對不同類型的規制工具對技術創新的影響進行研究的文獻較少。二是對環境規制工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討論傳統的命令控制型規制工具和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即集中于顯性的環境規制,忽略了隱性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研究。基于以上研究不足,文章從環境規制工具的視角出發,將環境規制工具分為命令控制型、市場激勵型和隱性環境規制,以此分析各種環境規制工具對西部地區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并給出相應地對策建議。
三、 模型與變量
1.模型構建
技術創新的過程就是利用勞動、資本等創造出新知識的過程。文章著重考察環境規制對西部地區技術創新的影響,因此構建模型如下:

式(1)中,I表示技術創新的產出,K表示技術創新的資本投入,L表示技術創新的勞動力投入,ER表示影響技術創新的環境規制因素。為了比較各種不同環境規制工具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文章將環境規制工具分為命令控制型(STS)、市場激勵型(PW)和隱性環境規制(XF),因此技術創新的擴展函數形式為:

由于技術創新是一種特殊的生產,C-D生產函數在經濟理論和實證研究中被認為是一種很實用的生產函數,因此文章采用技術創新的C-D函數形式進行分析研究。
技術創新產出的C-D函數形式如下:

為了剔除異常項對數據平穩性的影響,本文對(3)式兩邊取對數,即得:

其中,i代表地區,t代表年份,a0,a1,a2,a3,a4,a5均為待估參數。
2.數據來源與變量說明
我國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西藏等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由于西藏部分年份數據缺失,考慮到數據的連續性,在計量過程中將其刪除。樣本期為1999-2012年。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下面對實證分析所涉及的變量作簡要說明。
(1)技術創新的度量
專利授權量能夠客觀地反映一個地區的原始創新能力和綜合科技能力,且在各種研究開發中,專利的數據較為全面,具有可得性,本文選擇專利授權量作為技術創新產出(I)的衡量指標。
(2)技術創新投入的度量
技術創新投入主要包括兩個指標:技術創新活動的資本投入(K)和勞動力投入(L)。資本投入用研究和開發機構研究及實驗發展經費內部支出來衡量,勞動力投入用研究與發展人員全時當量來衡量。考慮到數據的可比性,本文以1999年為基期,用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對研究和開發機構研究及實驗發展經費內部支出總額進行平減。
(3)環境規制的度量
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是國家根據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技術標準,直接對企業的排污行為進行規范和干預。在諸多環境政策中,三同時制度是中國首創的環境規制制度,要求開發建設項目的污染治理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是中國目前提高環境準入門檻、防止新污染源產生的有力手段,同時根據數據的可得性,文章將西部地區各省份歷年三同時執行合格率(STS)作為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指標來進行研究。
以市場為基礎的激勵型環境規制主要通過價格、稅收、收費、補貼及信貸等市場信號來影響排污者的行為決策。排污收費制度目前是中國最主要的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因此文章采用排污費(PW)來衡量各地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的力度。考慮到數據的可比性,文章以1999年為基期,用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對排污費總額進行平減。
隱性環境規制指的是內在于個體的、無形的環保思想、環保觀念、環保意識、環保態度和環保認知等。隱性環境規制主要是通過具有環保意識的個體或組織對影響環保的個體或組織行為進行直接的或間接地指引、規范、監督、協商或抗議來實現的。依據數據的可得性及代表性,參考王嶺的研究,文章采用環境信訪(XF)來衡量隱性環境規制力度。
表1報告了各統計變量的主要特征。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檢驗結果及分析
文章采用Eviews 6.0軟件進行面板數據回歸分析。首先使用靜態面板數據模型中的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通過Hausman檢驗,結果證明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考慮到面板數據中截面異方差問題,文章采用可以消除截面異方差性和同期相關性的“Cross-section SUR”廣義最小二乘估計方法進行估計。Hausman檢驗和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均見表2。

表2 Hausman檢驗和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
從回歸結果來看,調整為0.9980,總體模型擬合度很高,F統計量為4793.26,伴隨概率為0.0000,模型整體通過顯著性檢驗。
三同時制度和排污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774和0.1725,且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t值的伴隨概率均為0.0000),說明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和市場激勵性環境規制工具對西部地區的技術創新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的促進作用稍高于市場激勵性環境規制工具。出現這個結果的原因:一是由于西部地區的環境規制政策基本上是屬于以命令控制型為主導的環境規制模式類型;二是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的執行力度較高,表1中西部地區各省歷年三同時執行合格率的均值為92.94%就是證明;三是西部地區市場化程度較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的實施效果。總體來說,西部地區的顯性環境規制工具是有效的,能夠激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從而彌補因環境規制帶來的成本上升,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對技術創新能力的正向影響反映了西部開發以來西部的市場化程度在不斷提高。
環境信訪的回歸系數為-0.0171,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t值的伴隨概率為0.0019),說明西部地區的隱性環境規制不僅沒有促進西部地區的技術創新能力,還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這一是由于西部地區地處偏遠、相對于全國經濟發展落后、都市化水平低、教育水平落后、環境普及教育程度低等導致公眾環保意識水平低;二是由于西部地區以環保為主要活動領域的核心型民間環保組織的數量少、專業化程度很低,從而導致隱性環境規制對企業的排污行為沒有約束力,使企業失去了進行技術創新的動力;三是由于西部地區是多民族聚居地,長期以來在惡劣的自然條件和物質環境下形成的特定民族文化中,缺乏對生態環境保護問題的認識和理解,環保意識薄弱。
技術創新投入包括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3078和0.3646,,且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t值的伴隨概率均為0.0000),說明技術創新投入對技術創新產出具有顯著地推動作用,且勞動投入對技術創新的推動作用高于資本投入。這與丹尼森的研究結果一致,他認為技術進步中60%來自于教育的發展,而教育是勞動投入的主要途徑。相對于東中部地區而言,西部地區經濟基礎最為薄弱,教育發展最為落后,導致地方政府在技術創新資本投入方面遠遠少于東中部地區、人力資本匱乏,因此未來在西部大開發過程中,加大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促進西部地區的技術創新能力對于推進西部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五、基本結論與政策建議
文章利用1999-2012年我國西部地區1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數據,基于命令控制型、市場激勵型、隱性環境規制工具等視角實證分析了不同環境規制工具對西部地區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結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對西部地區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顯著高于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隱性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有顯著的抑制作用,技術創新投入包括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對技術創新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完善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政策
一是要適度提高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標準。中國的環境規制政策具有明顯的區域“差別管理”的特點,相對于東部地區,西部地區的能源、資源開發項目的環境準入條件明顯比較低,但結果卻是西部各地區單位GDP能耗指標值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適度提高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標準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對技術創新的誘發作用,提高西部地區的能源利用效率。二是要調整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政策,盡可能選擇有利于技術創新的政策,建立基于技術驅動型標準,并加強對特定科技創新的后果評價,以促進技術創新能力。三要加強西部地方政府尤其是環保行政部門的能力建設,給地方政府必要的經費、人員和其他物質保障,命令控制型工具才能具有有效實施的物質基礎,政府才能全面提高環境執法力度,刺激企業不斷進行技術創新。
2.加快西部地區的市場化進程建設,為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的有效實施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一般來說在信息不對稱的現實中,與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相比,市場激勵型的環境規制工具具有明顯的信息節省優勢,執行成本低,對政府的監管水平要求不高,同時可以不斷給企業提供強烈的刺激,讓排污者去發明或采用更為經濟和成熟的污染控制技術,并從發明和采用更低減污成本的污染控制技術中獲益,從而能夠更有效地促進技術創新。但是由于西部地區的市場化進程比較慢,市場化程度比較低,制約了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使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對創新的促進作用弱于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因此加快西部地區的市場化進程建設,制定和完善相關的市場法律法規,是提高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對技術創新促進作用的重要條件。
3.提高西部地區公眾的環保意識,發揮隱性環境規制的作用
針對西部地區隱性環境規制發展相對落后的現狀,今后首先應強化以學校、社區、家庭、組織、民族教育等途徑的社會環境教育來提高公眾的環保意識,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環境保護。其次,地方政府要通過進一步的環境立法將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具體化,確保公眾的環境知情權,完善公眾參與環境規制的激勵機制設計,為公眾參與環境保護提供條件,為隱性環境規制發揮作用奠定基礎。最后,積極的建立和發展民間環保組織,通過經費支持等途徑加強環保組織的能力建設,提高其專業化程度,鼓勵其參與政府的環境決策,刺激企業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
4.繼續加大技術創新投入
相對于東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受制于軟硬件條件的制約,市場化水平較低,缺乏吸引資本和優秀人才流入的環境,因此需要國家在技術創新投入方面給與更多的政策傾斜。一是西部地區應建立技術創新投入專項基金,穩定資金來源,形成以中央統籌為基礎、東、中部地區為補充、西部地區自力更生的資金投入模式;二是建立教育發展專項資金,繼續完善對口支援等政策,通過全面提高西部地區人口素質來促進技術創新能力,從而實現區域的協調發展。
[1]Porter M E.America's Green Strategy[J].Scientific American,1991(4):142-153.
[2]王鵬,郭永芹.環境規制對我國中部地區技術創新能力影響的實證研究 [J].經濟問題探索,2013(1):72-76.
[3]Berman E,Bui L T.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Oil Refineries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2001,88(3):498-510.
[4]趙紅.環境規制對中國產業技術創新的影響 [J].經濟管理,2007 (21).
[5]李強,聶銳.環境規制與區域技術創新——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9(4).
[6]馬海良,黃德春,姚惠澤.技術創新、產業績效與環境規制—基于長三角的實證分析 [J].軟科學,2012,26(1):1-5.
[7]Jaffe A B,Palmer J K.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A Panel Data Study [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7,79(4):610-619.
[8]沈能,劉鳳朝.高強度的環境規制真能促進技術創新嗎?—基于“波特假說”的再檢驗 [J].中國軟科學,2012(4):49-59.
[9]Milliman,S.R.and R.Prince.Firm Incentives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Pollution Control[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89,17(3):247-265.
[10]馬富萍,郭曉川,茶娜.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績效影響的研究—基于資源型企業的實證檢驗 [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1,32(8).
[11]王嶺.環境規制、公眾參與和環境污染治理—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J].國有經濟評論,2011(1):612-623.
[12]賈瑞躍,魏玖長,趙定濤.環境規制和生產技術進步:基于規制工具視角的實證分析 [J].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報,2013,43 (3):217-222.
[13]原毅軍,劉柳.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基于經濟型規制分類的研究 [J].經濟評論,2013(1):27-33.
(責任編輯:FMX)
Study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West Reg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WANG Xiao-ning1,2,ZHOU Xiao-wei1
(1.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Shaanxi 710062,China;2.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Xining Qinghai 810000,China)
Destruction and deteri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has became the biggest challenge in the western region.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the paper uses Western Regi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9 to 2012 to make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The results show that:command-control regulation and marked-incentive regulation both obviously accele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nd the effect of command-control regulation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marked-incentive regulation,recess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uses adverse effects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vestment obviously accele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Therefore, the western region in future should improve command-control regulation policies;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 process in western China,to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ked-incentive regulation;Raise the public'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to play the role of the recess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Continue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technology innovation,in order to fully stimulate the induced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in western China.
West Region;Environmental Regulati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Regional economy
F124
A
1004-292X(2014)05-0114-05
2013-12-25
王小寧(1981-),女,河南南陽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周曉唯(1963-),男,陜西西安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制度經濟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