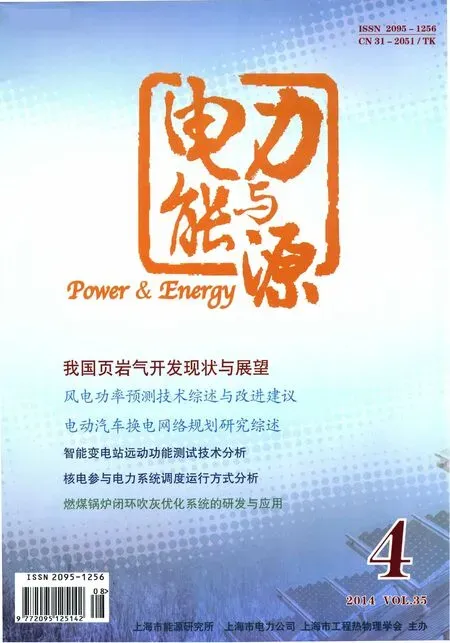我國頁巖氣開發現狀與展望
吳孟余
(上海市浦東新區新能源協會,上海 200136)
一次能源是指可供直接利用的能源,煤、石油、天然氣是一次能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天然氣是優質潔凈燃料,基本成分是甲烷,具有熱值高、燃燒產物對環境污染少的特點。因此,天然氣可應用于生活燃料和工業、交通運輸業燃料,如熱電冷分布式發電系統、燃氣空調、熱泵、燃料電池、汽車等方面。我國的天然氣資源量約為38.00萬億m3,占世界第十三位。天然氣的臨界溫度為190.58K,故在常溫下無法進行加壓液化。通常的液化天然氣(LNG)多存儲在溫度為112K,壓力為0.1MPa的低溫儲罐里,密度是標準狀態下甲烷的600多倍,體積能量密度為汽油的72%,十分有利于運輸和儲存[1]。
1 我國的頁巖氣資源及其分布
天然氣可分為常規天然氣和非常規天然氣。頁巖氣、煤層氣、致密型砂巖氣都屬于非常規天然氣。頁巖氣吸附或游離狀態聚集在頁巖中,主要成分是甲烷,是一種新的清潔能源。美國國家石油委員會基于Rognar的數據估算全球非常規天然氣資源量約為923.00萬億m3,其中半數為頁巖氣(約為456.00萬億m3)。
根據國內外對我國頁巖氣的評估,我國頁巖氣儲藏量十分豐富。但由于我國地質結構復雜,評估方法不一,因而評估出的儲藏量有所不同。根據2011年美國能源信息署(EIA)對33個國家頁巖氣資源估算得到,共計有187.00萬億m3,其中中國為36.00萬億m3,美國為24.00萬億m3。近期國土資源部對我國頁巖氣資源進行了初步地質勘探調查,經初步評價得到,我國頁巖氣可采資源潛力為25.08萬億m3(不包含青藏)。但這兩種評估方法都缺乏從地下頁巖氣樣品實測的含氣量數據。今后通過積累實測參數,該評估值的準確性將會提高。但這兩種評估方法都表明我國頁巖氣儲量豐富,占世界第一位。我國頁巖氣主要儲藏在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西北部)、鄂爾多斯盆地(華北)、松遼盆地(東北部)等地。
2 美國的頁巖氣革命
美國進行頁巖氣批量開采大約有40多年歷史。20世紀80年代,美國創新開采方法,即水力水平壓裂法,從而興起所謂“頁巖氣革命”。頁巖氣開采技術取得突破性進展后,引起競爭性市場形成,大規模商業化的成功,促使頁巖氣供應量猛增,從而導致價格驟降,使天然氣有希望代替煤炭、石油等傳統化石燃料。2007年,美國頁巖氣產量占天然氣總產量的比例為12%;2013年上升到35%;2030年將進一步上升到55%。其對相關企業的成本帶來巨大影響,北美的電力成本比中國低25%,比歐洲低50%,競爭優勢明顯[2]。
3 我國頁巖氣開發現狀
我國頁巖氣開發已經起步,但效益不高,產業發展較緩慢。我國對頁巖氣資源勘探程度低,雖然已經初步完成調查、評估、規劃,但由于地質結構復雜,尚需進一步大量的勘探實驗。2009年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出臺了《頁巖氣發展規劃(2011—2015)》,我國已經正式在重慶開始頁巖氣資源勘探。中石化在四川東北部、貴州東部、安徽南部等地,中海油在安徽、浙江等地,延長石油則在山西、延安等地,中聯煤在山西沁水盆地等地進行了局部重點勘探,初步摸清了我國部分有利區富有有機質頁巖分布,確定了主力層系,初步掌握了頁巖氣基本參數,建立了頁巖氣有利目標區優選標準,優選出了一批頁巖氣富集有利區。
2011年底,我國石油企業開展了15口頁巖氣直井壓裂試氣,9口見氣,初步掌握了頁巖氣直井壓裂技術,證實了我國具有頁巖氣開發實力。經國務院批準,2011年12月3日,國土資源部將頁巖氣作為獨立礦種管理,提出了“調查先行、規劃調控、競爭出讓,合同管理,加快突破”的工作思路,并且在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中設立“頁巖氣勘探開發關鍵技術”研究項目,成立了國家能源頁巖氣研發(實驗)中心,加大了研發力度。在對外合作方面,2009年,與美國簽署了中美關于在頁巖氣領域開展合作的講解備忘錄,就聯合開展資源評估、技術合作和政策交流制定了工作計劃。我國石油企業與殼牌公司簽訂富順—永川聯合評價協議,還與挪威、康菲、BP、雪佛龍、埃克森美孚公司建立聯合研究合作意向。
應該指出,在當前頁巖氣開發過程中,尚未全面實現大面積的頁巖氣勘探是阻擋我國進行大規模頁巖氣開采的重要原因,有必要完成適合我國國情的配套完善和低成本的頁巖氣開采技術體系。
4 我國開發頁巖氣資源的瓶頸
1)我國油頁巖資源勘探技術程度低,尚未在全國進行大面積資源勘探,對油頁巖資源的認識是很表淺的。此外,我國頁巖氣儲藏復雜,資源賦存條件差,且大多分布在地形復雜的區域,給認識資源、開采資源帶來很大的困難。
2)我國尚未掌握完善低成本的頁巖氣系統開采技術。如,我國僅初步掌握頁巖氣勘探開發的直井壓裂技術,尚未全面深入掌握水平井分段壓裂(水平井的鉆井完井、水力壓裂、含氣量測試)等開采技術。
3)頁巖氣開采需要豐富的水資源,而我國許多具有豐富頁巖氣資源的地區都缺水,如塔里木盆地、鄂爾多斯盆地等。在美國,根據頁巖構造特性,一次水力壓裂作業耗水超過1000萬L。而一口井的壽命可以達四五十年,需要龐大的水資源。
4)頁巖氣開采會產生廢水和有害的空氣污染物,嚴重影響環境。從長期來看,每百萬立方米的燃氣產量,會伴生3~13萬L生產廢水,而單井壽命可達到40年,那么單井生產廢水量可達到數百萬升,極易污染土壤、地表和地下水。同時,頁巖氣井的生產,會排放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和無機化合物(硫化氫)等有害于人體健康的氣體,如果不采取有利措施,將污染生產地的環境。
5)頁巖氣開采需要生產地具有完善水、氣管網,道路基本設施等。而我國大多數頁巖氣資源豐富地區都缺乏以上設施,要大規模開發難度大。
6)我國頁巖氣市場機制仍需進一步完善。民間資本準入準出機制未建立,天然氣價格尚未形成市場機制,稅收優惠政策力度不夠,關于頁巖氣開發政策還不完善。
5 對頁巖氣資源的開發展望
1)推進對全國頁巖氣資源深入全面的勘查。
2)借鑒美國開發頁巖氣資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積極開展頁巖氣開發技術研究。在吸收美國開采技術的同時,結合中國地質特點和具體國情,創新頁巖氣開采技術,重點解決我國西北地區缺水問題,以及在開采時如何對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氣污染予以防治。在美國,為了控制開發中的污染,甚至停止對紐約州和特拉華盆地的水力壓裂項目。賓夕法尼亞洲林區的鉆井活動就引發了土地破碎和生物多樣減少的傾向。
3)在成熟勘探區,先開展示范先導試驗,再總結經驗為大規模開采做準備。目前中石化重慶涪陵國家級示范區頁巖氣已開鉆27口,完鉆21口,已投入試采水平井10口,平均單井產量為15萬m3/天,商品氣量累計近7300萬 m3/天。“十二五”末期,涪陵年產頁巖氣33億m3。中石油長寧—威遠、昭通兩個國家示范區和富順—永川對外合作區完鉆頁巖氣評價井39口,累計實現商品氣量7000萬m3。勘探開發過程中發現,部分區塊前景遠超預期。國土資源部計劃2020年,優選20~30個頁巖勘探開發區,力爭實現150億m3至300億 m3的年產能[2]。
4)“十二五”期間,要基本完成頁巖氣資源評價,實現頁巖氣規模化生產。按照頁巖氣“十二五”規劃,到2015年我國頁巖氣要實現探明地質儲量6000億 m3、可采儲量2000億 m3、開采量將達到65億m3,到2020年頁巖氣開采量將達到1000億m3。然而,國土資源部最新統計報告顯示,2012年我國各地共鉆探頁巖氣井84口,其中僅兩口井有氣,而且還不是經濟氣。截至目前,全國共實施各類頁巖氣鉆井130口左右,其中實驗或勘探井129口,具有商業價值的為零。同時,據國土資源部內部的一項統計,去年頁巖氣產量約3000萬 m3,2013年預計可達2億 m3,算上2011年的開采量,近三年開采頁巖氣還不足3億m3,距離“十二五”規劃的開采目標還太遙遠。2014年要探明儲量達到1萬億m3,2015年產量達65億m3。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大頁巖氣勘探開發推進力度,繼續加強國家級頁巖示范區建設,盡快實現頁巖氣規模化、“工廠化”生產,加強科技攻關和裝備國產化,努力實現頁巖氣低成本開采,并盡快研究出臺政策、稅收等激勵措施[2-3]。
5)促進我國管網、氣站的基礎建設以及相關的服務業發展,同時也將促進油頁巖相關的技術發展。如杭州匯勘科技有限公司針對國內的開發需求和技術現狀,由美國引進的SES水平井地質導向軟件,是美國水平井導向領域市場上占有率第一的軟件。顯而易見,該類的頁巖氣開發相關技術的發展必然會提高頁巖氣本身的開發技術水平[4]。
6 結論
1)對全國非常規天然氣,建議全國統籌協調中央和地方,利用產學研,國企、民企各方面力量,以進行全面深入勘察。
2)同時加強自主開發,建立頁巖氣開發示范區,探索適合中國地質特點的開發模式,對全國非常規天然氣開發起到示范、引導和促進作用。
3)借鑒美國開發頁巖氣正反兩反面經驗,積極開展頁巖氣開采技術研究。在掌握先進的水力水平壓裂開采等技術基礎上,為解決頁巖氣富含地區缺水問題,需要創新開采技術,并且對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氣污染予以防治,通過創新形成中國特色的非常規天然氣開采技術。
4)促進我國管網、氣站的基礎建設以及相關的服務業發展,同時也將促進油頁巖相關技術的發展。
5)需要深化體制改革,不斷引入競爭機制。以頁巖氣礦業權管理制度改革為切入點,加快頁巖氣上游市場主體多元化。在進一步完善并落實好現有優惠政策的基礎上,比照煤層氣開發利用補貼政策,對頁巖氣開發利用給予支持。深化氣價改革,不斷完善天然氣價格形成機制,從長遠看應首先放開天然氣價格,建立反映市場供需關系的定價機制,由供求雙方通過市場機制確定天然氣價格。
[1] 顧安忠.液化天然氣技術[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
[2] 國家能源局.中國頁巖氣勘探開發最新進展[R].2013.12.4ECF(byy@ecfchina.com).
[3] 中研普華.2013年國內頁巖氣開采發展情況解析[EB/oL].中國 行 業 研 究 網,2013-11-13.http://w.w.w.chinairn.com.
[4] 潘繼平,王楠,韓志強,等.中國非常規天然氣資源勘探開發與政策思考[J].國際石油經濟,2011(6):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