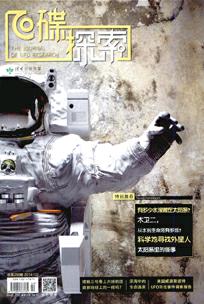自帶齒輪的蟬
三和君


1
最近,《科學》雜志刊登了一位英國教授的文章。他的孫女在花園里逮到一只很常見的鞘翅瓢蠟蟬幼蟲。這種瓢蠟蟬科的昆蟲在古北界(涵蓋歐亞大陸的北部,包括整個歐洲和中國秦嶺以北)非常常見,幼蟲可以跳得很高。在高倍數顯微鏡下,他觀察到這只幼蟲前后腿之間居然有一種半齒輪裝置,以保持協同性,這樣,就能夠用最小的力氣跳出最遠的距離。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在生物身上發現到齒輪裝置。
齒輪和車輪算是同一類傳動裝置,所以這個發現也部分回答了很久之前的一個疑問:為什么其他生物沒有類車輪裝置?科學家不肯承認自己的發現不足,所以只好絞盡腦汁去想為什么不能。我印象深刻的一個答案是,車輪效益的發揮在于道路的有無。如果沒有道路,車輪還不如四蹄跑得快。可是我們也有大草原、大平原、大沙漠啊!這個發現證明,道路確實是一個限制,但是進化,或者說環境的壓力,可以讓生物脫離人類的視野,發展出類似的裝置。
蟬科其他昆蟲也有類似裝置。這些裝置起源于什么時間?我們一無所知。但是這個研究給我們更大的啟示——我們所觀察的,乃是人類視野下的運動,所以會不自覺地帶入人類的視角,談到車輪和齒輪的時候,就只能想象出車輛奔馳在大道上的景象,而無法考慮為什么只要一個輪子、半個輪子呢?
所有的生物都是DNA和RNA所控制的蛋白質生物,所以,所有的生物都使用類似的物理化學過程。大多數生命是以太陽能為驅動,用幾十億年的時間進化出來的一套精妙的能量傳遞和轉換系統。它應用了所有的手段,讓所有該有的化學反應都能在一個很狹窄的溫度區間內(0℃至50℃)發生,而且這些反應能夠環環相扣,以最節約和最方便的方式完成。人體需要非常多的能量來維持這個低溫反應系統的運轉,即使你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思考。
為什么反應溫度必須局限這個溫度范圍?因為碳基生物的DNA和蛋白質只有在這個溫度才有活性。數億年的進化不斷鍛煉這一套化學反應,將它們包容在某一個肉身內,以更完美的方式驅動爪牙的萌發、口齒的磨礪、捕食、交配。不成功的物種只會靜悄地死去,永遠不知道失敗的原因,只是因為自己體內的某一個酶反應速度比競爭者慢一點。
但是在工業社會,這種反應不再受限于溫度和壓力,以及環境,所以以目前工業界的眼光打量自然界的這些精妙反應,就會有“棄之可惜,食之無味”的感慨。在生物體內的小鍋小碗里弄出來的手工定制,未必適合現代生活的大規模生產。這就導致目前我們所看見的“仿生學”就像驢子前面的胡蘿卜,或者猴子眼前掉到水底的月亮。
不過這也有一個好處,就是時時刻刻提醒人類的眼界有多么宏大,思維就會有多么狹隘。這個狹隘來自人類對自己的過分自信,無論是智慧設計論,還是拉馬克進化論,背后都以現有的生物結構完美為基礎。所以很多挑戰達爾文進化論的第一個質問就是,半個眼睛有什么用處?提這種問題的人,所想象的不是許多生物沒有眼眶、眼皮,只有若干感光細胞的某種器官,而是直接剝掉眼皮、視網膜等結構的人眼。鞘翅瓢蠟蟬的出現是還擊他們的絕好證據,半個輪子又有什么用呢?只有幼蟲才有的半個輪子又有什么用處?而且這種輪子的功能并非傳動,而是制控——進化的開始可能根本連一個輪子都沒有,只有幾個突起。而最簡單的突起,提高了跳躍的效率,使得擁有這種基因的生物跳得更遠,更容易生存。
嚴肅說來,并沒有所謂的仿生學——我們就是所有生物中的一個,我們跟其他動物分享著或近或遠的血緣,以及基本一致的生理代謝,我們不過是在研究自己而已。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狹義的“仿生”帶給我們的更多的是哲學的思考,而非實踐的啟發。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