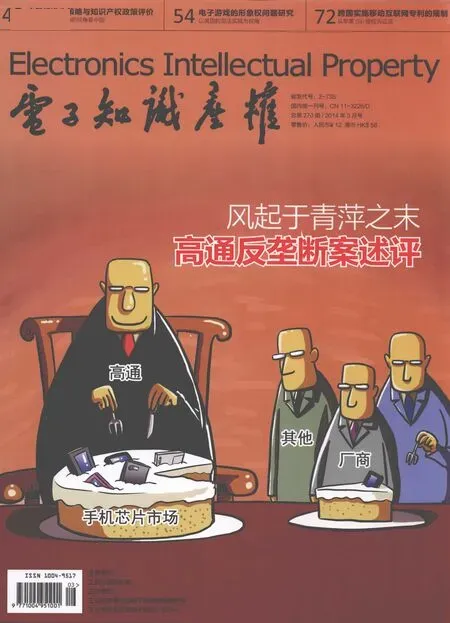首字為“國”字商標是否具有不良影響的判定評析國臺酒業集團有限公司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商標駁回復審行政糾紛案
陳志興 /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對帶“國”字頭但不是“國+商標指定商品名稱”組合的申請商標,應當區別對待。對使用在指定商品上不存在直接表示商品的質量特點,不會引發產源誤認的標志,不應認定屬于“不良影響”的情形。
案情介紹
第6874981號“國臺GUOTAI及圖”商標(簡稱申請商標)于2008年8月1日由貴州仁懷茅臺鎮金士酒業有限公司提出注冊申請,指定使用在第33類燒酒、果酒、白蘭地等商品上。在商標評審期間,申請商標經核準轉讓給國臺酒業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國臺公司)。
2011年9月8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簡稱商評委)作出第20489號決定,認定:申請商標中的“國臺”常用于海峽兩岸的政治、經濟往來事務活動中,將其作為商標使用易產生誤購誤認,從而產生不良影響,故決定申請商標予以駁回。
國臺公司不服第20489號決定,訴至法院。
法律分析
一審法院認為,“國”對于一般消費者而言,通常代表“國家的”等含義,申請商標指定使用在燒酒等商品上,易使相關公眾認為其指定使用商品的品質得到了國家相關機構的認證,其注冊使用將有損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從而造成不良影響,故判決維持第20489號決定。
國臺公司不服,提起上訴,并提交了五組證據,以證明其對申請商標的宣傳、使用情況。二審法院另查明:2010年12月20日,國臺公司經轉讓取得第1579793號“國臺”、第5235600號“金國臺”和第5235601號“國臺王”(簡稱“國臺”系列商標)在第33類酒(飲料)等商品上的專用權,且該三商標至今仍為有效注冊狀態。
二審法院認為:“國”對于一般消費者而言,雖然具有“國家的”含義,但是“國”與其他的漢字組合,會產生不同的意義。“國臺”并不會使一般消費者在其指定使用的第33類燒酒等商品上與“國家的”等含義產生聯系。國臺公司新提交的證據能夠證明其長期使用“國臺”商標在白酒行業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顯著性。同時,申請商標系對“國臺”系列商標的延伸使用,應當予以核準注冊。據此,二審法院判決撤銷一審判決、第20489號決定,由商評委重新作出決定。
法官提示
根據《商標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八)項的規定,有其他不良影響的標志不得作為商標使用。本案的爭議問題比較簡單,即指定使用在第33類燒酒等商品上的申請商標是否具有不良影響。
一、首字為“國”字商標與“不良影響”的關系
在《關于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10]12號)中,最高法院明確指出,人民法院在審查判斷有關標志是否構成具有其他不良影響的情形時,應當考慮該標志或者其構成要素是否可能對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民族等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產生消極、負面影響。如果有關標志的注冊僅損害特定民事權益,由于商標法已經另行規定了救濟方式和相應程序,不宜認定其屬于具有其他不良影響的情形。可見,該意見已將“不良影響”條款的適用明確限定為絕對事由的情形。但是,在商標授權確權司法審查實務中,該條款在法律適用上的爭議并沒有因為該意見而終止。
在為數不少的適用“不良影響”條款的案例中,其法律適用的核心爭議在于,商品產源誤認是否屬于《商標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八)項所指的“有其他不良影響”的情形。理論上來講,商標最基本的功能就在于產源識別,如果將僅是易引起產源誤認的標志適用《商標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八)項“有其他不良影響”予以調整,《商標法》其他條款的存在將沒有任何的意義。但是,在具體的商標司法審查實踐中,其在行政訴訟程序中僅涉及到“不良影響”條款的法律適用問題,如果相關的商標注冊行為不能通過該條款得到規制,勢必會影響到商標產源識別功能的正常發揮。因此,在商標司法審查實踐中,容易誤導公眾,使公眾對商品的質量等特點產生誤認的標志,可認定屬于“有其他不良影響”的標志,不得作為商標使用。
由于商標具有指示商品來源的作用,商家在選擇商標標識的過程中,一直以來都有強烈的“國”字情結。其試圖依靠商標標識中的“國”附著的品牌效應,贏得競爭優勢和商業價值。但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過多過濫的“國”字商標也導致對該商標所指示商品的質量、品質等產生誤認,進而引發消費者的混淆和誤購。為此,首字為“國”字商標的使用和注冊情況就非常有必要加以規制。
2010年7月28日,國家工商總局發布《含“中國”及首字為“國”字商標的審查審理標準》,規定:一、對“國+商標指定商品名稱”作為商標申請,或者商標中含有“國+商標指定商品名稱”的,以其“構成夸大宣傳并帶有欺騙性”、“缺乏顯著特征”和“具有不良影響”為由,予以駁回。二、對帶“國”字頭但不是“國+商標指定商品名稱”組合的申請商標,應當區別對待。對使用在指定商品上直接表示了商品質量特點或者具有欺騙性,甚至有損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或者容易產生政治上不良影響的,應予駁回。
本案中,申請商標由漢字“國臺”、拼音“GUOTAI”及圖形組成,其中的漢字部分“國臺”易于認讀,屬于商標的主要部分,其并非屬于“國+商標指定商品名稱”的情形。對于指定使用在第33類“燒酒”等商品上的申請商標而言,其主要識別部分“國臺”并不會使一般消費者產生“國家的”、“最好的”等含義,進而引發對其指定使用商品的質量、產源等的誤認,不屬于《商標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八)項所指“不良影響”的情形。
二、申請商標的使用情況與“不良影響”的判斷
在《關于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10]12號)中,最高法院指出,對于使用時間較長、已建立較高市場聲譽和形成相關公眾群體的訴爭商標,應當準確把握商標法有關保護在先商業標志權益與維護市場秩序相協調的立法精神,充分尊重相關公眾已在客觀上將相關商業標志區別開來的市場實際,注重維護已經形成和穩定的市場秩序。基于對該“司法政策”的理解和適用,商標司法審查實踐中,常常會出現原告或者第三人新提交證據的情形,以證明訴爭商標或者引證商標經使用獲得的知名度。
我國商標授權確權司法審查制度采取的行政訴訟的模式,即對商評委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而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行政訴訟程序中新提交證據并非商評委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事實依據,因此,對于該部分證據在一般情況下,法院是不予采納的。但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02]21號)第五十九的規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證據,原告依法應當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訴訟程序中提供的證據,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納。考慮到訴訟經濟原則及避免行政相對人因不能舉證導致其注冊商標被撤銷,而無其他救濟途徑的情況發生,對行政相對人在行政訴訟階段補充提交的證據不宜簡單、機械的一律不予采納。據此,二審法院采納國臺公司在二審程序中新提交的證明申請商標宣傳、使用情況的證據,是符合法律相關規定的。
二審法院認為,該部分證據可以證明,在相關公眾中能夠形成“國臺”商標與國臺公司的唯一對應關系。但是,值得思考的是,根據《商標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八)的規定,有“其他不良影響”的標志不得作為商標使用。既然這樣,對于該類標志來講,不論其經過使用獲得多大的知名度,亦不能使用獲得禁止使用的豁免權,這一點區別于顯著性因素。因此,二審法院的此部分判理似乎值得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