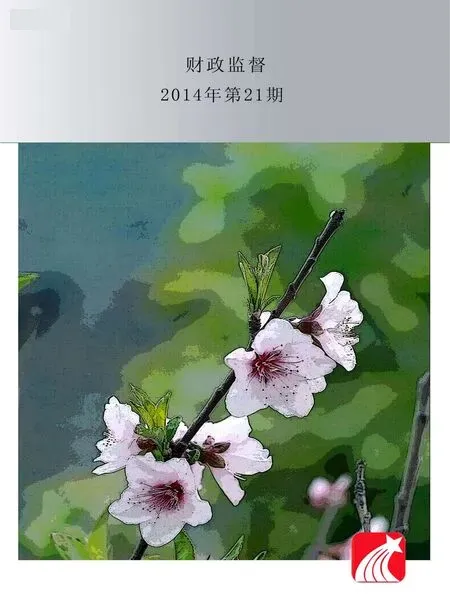合理劃分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的思考
●曾康華 李思沛
合理劃分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的思考
●曾康華 李思沛
編者按: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明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2016年基本完成重點工作和任務,2020年基本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會議確定了重點推進三個方面的改革:改進預算管理制度、深化稅收制度改革、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構建科學合理的中央與地方政府關系是現代財政制度的重要標志,也是今后我國財稅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對此,我國各級政府和財政學者進行了長期而系統的研究和探討。結合新的會議精神,本期專題圍繞“科學合理劃分政府間事權與支出責任”邀請相關財政學者展開探討,為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提供參考。
中共中央政治局 2014年 6月 30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會議明確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稅體制在治國安邦中始終發揮著基礎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并且要求,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2016年基本完成重點工作和任務,2020年基本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這次會議是繼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后,對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方案進行整體部署的又一次重要會議,標志我國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任務和目標已經確定,必將對建立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可持續的現代財政制度產生深遠和重大的影響。
2014年是我國實施分稅制改革20周年。自1978年改革開放至20世紀80年代末期,我國財政體制的改革一直遵循“擴權讓利”的思路,導致20世紀90年代初期出現了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和全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即“兩個比重”下降的局面。例如,1993年我國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為22.02%,全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12.3%,嚴重削弱了政府的財政職能。為提高政府財力集中度和加強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1994年我國推行了分稅制改革,這一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提高“兩個比重”。時至今日,國家的經濟總量大幅度擴張,政府財政收入快速地增加,例如2013年,全國財政收入達到129143億元,中央財政收入達到60173.77億元;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達到46.6%,全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達到22.7%。可以說,政府財力集中度得到提高,提高“兩個比重”的目標也基本實現。
但是,隨著分稅制的實施,分稅制運行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主要表現之一就是地方政府財力與支出責任嚴重不匹配。從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角度看,富裕地區可支配財力大大多于履行支出責任的基本需要,而欠發達地區可支配財力大大低于履行支出責任的基本需要,造成了區域間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盡管在進行分稅制改革的同時,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也相應建立起來,而且這一制度對地方政府財力起到了很大程度的調節作用,但由于分稅制這一體制因素一直持續地對地方政府財力與支出責任的匹配產生深刻地影響,造成了欠發達地區財政收支矛盾的加劇,導致許多地方財政陷入困難局面,嚴重制約了地區間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推進。實施分稅制的實踐表明,現實中存在著政府支出責任的層層下移,而財力層層集中的趨勢。分稅制實施的初期只是比較明確地劃分了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的財力,對政府支出責任并沒有予以清晰的界定,況且,隨著中國經濟強勁增長,各級政府財力尤其是中央政府財力得到了很大增強,但由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所引發的財政模式轉型,即由“建設財政”向“公共財政”的轉型,應當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進行適時調整,事實上這種調整嚴重滯后,這樣就造成了地方政府行使事權的支出責任與財力不相匹配的問題。
毫無疑問,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改革對我國政府財力與支出責任匹配關系產生了持續而深遠的影響,盡管此后相繼出現了對政府“財力與事權匹配”和“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等表述的演變,實際上這反映了實施分稅制以后,“財”、“事”、“責”關系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政府間進行動態調整的過程。
對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與“事”的權利和責任劃分,1994年以來我國實施的財政體制一系列改革措施,先后提出了“財權”、“事權”、“財力”、“支出責任”等概念,表面看是名詞的表述發生變化,實際上這里面反映了政府實施財政體制改革思路的調整。當然,對財政體制改革的思路和脈絡進行梳理和調整是必要的,這也反映人們對財政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不斷深化,有利于認清政府財力與支出責任的匹配關系,從而把握政府財力與支出責任匹配的內涵和動態變化的特征。
我國1994年分稅制改革所確立的基本原則是 “事權與財權相統一”,整個20世紀90年代在處理中央和地方政府“財”與“事”關系時,一直遵循這一原則。21世紀以來,一方面,我國實施了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政府采購、取消預算外資金等一系列的預算管理體制改革措施,構建起了公共財政體系的基本架構;另一方面,在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權和財力關系方面,改變以往表述,要求遵循“財力與事權相匹配原則”,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對中央與地方財力與支出責任的表述進一步完善,仔細梳理不難發現其內涵是一脈相承的。多年來,關于中央與地方關系所涉及的核心問題仍然聚焦在中央與地方在財力、事權方面如何配置才合理,這也是今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必須解決的問題。
從發展的視角看,財力與支出責任又處在不斷地變化之中,這種動態的變化要服從一定時期政府職能的變化。也就是說,當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生變化時,政府的職能就要發生相應變化,政府職能的這種變化反映在財政支出上,就是政府支出責任的變化,而政府財力是否適應政府支出責任的變化,這就是政府財力與支出責任相匹配的問題。
事實上,政府間的權責關系非常復雜,主要原因在于其內涵非常豐富而且影響該關系的因素有很多,如各級政府權力與事務的劃分、支出責任的劃分、事權與支出責任是否適應、財力與支出責任是否匹配等都涉及政府間的權責關系。政府間權責關系最直觀的表現就是政府層級的設置。而政府層級的多少可能受政府管轄區域的大小、政府管理方法與理念等因素的影響。如果管轄區域大,就會造成交通不便、通訊不靈、政令不暢等問題,往往導致政府層級設置較多;政府層級多就很容易產生政府支出責任中的諸多問題,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政府間的支出責任不容易劃分清楚。
在我國中央與地方的權責關系中,事權與事責往往并非同一概念。例如,某級政府擁有某項事權,并不是指該級政府就要獨享此權利,應該說是該政府擁有了行使這項事務的責任,即應該對之負責。然而,為之負責是一方面,而所負之責是否到位又是另一方面。換句話講,若低層級的政府有承擔事務的責任而高層級的政府有掌控這項事務的權力,這時事責與事權就可能出現分離。因此,很有必要將事權與事責進行區分。
對地方政府來講,其事權是為當地居民提供基本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然而由于多級政府設置而出現的責任推諉扯皮的現象,常常是事權掌握在上級政府而事責由下級政府承擔所致。尤其在省級政府與地市級政府之間,它們的事權、事責就較難達到一致。“經濟人”原理可以解釋這一現象:為了實現本級政府的利益最大化,一方面,該政府往往會向上級多索要事權而少承擔責任;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下放事權而傾向多分配事責給下級政府。這樣一來,就會導致省級政府與地市級政府擁有本不該有的事權或沒有盡到本該負的責任,即事權錯位、事責缺位。可見,處于中間層級的政府是我國政府權責最不易劃清的一級政府。因此,從省級政府的角度來研究政府財、權、責關系十分必要。
支出責任是指在現有政治環境影響下,某一級政府為了實現政府管理目標而需要承擔的財政支出。政府行使事權、履行事責通過提供公共服務來實現,提供公共服務是通過財政支出來表現。政府支出責任的衡量就是政府財力支出的大小,是表現政府事權、事責的具化形式。因此,支出責任是政府事責的量度,或者說支出責任可以看作政府事責的具體表現。
那么,如何量化支出責任呢?實際上,量化政府的支出責任存在多個視角,也有多個指標加以衡量。本文認為,從政府預算科目來看,以政府預算項目的設置作為衡量政府的支出責任范圍。那么,遵循該思路,政府履行支出責任的最后考量是政府決算支出金額,而政府想要履行支出責任的愿望體現在政府編制的預算金額上。所以,本文主張用預算執行率來衡量政府履行支出責任的程度,這里所指的預算執行率通常是指決算數與預算數之比,如果預算執行率小于100%,說明政府沒有完全履行支出責任,財力沒能有效配置,二者匹配關系較弱;如果預算執行率等于100%,說明政府完全履行支出責任,財力得到有效配置,二者關系匹配;如果預算執行率大于100%,說明政府超額完成履行支出責任,財力不能支撐支出責任,二者匹配關系有缺陷。能夠驗證其財力用于執行事責后是否達到預設標準,即政府財力是否得到了有效配置。因此,它可以作為衡量二者之間匹配程度的一個指標。
事權與支出責任的關系可以從事權與事責的關系進行推理。在通常情況下,政府事權與事責是一致的,而中間層級政府事權與事責較容易發生分歧;支出責任是行使事責的量度。省級政府與地市級政府的事權與支出責任往往不易相適應,這也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 “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體制”的原因之一。因此,明確事權,并使支出責任與事權相適應,有助于清晰界定政府職責、明確劃分支出責任界限,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與資源使用效率。
政府財力是政府通過行使征稅權或通過其他方式而獲得的財政資金。從獲得收入的途徑劃分,可以分為自有財力和轉移財力。政府財力是履行政府職責所需的經費,是政府可支配的財力。地方政府的財力與事權往往是不匹配的關系,因為地方政府通過稅收獲取的財力與稅種有關,外溢性較大的稅種由于會造成地區間稅負不公而常常由中央政府征收,這樣一來,地方政府征收的稅種就較少,稅收收入自然也少,這就容易形成財力與事權不匹配的情況。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強調,政府財政應遵循“財力與事權相匹配原則”。而在實際情況中,地方政府承擔事權少卻承擔事責重,其事權與財力匹配方面存在的問題不突出,反而事責與財力是否匹配更值得關注。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事責重則需要較多的財力供給,若財力供給不足,就需要上級政府進行轉移支付。但在轉移支付過程中,如果中間還有一級政府的話,往往被中間這一級政府以事權之名截留資金,而與事權對應的事責沒有發生變化,這樣一來,不但沒能使基層政府財力得到適量補充,達到與其事責相匹配的財力水平,反而還讓其事責變得更重了,加重了基層政府財力與事責的不匹配。因此,我國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政府財力與事責的匹配,把事責具體到各級政府,就是要解決政府財力與支出責任的匹配問題。
盡管對于如何將中央與地方“財”與“事”協調統一起來應遵循的原則的表述不斷發生變化,但其涉及的核心問題并沒有改變,就是政府要履行的事務要有相適應的財力相匹配,如果政府的支出責任劃分合理,政府財力安排能夠保證政府充分履行事務的職能,就說明政府財力與支出責任是相適應的。
在新的形勢下,要使市場機制發揮資源配置的主導性作用,就必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只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合理劃分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才有最基本的保證。如果不能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職能就會模糊不清,在政府職能不清的情況下,就難以合理劃分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
當然,如何合理劃分政府間的事權和支出責任,關鍵在于界定政府的職責范圍,只有在明確了政府的職責范圍后,才能在政府間合理劃分事權,而各級政府事權的劃分又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總是會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變化而變化。所以,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是一個永恒的主題,也是服務一定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客觀必然。■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