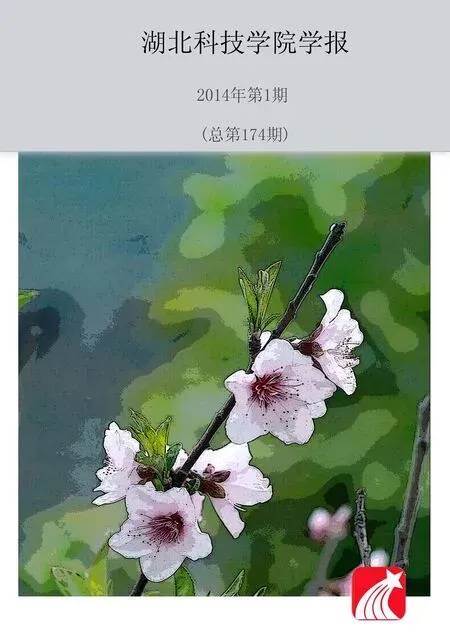對話瓦爾登湖
——巴赫金對話理論視域下重釋梭羅的對話*
廖中慧
(湖南大學 外國語與國際教育學院,湖南 長沙 410012)
*收稿日期:2013-09-29
引言
被愛默生稱為“思想上與肉體上的獨身漢”的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是19世紀美國超驗主義作家中頗負盛名的一位,他以一本田園牧歌式的《瓦爾登湖》享譽世界文壇。在眾人皆醉于物質的世態下,他獨醒著。他追求生活簡單化,認為物質生活是次要的,精神生活才是最重要的,越是簡單的生活越是能提煉人生的真理。在遷居瓦爾登湖的兩年多時間里,他在淡泊中明志,在寧靜中致遠,以獨特的思維、敏銳的眼光和幽默機智的筆調書寫了一段天人合一的佳話。
《瓦爾登湖》是梭羅與自然的一部對話錄。本文借用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分析《瓦爾登湖》中梭羅與自然的對話,闡述對話的積極意義及影響,從而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提供一些啟示。
一、巴赫金及其對話理論
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巴赫金(Ъахтинг,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1895—1975)是前蘇聯著名文藝學家、文藝理論家、批評家、蘇聯結構主義符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巴赫金一生理論成果頗豐,對話理論是他最著名的理論成果之一。自20世紀60年代被重新發現后,他的對話理論引起文論界的廣泛關注,一時形成對巴赫金的研究熱潮,而他也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對話理論是巴赫金哲學思想的重要內容,他將該理論應用到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作品的研究當中,形成了復調小說理論以及狂歡化文學等思想。他強調對話是生存的必要條件,一切手段都以對話為最終目的,單一的聲音并不具有意義。人們對真理的追求是以對話為橋梁展開,并在對話的過程中發現的。
巴赫金同時辨別了對話關系和對語關系。在他看來,相比實際生活中的對語關系,對話關系更具廣泛性與復雜性。只要兩個表述涵義相通,無論時間與空間相差幾何,他們仍具有對話關系。他指出對話關系幾乎無所不在,貫穿于整個人類語言。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為例,細致地研究了作者與主人公以及個中人物的對話關系。而今隨著文論的發展,批評家提出了將對話理論擴展應用到不同領域,而不限于以人類語言為媒介的對話關系。著名的生態文學批評理論家帕特里克·墨菲( Patrick D.Murphy)就曾提出,“巴赫金努力定制非正常性對話( 或個人習語) 的嘗試應該拓展到‘非人類語言’ , 例如包括動物和自然在內的對話中。”
二、梭羅與自然的對話
《瓦爾登湖》被視為生態文學的經典之作。梭羅移居瓦爾登湖畔的兩年多時間里,與自然對話,思考著人生的真理。其實,自生態危機以來人們就積極主張與自然對話,但是在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大流下,收效甚微。到底如何才能有效地和自然對話?或許,我們能從梭羅那里得到一些啟示。
在梭羅對話自然的過程中,首先他將自然視為一個對話主體,獨立于人類之外的一個平等的他者。這一點也是符合巴赫金提出的對話原則的。巴赫金認為,一個平等自由的他者是對話的必要前提。在這里他者和平等是兩個關鍵詞。所謂他者,是相異于我的主體的存在,無論是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上。巴赫金將對話性視為事物本質,而對話性以他者的存在為先決條件,一個異于我的存在才能促使對話的發生。其次是平等。在巴赫金看來,對話是平等意識的對話,沒有平等,對話無所展開,真理無處可尋。只有在平等自由中,不同的意識才能展開“旋風般的運動”,才能開始意義的創生。
平等的他者對于指導人與自然的對話同樣具有意義。自18世紀逐漸興起的啟蒙主義思潮把人的自由和解放作為最高追求。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加上工業革命在改造自然方面不斷取得成功,人們將自己與自然對立起來,人類中心主義風靡一時。直到自然展開“復仇”,生態危機愈見嚴重,人們開始反思,由此生態文學的各個分支發展起來。
梭羅似乎洞察先機,預見了生態危機的隱患。于是他拿自己做實驗,住進瓦爾登湖旁的森林里,希望能找到化解生態危機的可行之道。當其他人類的同伴或亂砍濫伐,或從飛鳥胸脯或巢里掠奪羽毛,對自然予取予求時,而梭羅將自然當做自己的同類一樣尊重。他與鳥雀為鄰,但并不以自己為中心,去捕捉一只鳥把它關起來,而是把他自己“關進了它們的鄰近一只籠子里”,與鳥雀平等共處。他在大自然里自由來去,“成了她自己的一部分”。他說道,“是什么藥使我們健全、寧靜、滿足的呢?不是你我的曾祖父的,而是我們的大自然曾祖母的,全宇宙的蔬菜和植物的補品,她自己也是靠它而永遠年輕,活得比湯麥斯·派爾還更長久,用他們衰敗的脂肪更增添了她的康健。”在梭羅心中,自然就是我們的同類,是我們的曾祖母,她供給蔬菜瓜果,賜予陽光雨露滋潤我們,像一個曾祖母一樣關愛著人類。梭羅將自然指稱作“她”,并主張平等尊重,可謂是現代女性生態主義以及深層生態學的先驅,同時也說明只有將自然視作平等的他者,才能與之展開對話。
其次,梭羅是怎樣與自然對話的呢?自然的語言不同于人類的語言,所以兩者間的交流方式也會有所不同。梭羅與自然的對話的媒介是對自然的審美移情。自然用自己獨特的語言表達自己,這一活動刺激著梭羅的審美觀照,促使他將自己置于自然的位置上,感自然之所感,想自然之所想,與自然合二為一,理解自然,然后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闡釋自然,回應自然。巴赫金在《論審美活動中的作者與主人公》中提到,“審美活動的第一個因素是移情:我應體驗(即看到并感知)他所體驗的東西,站到他的位置上,仿佛與他重合為一。”任何情況下,在移情時候都必須回歸到自我,回到自己外在與他者的位置上。只有從這一位置出發,才能把握移情的材料。梭羅在溫和的雨絲中感受自然無限的友愛,甚至每一支小小的松針都是他的朋友,他覺得自己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梭羅寫道,“太陽,風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寫的純潔和恩惠,他們永遠提供這么多的康健,這么多的歡樂!對我們人類這樣地同情,如果有人為了正當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會受到感動,太陽黯淡了,風像活人一樣悲嘆,云端里落下淚雨,樹木到仲夏脫下葉子,披上喪服。難道我不該與土地息息相通嗎?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綠葉與青菜的泥土嗎?”在這一段描述中,梭羅移情于自然,先將自己化身自然,感受自然所為。自然以陽光雨露滋潤萬物,哺育萬物生長。當人類悲痛時,太陽也黯淡,風也悲嘆,云也表達著自己的悲傷。它們和人類心心相印,為人類提供康健,帶來歡樂。在理解自然為人類所做的之后,他回到自己位置上,開始思考,自然無聲而潤萬物,對人類這樣同情,“難道我不該息息相通嗎?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綠葉與青菜的泥土嗎?”梭羅發出了與自然一體的感嘆,同時,他也引導著讀者思考,在這樣一個無私的自然面前,我們為一己之私對自然的恣意破壞,是不是很卑微,很不道德的呢?
梭羅在感自然所感時,也痛自然所痛。有一位農民紳士,為增加自己的財富,在嚴冬季節雇人耕地,梭羅心痛地感嘆道,“他剝去了瓦爾登湖的唯一的外衣,不,剝去了它的皮,而且是在這樣的嚴寒的冬天里!”人類的無情表現得淋漓盡致。
最后,梭羅在瓦爾登湖畔獨居兩年后就離開了,但是他與自然的對話卻遠未結束。在巴赫金的對話理論里,對話具有未完成性,存在就意味著對話,因此,對話不可能、也不會結束。在《瓦爾登湖》中,梭羅也是這樣暗示的。在季節的安排上,梭羅是7月搬進森林小屋的,也就是以夏季為開端,梭羅描寫了多雨的秋季,寂靜的冬季,最后以瓦爾登湖的春天,萬物復蘇為結尾。而季節是無限循環,沒有盡頭的,春去秋來,梭羅仿佛在這里埋下伏筆,暗示人與自然的對話也沒有終結,只要人類社會還在,只要自然尚存,那它們之間的對話就是未完成的。此外,梭羅在結束語的最后一段話也耐人尋味。“可是時間盡管流逝,而黎明始終不來的那個明天,它具備著這樣的特性。使我們失去視覺的那種光明,對于我們是黑暗。只有我們睜開眼睛醒過來的那一天,天才亮了。天亮的日子多著呢。太陽不過是一個曉星。”曉星這里指的是金星。金星本身是不發光的,它的光亮是太陽照射的結果。在日落西山時,太陽余暉灑在金星上,在西面天空,稱為昏星或者長庚星,日出之前它轉至東面天空,稱作晨星或者啟明星,而它通常都是在日落稍后和日出稍前達到最亮。可以說,它東西移動,既開啟了黑夜又預示著黎明,周而復始,無始無終,而且星星本身就是永恒的象征。黎明對梭羅來說是思考的最佳時機,“詩歌與藝術,人類行為中最美麗最值得紀念的事都出發于這一個時刻”,曉星帶來的無數黎明也暗示人們對真理的追求和思考也沒有盡頭。
三、對話的積極意義及影響
梭羅將自己兩年多與自然對話的深徹感悟與人分享,字字閃光,句句真情。盡管當時能夠欣賞的人寥寥無幾,但是他播下了一顆綠色的種子,為人們打開了生活的另一扇窗,引領人們思考生活的意義,同時也使美國的超驗主義運動從理論走向實踐。
也許是歷經不被世人所理解的冬天,梭羅播下的綠色之種在20世紀以來花開燦爛,影響深遠。梭羅的綠色思想對美國的環境傳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有學者說,“亨利·梭羅是美國環境觀念變遷史上的一座豐碑,他上承塞爾波恩的懷特和林奈,下啟約翰·繆爾和奧爾多·利奧波德,他的出現標志著美國人的環境觀念已經擺脫了簡單地追溯歐洲浪漫主義者進行描述和哀嘆的境地,從更高的哲學層次去思考人與自然關系,是美國環境意識和文化觀念走向獨立和成熟的標志。”梭羅半隱士的生活方式在當代引起了共鳴,引領人們紛紛回歸自然,返璞歸真,尋找本心。其次,梭羅的思想極大地促進了生態運動的發展,成為該運動最主要的理論來源之一,而梭羅本人也被稱西方學者稱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位自然主義者與生態保護主義者,是現代環保運動的“圣人”。他闡述的荒野思想也成為美國荒野保護意識的源泉,影響了包括“深層生態學的桂冠詩人”加里·斯奈德在內的眾多文人墨客,指引人們不僅從心靈上走向荒野,也從實踐上走向荒野。
結語
在物質生活綁架了精神生活的今天,人們該怎么松綁自己的靈魂去尋找最初的美好和幸福?在梭羅的《瓦爾登湖》中便可以找到想要的答案。梭羅以自己與自然兩年多的對話經驗啟示我們,生活越是簡單,幸福越是純粹,物質的煩惱不過是庸人自擾,不如回歸自然,回歸本真。
《瓦爾登湖》是一部梭羅與自然的對話錄,而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可以作為分析該對話的理論基礎。他認為對話關系中的差異性、內在的自由以及平等的對話地位是對話產生的必要條件,同時對話也具有未完成的性質,這些都為我們化解生態危機提供了方法論意義。如果我們能想梭羅一樣尊重自然的平等地位,堅持生命至上的和諧理念,和自然對話也將毫無障礙。
參考文獻:
[1] 徐遲譯.瓦爾登湖[M].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8.
[2] 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一卷)[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 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四卷)[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 沈華柱.對話的妙語——巴赫金語言哲學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
[5] 王建剛.后理論時代與文化批評轉型:巴赫金對話批評理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6] 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7] 朗松.方法、批評及文學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8] 翁德修,畢麗君.論《瓦爾登湖》的篇章結構及象征意義[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27(1):10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