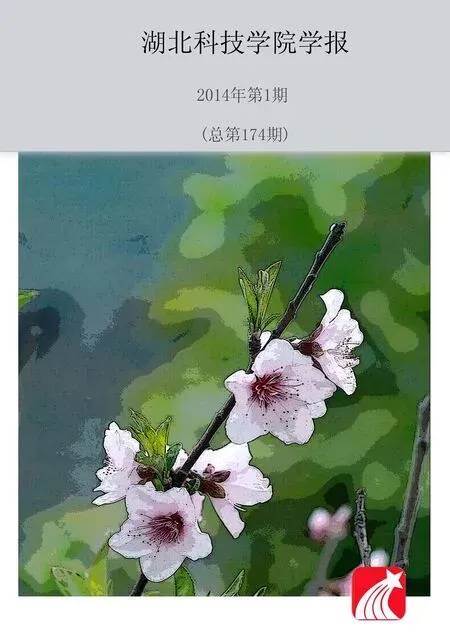新時期對《三國演義》“英雄史觀”的深層解讀*
徐彥峰
(太原大學 外語師范學院,山西 太原 030012)
*收稿日期:2013-10-15
“英雄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出現之前,社會歷史觀普遍認可的一種漠視人民群眾對歷史發展起決定作用的歷史觀。英雄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與人民群眾相對應的一種歷史范疇,一般指杰出人物,亦指對歷史發展有著重大作用的帝王將相和在思想領域起到明顯作用的人。在馬克思主義出現之后,這種片面夸大英雄人物創造歷史的觀點才受到強烈沖擊,人們開始正確認識和理解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決定作用。
在《三國演義》中,英雄人物眾多,他們扶大廈于將傾,救黎民于水火,肩負重任,臨危受命,勇敢地迎接著生與死的挑戰;尤其是那些悲情英雄更是激起了最壯麗、最絢爛的浪花,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演義者,本有其事,而添設敷衍,非無中生有者比也”[1],即“演義”是根據史實,敷陳大義的意思。《三國演義》就是一本歷史演義小說,其間,英雄人物更是群星璀璨,不可勝數,他們馳騁沙場,金戈鐵馬,或者救世濟民,力挽狂瀾,或者發奮圖強,建功立業,是時勢造英雄亦是英雄造時勢。
一、“英雄史觀”的文學再現
時過境遷,未曾想到的是,《三國演義》卻由于為英雄人物大唱贊歌而遭受白眼與非難,其“罪過”是抹殺了人民群眾的功績,忽視平凡小人物的存在,從而把歷史的進步完全歸功于個別英雄。一種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三國演義》的主要思想缺陷在于“歪曲事實,把歷史說成是少數剝削階級的‘英雄’人物創造的”,它對三國歷史現實的反映建立在英雄至上的思想基礎之上,其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盡管他們也注意到作品對封建階級的各類英雄人物也持有明顯的不同態度,特別是“擁劉反曹”,一褒一貶,涇渭分明,但又認為這僅僅是對英雄人物道德評價上的差異,所以無論是對正面英雄的歌頌,還是對反面英雄的詆毀,作者都宣揚了“英雄史觀”(何磊《三國演義·前言》)。
這樣的評述或許是事出有因。在當今社會,英雄似乎早已遠離了我們的視線,變成了遙不可及的天方夜譚;“英雄時代”不可挽回地悄然離去,連同那“英雄”的自信也一同化為塵土。我們早已無法體會那種驚心動魄、如霆如電的“尚武”精神,無法真正明了“英雄”頭上巨大光環的價值與意義。在沒有“英雄”的時代,群眾的力量、團隊的精神開始粉墨登場,在過著“小資”情調的日子,一些人早已經遺忘了兒童時代的英雄夢。而在失去英雄情結和英雄崇拜心理以后,難免與《三國演義》中的英雄有了“代溝”,覺得他們血腥味十足,成天就知道打打殺殺,也沒見著給老百姓帶來一點好處;即使不否認大家對劉備、諸葛亮等仁人志士還有那些好感,但再也不會傻呵呵地為他們的失敗哭天抹淚了。
時至今日,對“英雄史觀”在作品中的表現,也應作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對“英雄史觀”本身是否構成作品的“罪名”也可議論一番,因此,很有必要作新的評說。雖然活在當下的我們,與那個遙遠的“英雄時代”沒有半點關系,但是絕不能戴著有色眼鏡看人、看事,不能以現在的標準來框定那些亂世英雄,應該還他們一世的清白,因為正是這些“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才成就了《三國演義》不朽的神話!如此說來,“英雄史觀”恐怕只能是一種客觀性的存在,而并非完全是空穴來風。小說描繪了自東漢末年到三分歸晉的百年動蕩史,潛心讀來,可以隱約聽見“鐵馬冰河”的錚錚聲響,感受到英雄們“醉臥沙場君莫笑”的壯志豪情。
二、“英雄史觀”與“英雄人物”
三國紛爭,群雄割據,中原逐鹿,禍及黎民;但說到底,這不過是一場各個政治集團為爭奪政權而展開的生死大角逐。伴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抗衡,其斗爭的直接方式是軍事力量的對抗。而這殊死一搏,又表現為眾多杰出人士及英雄霸主們才識膽略的“大比拼”,其最后的勝負成敗取決于各路豪杰的自身命運。杜甫歌頌諸葛亮“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蘇軾贊揚周瑜“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文天祥贊嘆曹操、司馬懿“世以成敗論,操懿真英雄”,這些又何嘗不適用于三國的其他英雄?“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明擺著“人才”——也就是英雄——決定著三國爭霸的成敗;而英雄人物毋庸置疑地成了作品的中心,榮登至高無上的歷史寶座。
顯然,與這種英雄至上的英雄中心論相一致,《三國演義》不可避免地表現出人民群眾疏遠和輕視。曹操的狂言“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道出他極端自私的“奸雄”本色的同時,也顯露了所謂英雄視天下黎民草芥不如的隱情。無獨有偶,董卓的過激行徑更叫人驚嘆不已。作品第6回寫董卓與袁紹、曹操等十八鎮諸侯交兵不利,為避其鋒芒,決定遷都長安;群臣誓死苦諫草率遷都,百姓將騷動不寧,董卓厲聲大怒到:“我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無論曹操,還是董卓,無不視百姓任人擺布、宰割的羔羊;他們怎么會良心發現,把“天下”、“小民”的利益放在眼里?
在疏遠、拒絕人民群眾的同時,一言九鼎的英雄,理所當然的充當了“天下人”的救世主、人間的“諾亞方舟”。如果說在曹操、董卓那樣的“奸雄”那里,民眾的性命“輕于鴻毛”;那么在劉備這樣的仁慈明君那里,百姓的價值是否就“重如泰山”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小說第41回寫劉備攜民渡江,燒新野棄樊城,入襄陽,敗走江陵,裹挾民眾十萬迤邐前行,終于被曹兵追上。雖然一身是膽的趙子龍,在百萬曹兵中縱橫馳聘,力斬敵將50余員;張翼德聲若奔雷,在當陽長板橋頭作“獅子吼”,喝退曹兵;但劉備還是慘遭損兵折將、妻離子散的敗績。這里,劉備慘敗的原因昭然若揭,正是因為背著十萬民眾的大包袱。如果沒有這一巨大的牽累,劉備完全可以順利突圍;如果百姓具有一定實力,各自為戰,共抗強敵,那么劉備完全可以轉敗為勝,有濃厚文人氣質的羅貫中在歷史學家“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2]的影響下,筆下描繪的文學人物與歷史人物必有很大相似性。后來赤壁大戰前,諸葛亮出使東吳,聯吳抗曹,東吳謀士就以此為笑柄,譏諷諸葛亮;諸葛亮便以“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相隨”,劉備“不忍棄之”,“甘與同敗”云云,振振有詞,舌戰群儒。雖然作品的良苦用心是在以劉備的敗績來凸顯其“寬仁厚德”的品質和諸葛亮敏銳犀利、善于反敗為勝的辯才,但對人民群眾歷史作用的態度已經很明朗了。人民群眾成了不折不扣的“惰性物質”,與曹操、董卓把人民群眾視為“小民”、“群氓”,實在是沒有本質上的分別。
三、“英雄人物”與人民群眾
英雄人物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這種賜予與接收的關系,獨具慧眼的馬克思早已看得清清楚楚:在一般意義上,廣大人民群眾“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在這一維度上,人民群眾的社會地位和歷史價值變得微乎其微,不值的一提。
著名學者馮文樓概括“諸葛亮是儒家‘內圣外王’之理想人格的光輝典范,是知識分子參與政治‘為王者師’的優秀楷模,是集知識、道德、政治三位一體的完人形象”[3]。這是對英雄人物的集中概括和大力歌頌。《三國演義》中的“英雄史觀”不僅表現在對英雄的歌頌,對百姓的漠視,更主要的還體現在對黃巾起義的漠然態度上。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絕對是中國歷史上的“大手筆”,為歷史發展提供了絕佳契機,也是《三國演義》得以展開的歷史大背景。因為整個三國的歷史,是建立在勢不可擋的黃巾起義攻擊、瓦解東漢王朝的廢墟之上。然而作品無視黃巾起義的歷史必然性和推進歷史進程的巨大功績,把起義的原因,簡單歸結為太平道人的一己私欲,所謂漢室暗弱,“若不乘勢取天下,誠為可惜”。更無視黃巾起義的浩蕩烽火,只憑一紙朝廷文書,各路王師舉兵征討,便紛紛告捷。黃巾雖說“賊兵勢大”、“軍官望風而靡”,但畢竟是烏合之眾、無帥之兵,一觸即潰,很快就被斬盡殺絕了。
凡此種種,都證明《三國演義》中存在著“英雄史觀”這一鐵定事實,而在評價作品價值與意義時,如何對待這一惱人的“尷尬”? 法國文藝理論家丹納曾言:“文學作品能夠體現出一種人的心理,時常也就是一個時代的心理,有時更是一個種族的心理。”[4]既然一切木已成舟,不可回避,那就勇敢地面對,通過理性的分析來揭開這以事關宏旨而又亟須解決的“斯芬克司之謎”!
參考文獻:
[1]劉廷璣.在園雜志(自序)[M].上海:中華書局, 2005: 11~12.
[2]劉知畿.史通·惑經[M].上海:中華書局, 1997: 151~152.
[3]馮文樓.四大奇書的文本文化學闡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31~32.
[4]丹納.英國文學史(序言)[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