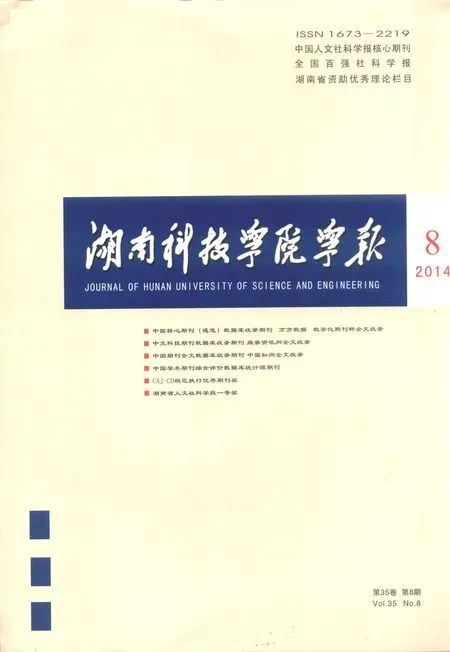論湖南永州陽明山文化彰顯的四個基本維度
陳力祥
(湖南大學 岳麓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湖南永州陽明山是湖南南部著名的旅游文化勝地。因陽明山獨特的自然環境,造就了她獨具特色的文化。十五大報告指出:文化大體可分為兩類,即物質文化層和精神文化層。物質文化即是實體文化,即在陽明山上所能見到的有形的各種實體文化現象。易言之,在陽明山生存與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人類利用各種材料對陽明山上各種自然物進行加工形成的各種可見的器物、器皿、建筑、工具、寺廟等等,這些屬于陽明山物質文化層面,是陽明山上可見的物態文化。其次,陽明山之文化現象還表現為精神層面的文化現象。陽明所凸顯的精神文化主要是指人類對陽明山的自然美景進行加工或塑造陽明山自我形象過程中形成的用語言或符號表現出來的、涵蓋著一些具有精神層面的、人格層面的虛體文化。如對陽明山秀美風景贊美的詩歌、文字、語言、音樂等,并由此而形成的宗教、哲學、繪畫、書法、風俗、制度等。陽明山所凸顯的精神文化、或者說虛體文化即是從兩個大的方面體現出來。當然,永州陽明山的文化精髓還可從文化定義的四個層面進行詳分,即陽明山彰顯了物態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以及心態文化四個層面,以下將從這四個層面詳述之。
一 對陽明山上自然物加工形成的實體而彰顯物態文化
物態文化表現為有形的、可見的文化形態。本文所界定的陽明山上的物態文化,表現為可見的、有形的建筑物、寺廟等,彰顯出先輩們對陽明山上的自然物進行加工的物質生產活動及其相應產品的總和。陽明山的命名與定位,是建立在人對自然認識的基礎之上,并對自然進行加工形成的物態文化。通常所說的文化表現出明顯的特征:即超自然性與超個體性。所謂“超自然性”,是指陽明山的自然風光、自然環境、自然物須打上人的印記與烙印,如此才能稱之為文化;易言之,純粹的自然物和自然風光不能稱之為文化,不屬于文化的范疇;只有在人有目的、有意義的基礎之上的活動作用于陽明山自然物和自然風光,如此方能稱之為文化。因之,陽明山物態文化的出現,不能脫離人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
首先,我們可從陽明山上的道場管窺其物態文化。有關陽明山的文獻記載曰:“陽明山:去縣治百里,在黃溪之尾。然山麓險絕,游者相望咫尺,無徑可達。山最高,日始自旸谷出,山已明,故謂之陽明焉。嘉靖間有僧秀峰者,禪定于此,今遂為秀峰道場所。”永州府志中提及了陽明山的來歷,也提供了陽明山上的物態文化:秀峰道場。就文化特色來說,文化須是主體作用于客體,人作用于自然界而成。陽明山上的秀峰道場,為佛教文化傳承者朝圣的地方,這種特殊的朝圣場地,凝聚的是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彰顯了陽明山上的物態文化。在陽明山上,還有著名的陽明山萬壽寺、鎮龍塔等古代建筑,這些古建筑物也共同構成了陽明山上的物態文化之一。這些物態文化所表征的是先人們在陽明山上的活動,并作用于自然對象而成的、可見的實體文化。這些古代建筑文化,凝聚了先人們關于古代建筑的心思,表達了他們對陽明山這個對象世界的基本思考。陽明山上這些古代建筑,表現為物態文化,必將給后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成就現代人對陽明山的無限遐想。陽明山上的物態文化主要是滿足人類最基本的物質生活需求,凸顯了古代人類對陽明山的利用與開發的智慧結晶。
陽明山上的物態文化不僅表現在古建筑物上,同時也表現為游客對陽明山奇山怪石的人化描述。比如說,由陳順柏拍攝到的陽明山上的“觀音合掌”與“望佛來朝”,同樣映襯了陽明山上的物態文化。陽明山上的一些自然景觀本不屬于文化范疇,因為文化須是人化、打上人的活動痕跡,方可稱之為文化。“觀音合掌”與“望佛來朝”,本無此稱謂,但通過人的想象與加工而成的臆想物后便成了文化。陽明山上的奇山怪石,本是陽明山上的自然物,在人的作用之下,陽明山上的自然物開始了人化作用,進而形成了我們所說的物態文化。陽明山上的“觀音合掌”與“望佛來朝”等物態文化,滿足了游客、文人墨客的觀賞需要,彰顯了陽明山上物態文化的基本價值。在陽明山上,類似的其他自然景觀為人所稱頌,繼而成為我們所熟知的物態文化。除了上述“觀音合掌”與“望佛來朝”有著豐富的物態文化意蘊之外,由陳順柏攝到的陽明山上的物態文化還有“天門口”和“秀峰塔”。其中“天門口”彰顯的是打上人類心智印記而成的天門實體文化。在陽明山上本無天門口,由于來往游客的對陽明山之驚奇,于是在想象中把陽明山上的奇山怪石人格化,充分發揮想象,把這道奇異的風景定義為自己所需的“天門口”,讓人形象地描繪為“天門”,一扇很難打開之門,人為因素描繪便成了人們看得見、摸得著的物態文化。同樣,陽明山上的秀峰塔主要源自于秀峰大師曾經修煉與圓寂的地方,為人所美談為秀峰大場所,也表現為物態文化。
綜上,陽明山的物態文化反映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反映了人在社會生活過程中必然向自然界索取并求得人與自然之間和諧平衡的基本價值傾向。物態文化必然是人作用于自然,并向自然進行索取、打上人的烙印的基本價值傾向。
陽明山不僅僅彰顯的是其物態文化意蘊,在陽明山作為有道而佛的過程中,高道、高僧大德遵守教規之時創造了獨具特色的陽明山制度文化。
二 因釋道二教教徒遵守教規而彰顯制度文化
陽明山秀美的風景,吸引了一些高道、高僧等到陽明山上修行、修煉。修行修煉需要固定的場所,于是就有了我們上文所說的高僧、高道們修行所需要的場所,如秀峰道場,這些道場成就了上文所說的物態文化層。據永州地方志的記載,陽明山最初由三山組成:
其一,“船櫓山:在城東百里,山傍斗絕,如船形,其間屈□水流,春霖積潦,凡三十六涉。”
其二,“福田山:在州東北五十里,山勢峭絕,中有一峰,聳立如塔,俗傳阿育王所建,故名福田。”這里說福田山,在州東北,方位記錄有誤,應為東南。
其三,“陽和山:在城東北八十里,接道州界,乃王真人修煉之所。”道州在零陵古城之南,接道州界,顯然應屬南,而非北。
船櫓山、福田山、陽和山是陽明山的三大山系。在這三大三系中,一些高僧、高道們因習慣于寂靜的修行環境,他們便棲息于陽明山修身養性。在陽明山上,最初到達此地修行的是道教修行者。這些道教修行之人,看重的是陽明山系中的寂靜與環境的優美,這與道家哲學中的“自然”學說相契合。“東南二里為陽和山,王真人修煉于此。”此處所說的東南二里應該是“東南百里”。(明隆慶《永州府志》卷七《零陵·山川》)可見,陽明山最初為一座道教修煉場所,后發展成為一座佛教場所,引文中的王真人所修煉的地方后發展成為佛教場所。從目前所查的方志文獻來看,陽明山最早是一座道教場所,始于王真人,并被元初賜額“萬壽宮”。明嘉靖后始易寺名為“萬壽寺”,陽明山從道家勝地轉而成為佛家道場。即是說,陽明山是由道而佛、由佛而儒的三教合一的圣地。道家也好、佛家也罷,制度文化規約著道家徒與佛教徒的行為。
所謂制度文化層,即是各種社會規范,它規定著人們必須遵循的行為規范。陽明山上有儒釋道三教文化的聯姻,儒釋道必定彰顯出其制度文化層面,因為就道教文化來說,道教徒必然有教規的制約,這些教規構成陽明山上的制度文化層。早期在陽明山上的道教徒必須遵循道教的基本戒律,稱之為道教戒律。道教的基本戒律有初真五戒,十戒、女真九戒等。女真的道德戒律雖然不一樣,但都有一種最基本的制度規約于其中,表現為制度規約,并因之而表現出制度文化層。陽明山上的道教徒,我們現在無從考證他們是否遺留下關于道教的基本文獻,但有一點可以確認,即便是他們沒有留下任何關于陽明山上的文獻(物態文化),但道教徒所遵循的基本教義,已在他們心中根深蒂固。道教的基本教義可以說是從制度文化層的基本要素呈現出來的。根據宗教學的定義,任何一種教別都有自己的教義與教規,這種教義與教規即表現一種制度文化。比如說在《太平經》所說“天道無親,唯善是與”[1],此言實際上彰顯出一種制度文化。《太平經》所規定的文化層面,即是一種制度文化。道教創立之初,嚴密的規誡制度就建立起來了,比如說“老君說一百八十戒”、“老君想爾戒”等,到了宋元明清時期,道教的教義在全真派的推波助瀾之下,還效仿佛教的基本教義制定了“全真清規”。所有這些道教徒所遺留下來的戒律與戒規,均作為一種制度文化遺留下來。
陽明山在明末清初的時候已經享有盛名,且最初作為道教徒修身養性的地方,以有文字記載的時間為明朝,摘錄如下:
明弘治《永州府志》卷二《山川》又載:“陽和山,在縣東南二里,乃王真人修煉之所。”很明顯,其“東南二里”有誤,應為“東南百里。”
明弘治《永州府志》卷四《人物》又載:“王真人,德安人,修煉于零陵陽和山。元初賜觀額為萬壽宮,封懿德真人,征入朝,遂不返。”
明隆慶《永州府志》卷十七《外傳》載:“王真人,德安人,修煉于零陵陽和山,元初賜觀額為萬壽宮,封懿德真人,征入朝,遂不返。”
就目前有文字可考察可知:陽明山作為道教活動場所始于明朝,而在元朝之時的道教的教義與教規,已經展現為“全真清規”,這種“清規”即可視為道教制度文化的一種出現的。
當陽明山由道而佛成為佛教文化圣地以后,陽明山的高僧大德在寺廟中的生活所需要的內部管理需要嚴格的制度文化。在陽明山,制度文化所彰顯的是高僧大德們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陽明山成為佛教文化圣地以后,凸顯了制度文化。陽明山作為佛教僧人修身養性之地,無形之中有一種制度文化規約著僧人的行為,也正是這種制度文化敦促著人們修身養性,敦促著人們守善、求真、務實。在中國傳統文化的三種境界當中,儒教文化倡導的是人如何成為賢人、圣人;佛教文化引導人們如何在佛教戒律的引領之下,讓人們進入到成佛之境界;而道教也通過制度文化,引領著人們能成仙。因之,儒釋道三教均凸顯了自己的制度文化。在制度文化的規約之下,使人之道德境界不斷得以提升。
陽明山作為中國的佛教文化圣地,其制度文化的存在不言而喻,盡管這種制度文化有隱形的成分蘊含期間。佛教文化引導人們成佛,其前提條件是通過制度文化的規約,更好地提升人之內心世界的道德素養。故此,在陽明山這個佛教圣地,無形之中就有一種制度文化規約著人之心靈,外化進而規約著人的行為。生活在陽明山的高僧大德,就有一種非同尋常的制度文化在規約他們。佛教文化底蘊為:“是心是佛,是佛是心……欲得早成,戒心自律。”[2]在陽明山這個特殊的佛教圣地,人們修行的目標在于以制度為規約,以制度戒心自律。可見,在佛教徒看來,人之內心世界的活動是制度安排使然。尤其是陽明山曾經作為佛教圣地,無形之中有一種規約自己行為的外在制度文化在規約著自己,這種無形的規約可以說一種無形的制度制度文化在規約著人們的行為,或者說是一種無形的佛教戒律在規約著佛教徒的行為,我們稱這種無形的佛教戒律為陽明山佛教制度文化。在制度文化的規約之下,高僧大德們均有最為基本的內心世界的活動:即守心。佛教堅持要守心,并認定守心“乃是涅之根本,入道之要門,十二門經之宗,三世諸佛之祖”[3]。守心的基本前提在于有制度的規約,將制度規約逐漸轉向為人之內心世界的“慎獨”。制度的規約能促使人慎獨,慎獨之后,則能于此向心,繼而成佛。修心養性,不向外尋求。陽明山系佛教圣地,因之,進入到陽明山,我們能感受到曾經興盛于斯的制度文化,是其制度文化在規約著每個佛教徒的心靈。由心靈之美,而逐漸影響到人之性:“佛向性中作, 莫向身外求”[4],那么向性中求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造成這種背后的原因是陽明山潛在的制度文化之規約使然,是制度成就了信仰,信仰修復了人之心,制度讓人修心靈、養氣質,從而提升人之性情。可見,陽明山在很大層面上已經凸顯了其制度文化。制度文化的彰顯,培養了人之心靈,因為“行道之人,每慎獨于心,防微始慮”[5]。可見,進入到陽明山,這個地方仿佛有一種無形的制度力量在左右著信徒的靈和肉,無形之中對一些信徒的靈和肉進行熏陶,這種熏陶和教化的背后力量是制度文化,這種制度文化來源于佛教經典,來源于佛教的基本教義。在陽明山這個佛教圣地,這種制度文化已經徹底內化為人們內心世界的制度文化,表現在外則體現為行為規范。在陽明山這個佛教圣地,制度文化對人的心性以及靈魂必將產生強烈的洗禮,經由內心世界的洗禮之后,在外直接表現為人之制度文化對人之行為的規范。比如說,在佛教經典教義對人之行為的規范即是如此,佛教的基本教義教導大家:“不得廢壞器用不賠償”,不得挑唆斗爭。“開兩舌頭,戒無益言”,“不得欺心,不得貪財,不得使奸,不得用謀,不得惹禍,不得侈費。”[6]因之,陽明山作為佛教文化圣地,對佛教徒的制度規約頗為明顯,且和佛教的普適性的經典教義具有一致性,從而凸顯出陽明山的制度文化意蘊。在我們看來,佛教文化的基本教義使我們更能清楚佛教文化的制度文化層面,也更能清楚陽明山這個地方作為佛教文化圣地的制度文化意蘊。此外,佛教的制度文化層還表現在“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凈其意,是諸佛教”[7],這也是一種典型的佛教制度文化。佛教的這種制度文化,教育大家要行善,善施天下。進入到陽明山,無形之中就可能受到佛教制度文化的規約,這種規約,彰顯的是作為佛教文化圣地陽明山的制度文化之底蘊。
陽明山作為佛道文化圣地,在這個圣地中生活的人們總有一種無形的、抑或是有形的制度文化在規約著人們的行為,我們將這種制度文化行為稱之為陽明山的制度文化。在制度文化的規約之下,道教文化引導人們進入到成仙的境界,佛教制度文化引領人們進入“涅槃境界”,“每個生命,均沒有高下貴賤等差別,一切眾生都具有真如佛性,也都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成就佛果,進入涅槃境界”[8]。可見,陽明山所彰顯了其制度文化,正是因為制度文化,使陽明山成為中國有名的佛道教文化圣地。
三 因善男信女對佛道二教篤信而彰顯陽明山之行為文化
陽明山作為旅游圣地,此地不僅景色迷人,更為可貴的是:此地作為宗教文化圣地,往來朝拜者更是絡繹不絕,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陽明山行為文化。陽明山文化中的行為文化可從歷史角度和當下角度來說明其文化意蘊。
從歷史角度來說,陽明山作為曾經的由道而佛的宗教文化圣地,曾經出現在此山的高道與高僧,他們的行為共同構筑了行為文化。
首先就陽明山的高僧、高道而言,他們修行行為即屬于行為文化之范疇。以高僧大德為例,高僧活動有很多明顯的特征:其一表現為高僧大德的集體約定俗成。易言之,高僧大德之修行、打坐、念經、悟道等系列活動的完成,是通過高僧集體商討約定的行為,且是每天必須完成的一種行為,久之,則形成獨具特色的行為文化。其二,高僧大德的行為具有一定的模式化、類型化特征。比如說高僧大德的行為,什么時候打柴、什么時候念經、什么時候打坐,均具有比較嚴格的規定,表現出其行為的模式化以及類型化的特色。其三,高僧大德行為的傳承性。陽明山作為中國佛教文化圣地,在很大層面上表現出其行為的傳承性。陽明山的行為文化,高僧大德的行為模式,與現代高僧大德的行為模式具有很大的承接性、“遺傳性”以及一致性。比如說,有很多的行為模式在一定層面上趨向于創新性,但大部分的行為模式均具有一定的傳承性,有一定的歷史性痕跡在里面。比如說,念經打坐等,均具有一定的傳承性。
其次,就當下社會情況而言,陽明山的行為文化除了高僧大德每天行為的固定性而外,還有居士們的一些行為所表現出的行為文化。居士們的行為也表現出行為文化的特點,居士們所凸顯的行為文化,主要表現出時間上的周期性、定期性等。為了求得佛祖的庇佑,或者是為了求得自己的財運,或者是為了求得家庭的幸福與安康,抑或是為了其他諸多因素,在信仰佛教的層面,我們認為居士們的信仰更表現出對宗教的一種篤信與虔誠。居士們在佛教基本教義(制度文化層面)中能體悟到諸多關于人生的基本道理。在儒釋道三教中,儒家哲學教育人們如何成圣、成賢;道教教育人們如何成仙,佛教教育人們能夠成佛。因之,居士們的理想與志向不變,即不斷向成佛的境界邁進,需要不斷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正因為如此,居士們也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行為文化。
每年到陽明山燒香拜佛的人絡繹不絕,從而形成了陽明山獨具特色的陽明山行為文化。在陽明山,他們有著固定的行為模式,比如說,居士們也到陽明山燒香拜佛,以尋求佛祖的庇佑。正因為如此,陽明山香火異常興旺。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行為文化。一旦到了每年的節日,或者是佛祖的生日、或者其他中國傳統的節日,陽明山就會熱鬧異常。居士們對佛祖的敬仰而付諸行動,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行為文化。居士們的這種行為文化同樣也表現出山三大特色:即集體的約定俗成、類型的形式化、模式化,以及時間上的傳承性。
陽明山居士們虔誠的信仰而表現出的行為文化,與陽明山的高僧們所表現出的行為文化層面,具有相同的行為文化的基本特點。可見,就陽明山行為文化的特色而言,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文化,與流行的行為文化的基本特點也頗具相似性。而在陽明山這個佛教圣地所表現出來的文化特色,正好反映了行為文化的內在特點。
當然,由陽明山而表現出的行為文化特色,其內在原因還在于信徒的心理文化,也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心態文化。因之,陽明山所彰顯的文化特色還表現出心態文化。
四 陽明山因人之宗教情懷而彰顯其心態文化
陽明山不僅僅有物態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之內蘊。陽明山所關涉到的三種文化層,其終極原因要歸結為陽明山所“綻放”的心態文化。心態文化是宗教信仰過程中所形成的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以及心理活動等的總稱。陽明山所彰顯的四種文化層中,陽明山的心態文化最為關鍵,也極為重要。心態文化系陽明山所彰顯出來的文化的核心泉源。事實上,陽明山所彰顯出的物態文化、制度文化以及行為文化均是心態文化的外顯,心態文化是這三種文化價值的內在動力泉源,是發生學意義上的其他文化源泉。陽明山的心態文化最為關鍵。
陽明山的心態文化分為幾個方面:首先是就陽明山的高僧大德而言,他們所表現出“色即空也”的內心寧靜的心態文化。他們所關注的是內心世界的安寧,不為外物所侵擾,不為外物所誘,這構筑了高僧們寧靜的心態文化。這些高僧們的心態,與塵世間游離的利益文化截然不同,他們所關注的是如何成佛,如何成就他們最高的宗教信仰問題。高僧們之所以選擇陽明山這個地方作為他們的安身立命、安道成性之地,完全是由他們的心態使然,由此也就構成了獨具特色的高僧心態文化。
陽明山地杰人靈,不同層次的人有不同的心理活動、有不同的價值判斷、審美情趣、思維方式。陽明山的高僧們有著不同尋常的心態文化,同時居士們也有著不同的心態文化。如前,陽明山居士們所表現出的行為文化,最初原因還在于居士們的心態文化外化為其行為使然,因為由心態文化可以外化為一種與眾不同的行為文化。在陽明山心態文化中,不同層次的人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文化不同。居士們雖然在家修行,但卻在特定的時間、以特定的方式到陽明山進行佛法活動,表面看來這是一種行為文化層,其本質上卻體現著居士們的心態,并由此而彰顯出陽明山獨具特色的心態文化。居士們雖然在家修行,由此表現出特定的行為文化,在家修行實際上表現為特定的心態文化。此外,居士們以為在家修行佛法遠遠不夠,基于此,他們內心世界的心理活動就會發生微妙的變化。居士們就會以自己的誠心與實意,到陽明山里表達自己的對釋迦牟尼的敬仰,對佛法的無限渴望與景仰,并超度成佛。他們到陽明山燒香拜佛的行為文化的內在動因就在于他們內心世界的矛盾與沖突,在于其內心世界所激起的漣漪,并因之而成就了陽明山獨具特色的居士心態文化。
就到陽明山旅游的人來說,他們也有一種共同的心態:對佛祖的懷念與尊重,這也表現出一種共同的心態文化。由陽明山所彰顯出來的心態文化,可從到陽明山上游客所遺留下來的詩歌中得以管窺。如何全華先生所作詩歌《詠秀峰修道》:幽巖獨坐影隨身,疊嶂遮天不見人,一念靜修誰可效,山精水怪轉相親。此處凸顯出那些在陽明山旅游的人的一種心態,即對秀峰法師的尊崇與懷念之心態、內心世界寧靜之心態。對秀峰法師的尊崇,此乃上山旅游之人所共同持有的心態。對秀峰法師懷念的游客還有羅文藻與揚杏。如羅文藻游陽明山的時候即作了一首《詠秀峰祖師》:山高雖藉道高傳,來到山中了世緣,滿岫白云真性見,靜參別透一重天。在詩歌中,表達了作者羅文藻對秀峰法師的無限懷念與尊崇的心態,因此,此詩歌凸顯出陽明山的心態文化的另一類。揚杏之詩歌《登陽明山有感》也同樣表明了他的一種文化心態:重九興登陽明山,名花異草撲鼻香。仰觀二龍戲寶寺,極目浩氣貫長空。秀峰奇洞似仙境,艮沙碧水賞心目。五百年前佛始奠,終有名山萬古傳。揚杏的這首詩歌,同樣也表明了作者的莊重與怡情的心態,凸顯了心態文化。
當然,陽明山的心態文化還因時代的變遷而更加持久留香。因為,一些高僧、信徒、居士的心態是不一樣的:居士們對佛教的信仰層面主要來自于他們內心世界對自己財產、對自己當下生活的不安以尋求佛祖的庇護,并由此而形成獨具特色的心態文化;而高僧、信徒他們終極目標一樣,并由此而形成他們獨具特色的心態文化,成就他們心中永恒的信仰,也即通過對釋迦牟尼佛的信仰,該放的放下,從而形成一種忘卻塵世間凡夫瑣事的超乎常人的心態,進而不斷地進行道德追求與價值追求,不斷提升自身的宗教信仰,以達到人身至善的道德境界,由此也就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心態文化。
五 結 語
陽明山看似一個簡單的地名,一個曾經普通的山澗林地、一個曾經在歷史上滄桑的地方,一個曾經風風雨雨、平平靜靜相互交織的地方。但這個地方經過歷史的洗禮,孕育了豐富的陽明山文化,我們稱之為獨具特色的陽明山文化。從文化四層面來說,陽明山文化包涵著物態文化層、制度文化層、行為文化層以及心態文化層。陽明山文化四層結構,共同構成了陽明山文化完整的邏輯結構。首先,從物態文化層方面來說,陽明山上整體可見的部分均表現為物態文化層。物態文化層是陽明山制度文化層、行為文化層的載體,也是心態文化層的載體,她承載著制度文化、行為文化以及心態文化。陽明山的制度文化,是建立在其物態文化的基礎之上的。陽明山釋道二教內部管理而制定的規章制度的總和,信徒們在相互約束、相互制約的基礎之上而形成的獨具特色的陽明山的制度文化。同時,在陽明山制度文化的背后,陽明山的文化還包含著行為文化層。在陽明山,制度文化規約著陽明山的高僧大德的行為,并由此而形成居士們的行為文化。當然,在陽明山,無論是物態文化的呈現、抑或是制度文化的開顯,還是行為文化顯現,最終都要規約為心態文化的規約。關于物態文化的形式與內容,制度文化的制定、行為文化的出現等,均要受到心態文化的制約。在心態文化的規約之下,將陽明山文化的四個層面進行了具體的鏈結,并由此構成了一幅完整的陽明山生態文化圖。總之,陽明山從其一開始,就以文化生態的形式出現,陽明山文化凸顯了其成為佛教圣地、人間仙境的自然的、人為的、歷史的必然性。陽明山文化彰顯的四個維度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共同構筑了陽明山獨具特色的文化名片。
[1]太平經合校[Z].北京:中華書局,1960:4;148-149;152.
[2]景德傳燈錄·傅大士心王銘[A].大正藏(第五十一卷)[Z].
[3]最上乘論[A].大正藏(第四十八卷)[Z].
[4]楊曾文,校寫.六祖壇經[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546.
[5]郗超.奉法要[A].大正藏(第五十二卷)[Z].
[6]百丈清規證義記(卷7下)[A].大正藏(第63冊)[Z].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485-486.
[7]法句經(卷下)[A].大正藏(第四卷)[Z].
[8]石剛.佛教文化精神與和諧世界理念[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