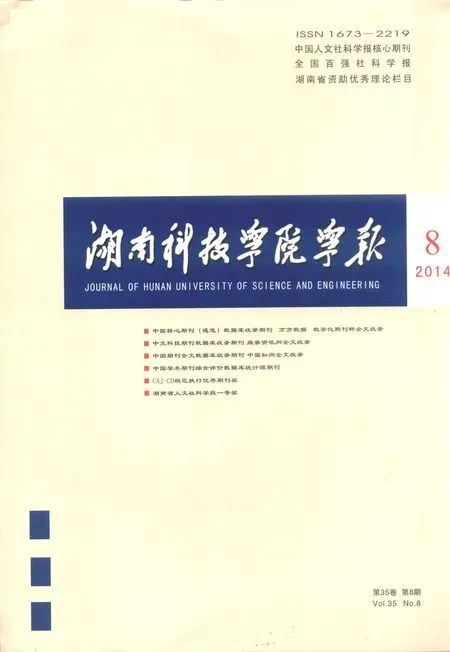《黑暗的心》的“文明”偽命題研究
謝冬文
(湖南科技學院 大學英語教學部,湖南 永州 425199)
當以占有和掠奪為主要目的殖民統治漸漸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人們驚訝地發現以西歐為代表的西方人時至今日尚無法完全褪去他們自以為是的、虛偽而高傲的外衣。然而文學家約瑟夫·康拉德在殖民猖獗之時就清醒地揭露了其虛偽性。殖民不是個體的行為,不是某一個西歐國家的行為,是當時的西歐強國均牽涉其中的行為。“殖民主義是一個體系。”[1]P9康拉德通過《黑暗的心》告訴大家歐洲在世界的殖民與古羅馬的征服戰爭本質上是一樣的,“只需要有殘暴的武力就夠了”[2]P488。兩者唯一不同之處在于殖民主義給自己強加了一個“觀念”[2]P489。這個觀念的核心是利他主義,即教化土著、傳播文明。既然殖民被描述為一項利他的事業,那它自然就是正義的事業,值得歌頌的事業。且不論殖民正義與否(當今的世人都知道它是非正義的),殖民主義的利他主義宣揚有一個看似完美的假設前提:西方人是文明的,非西方人是不文明的。殖民主義于是成為了文明的殖民者懷著崇高的利他主義精神幫助不文明的土著居民。殖民者成了“憐憫、科學和進步的使者”[2]P517,文明的使者。
然則在殖民的世界里只有一種文明:“西方文明”。(Kidd認為這種文明體系不是Teutonic or Celtic or Latin civilization,被稱為 European civilization也不貼切,最合適的稱謂是Western Civilization。)[3]P121將整個世界描述為一種文明與多種不文明的二元對立是粗暴的、武斷的、不可取的,這種“文明”注定是一個偽命題。
一 “文明”的虛偽性
殖民世界所謂的“文明”是殖民主義者為殖民量身定做的。著名的殖民主義者,英國功利主義代表人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對殖民主義世界的“文明”有過一次精準的定義:
文明不是改進的同義詞,而是與原始或者野蠻直接相對或相反的詞。我們稱之為野蠻生活習性的東西,與其相反的,或者社會用以擺脫這些習性的品質,就構成了文明。因此,野蠻的部落包含一些個人,游蕩在、或者稀稀落落地分布在一大片野地里:反過來,人口分布很稠密,有固定的居所,且大量集中在城鎮和鄉村的,我們叫做文明。在野蠻生活中沒有商業、沒有制造業、沒有農業、或者幾乎什么也沒有:一個農業、商業、制造業成果豐碩的國家,我們稱作文明。在野蠻群體里,除非戰爭來臨,每一個人都為自己忙碌,我們很少看見他們采取聯合行動;野蠻人常常也不會在自己的社會里發現多少樂趣。人類在大集體里面為了共同的目的一起行動,并且在社會交往中享受快樂,我們稱作文明……[4]P120
在這個文明的定義中,殖民者假設出了一種絕對的“原始或者野蠻”的狀態,通過對野蠻的定義得出一種荒謬的結論:凡是與野蠻相對的就是文明的。在這種看似荒謬的背后,那些所謂“文明”的特點竟然如此驚人地無一例外地可以適用在當時的西歐殖民列強身上。穆勒機巧地以一種荒謬而又看似客觀的方式將當時西方發展階段的所有特點迂回成為文明的內涵,企圖將文明內在為唯一的西方文明,進而粉飾殖民主義。穆勒認為,“文明”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合作的能力和克制的能力。這是文明的西方人與非西方人的重要區別。《黑暗的心》對這兩個特點逐一進行了批駁。
貿易站的混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殖民者的自私主義與不合作造成的。“道德派”站長庫爾茲因為自私與貪婪罔顧公司要求其回中心站的決定,決然走進殖民地的深處。自私與貪婪的膨脹激起了他強烈的占有欲望。“‘我的未婚妻,我的象牙,我的貿易站,我的河流,我的——’每一樣東西都是屬于他的。”[2]P553中心站長感受到了貪婪的庫爾茲的威脅,置公司事業于不顧,處處為難他并趁庫爾茲生病之時,不發醫藥補給、延誤救治時機,費盡心思置其于死地。在所謂“文明”的殖民群體中,合作只不過是一個笑話。
康拉德以為土著黑人在饑餓威脅面前所展現的克制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他認為饑餓是人類最難過的一道坎。“沒有哪一種恐懼頂得住饑餓,沒有哪一種耐力能熬得過饑餓,厭惡不存在于饑餓存在的地方;至于說迷信、信仰,或者什么你們不妨稱之為原則的東西嘛,還不如微風中的一把稻草末。”在饑餓面前,一切都顯得微不足道。然而被稱為野蠻人的土著們在饑餓面前所展現的克制卻是“深奧莫測”。[2]P541與克制的黑人不同,正是代表“文明”與“道德”的庫爾茲在誘惑面前無法克制自己。庫爾茲的“商業秘密”就是“毫無節制地滿足他的種種欲望”[2]P566,最終被自己的欲望吞噬。
二 “文明”的利他主義
Kidd認為“西方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利他主義”[3]P45,而這種自封的特征得到殖民國家的一致認同。Kidd舉例說正是因為這種利他主義驅使西方有識之士促成奴隸制的廢除,他似乎忘記了正是所謂西方文明人的殘暴與貪婪造就了臭名昭著的奴隸貿易。事實上,殖民主義者時時刻刻高舉著利他的口號。敘事者馬洛的阿姨在他臨行前一再囑咐他要“使那千百萬愚民擺脫他們可怖的生活習慣”[2]P497。庫爾茲宣稱:“每一個貿易站都應該像道路上的一盞能夠指向更美好事物的指路明燈,它當然是一個貿易中心,但是也應該是一個博愛、進步和教化的中心。”[2]P528西方媒體報紙上充斥著這種博愛利他的言辭,西方人為此還專門成立了“國際禁止野蠻習俗協會”并且委托庫爾茲“撰寫一份報告”。庫爾茲“居然有時間來寫下密密麻麻的十七大頁”,且有著“莊嚴靜穆的仁愛胸懷,異乎尋常的浩然之氣”。在最后一頁還有一個“類似注解性的東西”。這段文字“娓娓動人,足以激起各種利他主義情感”。[2]P555在殖民者的文宣與話語中,殖民成為了一種純粹利他的自我犧牲性行為,他們最重要的動機與目的似乎是引導“野蠻愚昧”的土著走向進步與光明。
庫爾茲還常常談論“博愛、正義、品行”,他似乎成了“道德”的化身。庫爾茲的話語一向冠冕堂皇,他還時時提醒自己的追隨者“必須注意動機——正確的動機——永遠要注意”[2]P583。所謂動機就是永遠利他的話語。他一方面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宣揚利他的動機,一方面卻肆無忌憚地攫取象征財富的象牙。殖民世界里的所謂“西方文明”的利他主義只是一種欺騙與掩飾,欺騙殖民地人民與公眾輿論,掩飾因為自己的貪婪與殘暴在殖民地所做的種種惡行。康拉德通過這位時刻注意利他主義正確動機的庫爾茲之口道出殖民者真正的殖民目的:“我的象牙,我的貿易站,我的河流。”殖民真正的目的就是占有與掠奪。利他主義將土著視為需要幫助與引領的對象,而殖民的目的瞬間將他們客體化為“敵人、犯人、工人”甚至“反叛的人”[2]P568。馬洛所看到的殖民者赤裸裸的貪婪、自私、占領與掠奪讓被宣揚的“西方文明”的利他主義特征變得蒼白無力,變得虛偽荒唐。
三 為什么是唯一的文明
在殖民體系中,殖民者是文明與道德的。殖民主義者將自己的文明定義為當時世界唯一的文明不是因為他們過于自大。這不是純學術意義上的文明探討,文明與道德已經成了殖民者的一種工具與手段,他們玩弄文明只是為了殖民的目的,為了讓殖民道德化。斯賓塞早就強調過了“為了目的而調整行為”[5]P13的重要性。當然這種手段的形成與西方殖民者所擁有的不對稱的強大力量是分不開的。康拉德認為他們的“力量僅僅是從別人的軟弱中產生出的一種偶然”[2]P488。在歷史的長河中,力量的此消彼長確實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重要的是殖民者對力量的運用。殖民列強使用這些力量將非西方的世界客體化、黑暗化、野蠻化。凡是非歐洲的地方都是黑暗的,而庫爾茲呆在“黑暗的心臟”。
殖民列強為自己設立標準去定義文明道德與野蠻,然后自封為文明的化身。尼采對這種自封模式進行過精彩的推理:
“好”的判斷不是來源于那些得益于“善行”的人!其實它是起源于那些“好人”自己,也就是說那些高貴的、有力的、上層的、高尚的人們判定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行為是好的,意即他們感覺并確定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行為是上等的,用以對立于所有低下的、卑賤的、平庸的和粗俗的。從這種保持距離的狂熱中他們才取得了創造價值、并且給價值命名的權利……以每一種工于心計的精明,以每一種功利的算計為前提—不止一次的,不是特殊情況,而是永久的。[6]P12
殖民者利用偶然強大的力量強行奪取話語權力的高地,將自己定義為好的、高貴的、高尚的、有道德的、文明的,將殖民地居民定義為壞的、卑微的、沒有道德的、野蠻的、無知的,從而在白色人種和其他人種之間埋下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進而賦予白人世界唯一的“文明”。
殖民者所需要的就是這種將自己與殖民地居民區別開來的距離感。這種距離感的背后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殖民者“詮釋、賦予、美化、詩化的力量”[7]P247。西方列強只有將自己美化詩化為唯一文明的代表者,才能定格自己文明、進步、道德的形象,才能合理化自己道德的制高點,進而讓“西方文明”所謂的利他主義成為一種必要與必然,并最終將殖民粉飾為一種利他的體系,為殖民合理化、道德化提供話語保障。尼采認為“粉飾是力量增大的結果。粉飾只不過是勝利意志的一種表述”[7]P241。粉飾是自以為勝利之時將自己進行美好包裝的一種心虛的行為,是一種自圓其說。無論粉飾得多么美好,殖民體系的邪惡本質無法被去除。“看待一種美好的東西必然要看它的虛偽性。”[7]P247無論西方列強怎樣絞盡腦汁使用自己所謂的理性與邏輯牽強附會地勾勒一張偉大的利他文明圖景,他的偽命題本質絲毫不會有所改變。
[1]Sartre,Jean-Paul.Colonialism and Neocolonialism[M].London:Routledge,2001.
[2]約瑟夫·康拉德(袁家驊,智量等譯).康拉德小說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3]Kidd,Benjamin.Social Evolution[M].New York:Macmillan and Co.,1894.
[4]Mill,John Stuart.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Volume XVIII[M].London: Routledge, 1963.
[5]Spencer, Herbert. The Principles of Ethics[M].New York:D.Appleton and Company,1897.
[6]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周紅譯).論道德的譜系[M].北京:三聯書店,1992.
[7]Nietzsche, Friedrich.The Will to Power Vol.II[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24.